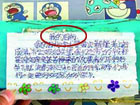10月29日,程家的北上计划提前了。程凤林告诉本刊记者,村里说程春明得了急病,要家人都去北京。因为患有严重的心脏病,程凤林被留在老家,其余亲属都赶到了北京。在首都机场,知道内情的人终于忍不住将真相告诉了程保忠。77岁的程保忠本来身体硬朗,得知噩耗后当场就昏倒。随后赶到北京的村主任刘光益向本刊记者描述了程春明家人的悲痛:大妹妹认尸回来后就神志不清,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程保忠昏厥了几次。只有程春明的妻子杨寒(化名)相对坚强,她拉着程保忠的手抚着自己的肚子说要跟公公一起把孙子抚养大,她不能太悲伤,会影响孩子的发育。刘光益说,香火传承是农村头等大事,杨寒这番话给了程保忠活下去的希望,刘光益转达程保忠的说法:“读过书的人就是不一样,通情达理、深明大义。”
刘光益算起来与程家还有亲戚关系,对程家的情况很了解。“那个年代村里都不富裕,程春明家尤其困难。”刘光益告诉本刊记者,实行联产承包制之前,劳动力的多少直接决定着一个家庭的经济状况。当时规定每人每年有400斤粮食,按照工分折成现金兑换。劳动力多的人家干的是“进粮活”,不但可以得到相应的粮食还能挣到一些钱,劳动力少的人家则是“缺粮活”,工分不够还要自己出钱买回粮食。程春明的母亲常病,家中只有程保忠一个劳力,每年都要向生产队交钱,生活困难。程凤林则回忆,哥哥小学毕业后,自己要求还要接着读书。程春明的大姐于是从高中辍学回家务农,成了地地道道的农妇。因为家里的经济条件一直没有什么好转,两个妹妹也都没有读到高中,早早结束了学习生活。
程春明外出读书多年,家里全靠三个姐妹互相依靠扶持过日子。直到2000年他从法国学成归来,才逐渐成为家里的支柱。程凤林告诉本刊记者,哥哥回国不久就开始每两个月寄一次生活费给父亲,一年有万把块钱。本来,程春明还想每月给她一些钱作为这些年代替自己照顾父母的补偿,但程凤林没有收。“哥哥读了这么多年书没有积蓄,刚刚工作,负担还是挺重的。”她说。
程春明以另外的方式照顾妹妹。程凤林患有严重的皮肤病和心脏病,因为没钱,最严重的时候也只是在县医院抓点药。去年,程凤林病重,躺在床上起不来,程春明把她接到北京,“花了几万块钱在大医院治病”。
甚至程春明的外甥、外甥女们也感受着舅舅回来后家里的变化。“农村人教育孩子也没什么方法,哥哥每次回来都要问小孩听不听话,他既很严肃,又会用孩子们喜欢的语言教育他们。”程凤林说,外甥、外甥女们都非常怕程春明,他讲话要比父母管用。
而在刘光益眼里,程春明虽然只是个“没什么权力的大学教授”,但他的同学是不可多得的人脉资源。程春明出事后,很多他在北京的朋友和学生赶来慰问,刘光益把这些人理解为程春明的“把兄弟”。他说,这些“把兄弟”最少都是“市以上的干部”,如果不出事,“将来能给程家、给村里办多少事呢”。刘光益对程家的遭遇唏嘘不已,他对本刊记者说:“熬了这么多年,眼看着有了盼头,却出了这样的事情。”
熟悉又陌生的家人
程春明家所在的上冲村由不同的湾组成,每个湾都是在山上开出一条小路,村民的房子沿着小路排成一行。程家所在的这个湾,只有程春明家和堂弟家两户姓程,其余全部姓李。“我妈妈说我们姓程的在湾里是小姓,你要留下帮着堂哥一家。”因为独子程春明外出求学,父母决定把最小的女儿程凤林留在身边。程凤林23岁时,招了一个上门女婿,在程春明“缺席”的12年里,担起了应由儿子承担的所有责任,给母亲送终,照顾年迈的父亲。现在,程家的祖屋已经被程凤林翻修为二层楼房,程春明每次回老家其实就是住在小妹妹家里。
记者到程家的第一个晚上,程凤林半夜起床吃速效救心丸,第二天一早就去村里医疗室打吊针。程春明的离世让她好转的病情再次复发。她说,感情刚刚好起来就出了事,早知道这样,哥哥还不如不回国,她心里也不会这样悲痛。从1982年17岁的程春明离开上冲村去武汉求学开始,随着他越走越远,与家里的关系也越来越疏离。
程凤林的印象里,哥哥放假回家就去山上放牛,兄妹间很少谈论学校的生活。她不记得哥哥填报大学志愿征求过亲人们的意见,“父母都不识字,农村人也不懂那些”。家里只能从经济上给予支持和关爱。“哥哥读大学的时候,实行了承包制,家里条件好了些,父亲每月都要寄给哥哥几十块钱的生活费。”80年代初,在一个农村家庭,这是很大的支出。对于记者“大学本来就发生活补助”的询问,程凤林说:“他除了日常生活,还要买些书吧。”
留学法国对程家来说不是一个喜事。“我妈妈当时就哭了,不同意。她身体不好,希望儿子毕业就找个工作留在身边。”程保忠当生产队长很多年,“比较有见识”,在父亲支持下,程春明的赴法求学之旅才得以成行。
1988年程春明出国后,他与家乡的联系就由小妹妹程凤林来维系。“通常都是我来写信,主要都是谈家里情况。”信封由程春明在法国写好寄回来。程凤林说,当时寄一封信要20块钱,很贵,一年只写三封信。程春明的母亲去世前,把程凤林精心保存的信都烧掉了。“这是一个农村老太太思念儿子最好的方式。”程凤林解释说。
程春明没有回来奔丧。程凤林解释,那时哥哥已经要自己赚学费和生活费,正是困难的时候,而且写信去已经来不及了。她不愿告诉记者,是自己没有写信去告知,还是程春明接到信赶不回来,抑或是当时他们兄妹已经失去了联系。但因为这次的缺席,村里人开始怀疑没有音讯的程春明已经死在了国外。
2000年程春明回国后,没有在第一时间通知家人,大约过了一个多月,程凤林才收到程春明定居北京、执教中国政法大学的来信。这一年也是程春明母亲去世的3周年,祭奠是一直等他回乡省亲才办的。此后,久违的男孩重新回归了家庭,放假和过年的时候都会回老家。“身上穿一套,夹一个包里带一套换洗的就回来,鞋不用带,回家就有换的鞋了。”为了让经常回家的哥哥生活舒适,程凤林甚至在家里装了农村罕见的冲水厕所、热水器和浴霸。“我哥哥不让我装,说自己是从农村出来的,都习惯。”程凤林坚持安装的这个卫生间利用率并不高,平时锁着门,一般只有程保忠和程春明使用。
因为哥哥省亲住在自己家,程凤林与程春明的关系逐渐密切起来,平时也会每隔几天通一次电话。但她从来不询问哥哥在法国的经历。“我和哥哥一起洗漱,看他40多岁满口牙都没了,就什么都不问了。”程凤林猜测,哥哥在法国一定很辛苦,“牙都没了,应该是劳累过度吧”。
程凤林不爱讲话,情绪好的时候最多笑一下。在她眼里,程春明是截然不同的性格,开朗、随和、没有距离感。程凤林说,哥哥每次回来都是“从这个湾到那个湾,每家都要去恭喜一下”。这个村里过春节时的习俗成了程春明的惯例,只要他从北京回来,就会挨家挨户地拜访。与中国政法大学校园里的“地中海标志性的红色花格裤”截然不同,程春明在村里并不张扬,程凤林见到的哥哥穿的是和乡亲们差不多的旧衣服,很纯朴。程凤林还回忆,有一次村里的老婆婆误会程春明出国是去做木匠了,程春明就顺着承认。“哥哥回来告诉我,他不能否认,然后告诉人家是去读博士,那样会让人觉得你出国回来骄傲了。”
平凡的农村高中生
程春明的数学老师叶大富告诉本刊记者,程春明就读的五中不算是好学校。“从学苗来说,最先挑学生的是孝感高中,然后县一中又挑,到了五中没有好苗子了。”而程春明肯定不是班里学习最好的学生,叶老师说,程春明能够稳定在班级的3名到5名左右,感觉“他学习很认真,但不是一个只知道读书的学生,也不老实,不是能让人欺负的那种”。叶老师能说出班里其他一些同学的特点,比如某学生听懂老师讲解的表情,某学生怎么教都不会,但他想不起与程春明交往的细节。“他不是一个特别引起老师注意的学生。”他这样总结。
之所以还记得这个学生,叶老师说是因为程春明是县里的名人,一有什么动静就会有人谈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程春明回家探亲的时候,曾经专程看望过叶老师。“我记得他当时告诉我,好几个大学都邀请他去工作,他选择了中国政法大学,他说他是个‘自由主义’,中国政法大学除了正常的教学外,有许多自由时间,可以做自己的事情。”程春明送给了叶老师自己的名片,这让叶老师念念不忘:“我教了一辈子书,很少有学生送我名片。”
大新中学的校长罗立俊与程春明是同铺而眠两年的同学。罗立俊告诉本刊记者,当时已经懂得了读书好穿皮鞋、读书不好穿草鞋的道理,他们读书都很刻苦,每天晚上21点半下了自习之后,还要和程春明一起在教室里多学两个小时。
程春明后来用《地中海的红帆》、《我的大学》抒发情感,而在罗立俊的记忆里,高中时代的程春明没有什么文学爱好。他们除了课本,接触不到其他的书,况且还是理科生,没读过什么文学作品。如果非要追溯程春明的浪漫行为,高他一届的师哥万少文回忆,早上看见过程春明吹笛子,是用竹子做成的很便宜的那种。
当时的高中毕业生有三种升学出路,最好的是考上大学,其次是念大专,再次是中专。罗立俊说,他们那一届只有两个人考上大学,程春明的成绩刚刚过线。大部分成绩好的同学最后都去了中专,对于农村孩子来说,这已经是很好的出路了,毕业就能转户口,分配的工作也不错。
这些念中专的同学中出了大悟县的县委书记、财政局长、教育局长、公安局长和罗立俊这样的校长。罗立俊说,大家私下里议论程春明上学上得不划算。与中年发福的同学相比,2000年刚从法国回来不久的程春明“又黑又瘦”,“他穿着皮鞋,还打着赤脚,我就说我们都有袜子穿,你怎么不穿袜子?”虽然程春明告诉好友,法国人都是这样穿的,罗立俊还是不置可否,这成了程春明在法国“混得很惨”的一个例子。
|
作者:
朱文轶 吴琪 王鸿谅 蒲实
编辑:
汪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