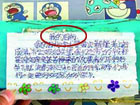孤独和解药
程春明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杀机从何而来。如果硬要程春明想个在学校里的夙敌,恐怕就只有折磨他很长时间的孤独感。
对于这种孤独感,程春明并不陌生,他过去曾用了12年来克服它。1988年,刚到法国的第一年,程春明几乎没有任何交流对象,就饱受孤独之苦。他和国内唯一的精神纽带,是在华中农业大学读研时的导师刘均谦教授。程春明给这位老师一连写过好几封信,把他刚到法国的困难一一诉说了一遍。刘均谦回信鼓励他克服困难。次年,刘均谦调到广东工作,他又把信寄到广东。
一名在法国和程春明一起留学的朋友告诉本刊记者,程春明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在这个国家留下来,而要在法国取得永久居住身份,首先得找到一份工作。和很多留学生的应对之策一样,程春明的办法是不停地念书、拿文凭,以延缓回国的时间,等待机会。他先后进了5所大学,涉足了4个学科,获得了6张证书或文凭,从文学、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一直到法学。机遇始终没有出现。上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虽然都放宽了对留学人员的时间约束,但在就业问题上却一直没有宽松。
到1992年,新的问题出现。国家中断了这批公费留学生的经费,要待在法国,就要继续维持学业,要维持学业,就需要钱。程春明陷入了人生的一个艰难时刻。他的银行账户到月底时常只剩几法郎,他靠给别人打字和翻译挣取生活费。“程春明的性格本来挺内向的,不擅交际。”这位朋友说,“生存的压力逼迫他在法国交些朋友。当时,我们这群学法律的留学生里,有很多韩国人,程春明跟他们走得很近。”
打零工根本不足以支付他在法国的生活费用,程春明只有通过举债来解决财务困境。他靠一个朋友的信用做担保,依次在3家银行贷款。当第一家银行贷款到期时,用在第二家银行贷的款还第一家的,同样用第三家的还第二家的,这样不仅能按期还贷,而且他自己的信用度也会不断增加,以后贷款额度也会越来越高。
就在这段边勤工俭学边读学位的时间,程春明结识了他的韩国前妻,比他大3岁的池英华。据说,池英华给程春明度过在法国的那段困难处境提供了不少帮助。程春明在留法的最后一年,跟池英华结婚了。
程春明最终没有在法国找到一份正式工作,他必须在回国和继续学业中间做出一个选择。实际上选择显而易见:即便有人帮忙,他也耗不下去了,他口袋剩下的钱,连博士生公寓一个月的租金都付不起了。
中国政法大学当时并非程春明回国求职的唯一选择。在他递交申请的3个学校里,其实他更倾向于另外两者:华中师范大学、武汉大学。他的学生时代和青春岁月是在武汉度过,以他的性格,那座生活了6年的城市对他更有吸引力。当他在法国得到中国政法大学的接收通知时,程春明仍然在犹豫自己的选择,迟迟没有给对方回复。
“我主要是看重他的法国求学背景,他可以说是我所见到过的第一个从法国博士毕业而又愿意从事法哲学研究的学者,是很稀少的人才。”程春明的领导舒国滢回忆这件8年前的事,这样告诉本刊记者,“我们同意接收他,可当时他在法国,等了很久,我们都没等到他的回信。”
“我专门打电话到法国跟他讲,希望他到中国政法大学来任教。就是接到我这个电话以后,他才下决心到我们学校。”舒国滢说。舒国滢是程春明的湖北老乡,1999年程春明32岁,舒国滢37岁,程春明被舒国滢的梦想打动了。舒国滢当时已经是中国法理学研究领域颇有建树的权威,他跟北京大学的朱苏力和吉林大学的邓正来,被视为法理学界“三足鼎立”的人物。舒国滢对程春明说,他希望程春明的加盟让中国政法大学的“欧陆法学派”得以壮大,这句话让程春明热血沸腾。他很快答应了邀请。1999年,舒国滢去首都机场接程春明时,看到他身边的韩国妻子,“他们一直是用法语进行交流”。
新学校太小了。程春明在舒国滢的引导下,把蓟门桥的校园逛了一圈,连一支烟都没抽完。这大概是他对中国政法大学这所自己即将执教终身的学校的第一印象。这跟他想象里的高校有点不同,和他追求的氛围也大相径庭。
程春明很快意识到了梦想和现实的距离。同一批被舒国滢引进到法学院的,还有留德学者郑永流,事实上,大部分研究大陆法系的法学者都选择了学习德语。到2000年,程春明在中国政法大学安置下来,他发现,整个法学院,研究“法国法”的只有他一个人,他连在学术上交流的对象都没有。他的一名学生对本刊记者回忆,程春明实在不太会跟学院里的那些同事相处,那时候,他在校园里见到法国人要觉得更亲切。
他把一些精力花在了校外,他参加了法国大使馆组织的“留法学生俱乐部”,所有和法国有关的社交活动,他都无一例外地参加了。
程春明沉浸在过去的时光里。法国的生活,在他的回忆里早已不再苦难重重,相反成了最令他骄傲的过去。他不仅乐于一遍又一遍地在他的课堂上跟学生讲述那些经历,还希望完全用法国式师生关系来构建他的新环境。“我们这届学生分导师时,已经是‘研一’下学期了。拜师的那天,程春明带我们几个学生先去家乐福,他说,‘要想做好学问,先要学会生活’。从超市出来,他就拿出充满奶酪香气的牛角面包,递给我们一人一个,‘你们一定都饿了,先吃一个面包,然后我们再去吃饭’。他就和我们在人流穿行的家乐福门口吃起了面包。”程春明带的一名研究生这样对本刊记者回忆,“当时觉得这个场景怪极了。后来,我们几个人到法国、德国留学后,才发现在任何一个场所,你都可能看到一个人在随口吃着面包或者三明治。一个学生在课堂上,一边吃着三明治一边和一个国宝级的法学教授讨论问题。”
程春明跟韩国人池英华以前累积的婚姻矛盾没有缓解,反而加剧了他的孤独感。池英华不会中文,在家属院里她基本上和其他邻居没有任何交流,也无法进入程春明的世界。程春明回国后,池英华“法国文学”的博士论文还没有完成,她在中国写论文,还要经常回法国开题与答辩。程春明的婚姻生活于是处于断续状态。“来回机票、住宿费都是春明给她凑的钱,最后帮她完成了学业。”舒国滢告诉本刊记者,“大约在2006年左右,两人和平分手,因为程春明的韩国前妻拿到学位后不能在中国找到工作,于是回到韩国一个大学任教,而程春明又不愿放弃他在中国的事业去韩国。”
要说刚刚回国这段时间程春明从就职的这所高校中得到了什么,就是他收获了很多学生朋友,这些年轻人成了他孤独的解药。他跟学生,包括一些女学生太亲密无间了,以至于,一些流言始终没有平息过。
法学教授的名利问题
在事发3天前一个周末的上午9点,还在被窝里睡觉的中国政法大学青年教师杨玉圣接到了程春明的电话,程春明告诉他,10月24日晚自己已经拿到北航的委任通知书了。这两个青年学者成为朋友是因为一些共同点:特立独行,怀才不遇。更实际的问题是,他们学术晋升的道路上都被职称问题绊住了脚步。杨玉圣曾经因为在北师大的教授职称问题迟迟不能解决,而跳槽到了中国政法大学。
“法学教育界已经越来越是个名利场了。”一名接受采访的政法大学老师说。跳槽现在是法学界司空见惯的现象,两年前,“人大”刑法学的支柱性人物赵秉志带着他的团队集体跳槽北师大,成为轰动一时的业内新闻。因为赵秉志的加盟,从来在法学上默默无闻的北师大一夜间成为国内刑法研究的前沿重镇。
这位老师说,另一方面,法学老师与现实社会联系非常紧密。有些老师把这个教职看做资本,帮助他们作为律师身份获取现实收益。向来被视为法学界黄埔军校的中国政法大学,面对着更多的现实诱惑。不过,在政法大学由最早的“法学院”衍生出的四大法学院:法学院、民商经济法学院、刑事司法法学院和国际经济法学院中,炙手可热的仍是几个热门专业的老师,比如行政法专业、民商法专业、经济法专业和国际经济法专业。
|
作者:
朱文轶 吴琪 王鸿谅 蒲实
编辑:
汪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