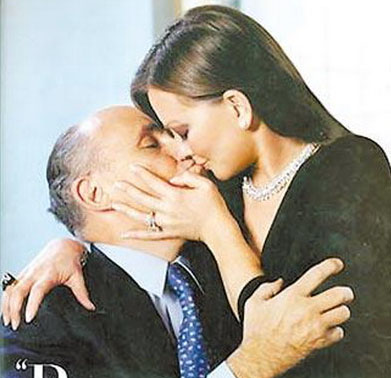凤凰资讯 > 视点 > 正文 |
|
| 相关标签 | [穷人堕落] |
结构定型的过程
什么是结构定型的过程?穷人和富人,谁是穷人和富人差不多了,八十年代也有贫富,但是一会儿他穷了,一会儿他富了,总是在变化,但是今天的情况不一样了,谁是穷人谁是富人差不多了,在座的还是年轻的朋友比较多,你们肯定是有希望的,但是也有跟我年龄差不多的,凡是跟我年龄差不多的,到现在还没有富起来的,我说够呛了,这个社会定型了。不太容易改变,一个很重要就是社会的门槛高了,你看最早的那批房地产商,有的是借来几万块钱就搞房地产,全国很有名的一个房地产商,开始借了五万块钱搞房地产,现在全国著名了,现在不是借,而是给你五万、五十万、五百万,弄一个房地产试试,没有可能,因为门槛高了。不但是这个门槛高了,你去菜市场摆一个菜摊,可能都进不去,因为那得靠人脉的积累、得靠经验。这个社会开始定型化了,定型之后一系列的问题就都来了,其他的问题我不讲了,就和今天这个主题相联系的是什么?是一个开始固化下来的下层,开始出现了。
刚才讲八十年代,八十年代的个体户哪儿来的?个体户曾经成为中国第一批富人,个体户哪儿来的?个体户当时往往是中国社会地位最低的人,知青回城,家庭没有背景,机关进不去,没有单位,只在街道的福利厂里,还有那时说什么人富起来?不三不四的人富起来了,还有山上下来的,什么是山上下来的?就是刑满释放回来的。这些都是当时社会地位最低的人,获得最早改革开放机会的人。但是如果现在还是在下层的,上来的可能性就很小了。
我们这些年在讨论这些问题,就象逗蛐蛐,得放在一个蛐蛐罐里,一个很小的地方才能斗的头破血流,现在我们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原来蛐蛐罐可能没有盖上盖子,但是现在盖上盖子了,你想跳出来都不容易了。这就是在一个社会结构定型化背景下的底层的状态,或者说底层状态是和这样的一个背景密切联系在一起。这是第二个大问题。
第三个大问题,优化社会结构,营造多数人生存的空间。
我最近在很多地方一直在讲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是生活在一个经济迅速发展,但是贫富差距在急剧扩大的社会当中,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当中出现了一个问题,我们如何使得绝大多数人在这个社会当中能够有一个生活的位置,能够有一个生活的空间,甚至可以说不是绝大多数人,而是所有人,在这个社会当中,有一个位置、有一个空间。我们不能否认经济在迅速发展,我们也不能否认绝大多数人的收入和生活在改善,但是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近些年来下层的状态实际上是有恶化的趋势。为什么?就是这个下层对于这个社会来说,他已经分出来,刚才说已经定型了,而且定型之后越来越表明你对社会是多余的,那么也就是说整个下层在社会当中已经越来越找不到他的位置。
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们现在讲构建和谐社会,我觉得我们就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无论是那一个阶层、无论是那一个群体、无论是那一个个人,只要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成员,他在这个社会当中都应当有一个生活的空间、生活的位置。这个生活的空间、生活的位置,不是说要靠平均主义,谁说搞平均主义了?这个空间、这个位置,最高纲领你活的好、活的成功,你在这个位置当中能够安居乐业,你活的不好、活的不成功,这个社会也有一个地方,你起码可以在这里安身立命,这是最低纲领。
我们说一个社会的底线,不仅仅是一个伦理的底线、道德的底线,或者是一个正义的底线,我们一个很现实的底线,就是使得我们这个社会当中的每一个人,哪怕是能力最差的人、活的最差的人、最贫穷的人,在这个社会有一个立锥之地,因为这是人,这不是动物。这是这个社会当中,现在我们所面临的一个问题。
现在我们在讲构建和谐社会,构建和谐社会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我觉得就是优化我们的社会结构,优化社会结构,有一些和我们今天的话题有一些是直接关联,还有一些不直接关联,比如说发展中产阶层。就我们今天的主题来说,优化社会结构,至少有两点。
第一,保护弱者的社会生活空间。保护弱者社会生活空间,使得他能有一个保护,或者是改善他生活的底线。在这个方面,应该说有一些好的进展,比如说在最近这几年的时间里,各级政府用于扶助弱势群体、扶助贫困群体的开支在增加,而且增加的速度是比较快的,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趋势。但是有一个问题,就现在我们叫贫困群体也好,我们叫弱势群体也好,我们叫下层或者底层也好,是一个规模不小的存在,所以仅仅靠政府的再分配,当然这个东西肯定是非常重要的,政府兜底的责任是非常明确的,但是我觉得仅仅靠这个是不够的。这当中很重要的就是如何使社会的下层、社会的底层,能够有一种谋生的机会、谋生的能力,这是至关重要的。这种谋生的机会、谋生的能力,是在什么地方?我最近一直在讲一个问题,生存的社会生态系统,这个生态系统是什么?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就可以形象的知道了。
原来在上海的浦东,刚刚开发的时候,浦东的条件还不是很好,上海有一句话,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套房。那时候在民间有一个说法,如果在浦西老城区,即使夫妻两个人都失业没有工作,没有关系,一天煮一百个茶叶蛋很容易卖出去,把这一百个茶叶蛋卖出去,一家老小的生计就不是问题。但是这个茶叶蛋能够卖出去是有条件的,是在老城区的社会生态里。如果到了浦东,不要说煮一百个茶叶蛋,就是二十个,都可能卖不出去,社会生态改变了,谋生的机会和能力就因为生态的改变而丧失了。
这里有一个很现实的,就是要造就这种生态,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今天的城市管理、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往往是以牺牲弱者的生存生态作为代价的。比如说原来上海把多少平米以上的小食摊、小饭馆全部取缔了,一般市民的感觉是吃早点没有过去方便了,但是更为重要的,可能十几万人就因为这个失去了谋生的机会,因为他没有工作啊,一早上包包子卖就可能一家的生计就有了,如果要搬到一个楼里去,收费高,人们又不愿意去,他生存的机会就丧失了。当一个大城市把马路的摊贩赶尽杀绝时,可能几十万人生存的机会就丧失了。一个三轮车在路上,我和司机聊天,让不让三轮车走,这一个三轮车后面是四五口人的生计,当你把这一辆三轮车没收时,可能四五口人的生计都没有了。当我们把马路上的摊贩赶尽杀绝时,可能一个大的城市就涉及到几十万人的生计了。
我们看到所谓城中村脏乱差、城乡接合部,看着有碍观瞻都要改造掉时,可能又有无数人的立锥之地丧失了,你把这种东西改造掉,给铲平了,这些人能够马上搬到别墅里吗?不可能,能够马上搬到三居室、二居室、一居室吗?不可能,只能是原来的生存之所完全没有了。
我觉得现在,包括在座的各位,其实我们都是脏乱差、城乡接合部的受益者,你想还可以按照现在的价格买到这个菜的话,你说贵,我说便宜多了,为什么?因为运菜的、买菜的,就是生活在脏乱差中,生活成本很低,这个价格把菜卖给你。如果运菜的住在别墅里,卖菜的住在三居室里,菜提高一倍的价格也不会卖给你。说现在的房子价格贵,那现在建房子的人,搬砖头的睡在工棚里,如果搬砖头的都住在别墅里、三居室里,现在的房价比现在高一倍,你都拿不下来。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生态的受益者,但是我们忘恩负义,我们不想这一点,我们也是拆掉脏乱差的积极鼓吹者,说这个地方都乱啊,不乱就不是这个价格了。
但是我这样说,并不是说城市不需要秩序,我们城市也是在发展,需要秩序、需要管理,这是没有错的。但是问题出就出在我们的管理上,就刚才所说的,马路上的摊贩没有秩序行吗?没有秩序,像北京,一年机动车增加四十万辆,一天一千多辆,现在上班没有小摊小贩都车走不动,如果都是小摊小贩别上班了。但是每天每个时段、每个地段都是这么塞吗?有的时间、有的地段不是这么塞嘛,有没有这个可能,特定的路段,平时不怎么塞车的,早晨上班高峰过去了,十点钟开始限定一个路段可以摆摊了,十点开始,但是有一点,下午四点必须收摊,而且要打扫干净。如果这样,他摆摊六个小时,一个大的城市,可能就这一条,能为几十万人提供一个生存的机会。问题是管理的问题,我们现在要么就是放任,要么就是一刀切,所以现在我们不但是说下层的生态在城市的管理中不断的恶化,而且矛盾越来越尖锐,所以摊贩和城管的矛盾,是我们大家经常看到的,一会儿他把他打了,一会儿谁把谁杀了,去年北京有一个崔英杰,杀了城管,也不叫杀了,就那么一挥刀,故意不故意的我也弄不清楚,反正就杀了。想起来,这也是前面《盲井》、黑砖窑同样的悲剧,扎和被扎的人都是谁呢?也都是下层。那城管,如果真正有门路的,也不去当那城管了,如果有门路的,也不去卖那个烤肠了。那个城管其实也是一个克尽职守的城管,那个崔英杰也不是一个坏蛋,原来在部队还是优秀战士,复员军人,几个月领不到工资,别人说你卖烤肠吧,但是他都不懂规矩,别人都是卖二三十块钱的破车,城管来了自己跑了车给扔了,结果他借了三百块钱买了一辆新车,没收了这车他是什么感觉,生计没有了,活路没有了,一刀进去,两条生命的悲剧。
第二、要有一个流动的机制。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如何来保护,甚至是改善下层的生存生态,这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这当中,最重要的还是要解决就业的问题,因为我们今天不是谈这个问题,简单提一句。就业的问题我觉得更重要是在中小企业。要优化社会结构,如何通过社会流动,造成这样的一种局面,就是你贫困但不至于绝望,社会当中有下层,但是这个下层仍然是一个虽然贫困,但是还是多少有希望的一个生存空间。如何造就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要有一个流动的机制。
现在我们这个社会,刚才说门槛太高了,你改变自己的地位机会少了,而且地位已经开始在世代之间传承了。前几年我们就有一个词“第二代富人”,也就是财富的继承、社会地位的继承和传递,这个过程已经开始。那么最近这几年的时间,又开始出现另外一个词“第二代穷人”,这表明的是贫困的继承和传递。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当中,提出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们如何在贫富差距比较大的情况下能够形成一个相对畅通的社会流动的渠道,用它来抵消贫富差距过大的负面效应。其实一个社会当中,仅仅是贫富差距大一点我觉得还不要紧,最怕的就是穷人失去向上流动的希望,最怕的就是一种绝望的感觉。但是现在应当说这样的一种趋势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是存在的。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当中,这种社会流动我觉得最主要的是两点,一个是教育,一个是就业。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在这里不可能说太多了。历史上,传统社会当中我们还有一个科举,每年考上秀才、举人、状元的为数寥寥,但是给无数人提供了一种希望,你这个渠道得有。就文化大革命那么荒诞的时候,你想人们有没有希望?不是完全没有希望,两条希望,做官、提干,相当于科举当中的文举、武举,社会不是让你完全没有希望。
这里尤其要强调一点,就是在保护和改善下层生存生态当中的政府责任,穷人、弱者已经到了那个状态了,他没有自己来争取自己利益,甚至保护自己都没有可能,你想想黑窑工,外面六条狼狗,还有一帮打手,怎么为自己守卫底线、怎么为自己求得一个最基本的公正?没有这个办法。这个时候,谁的责任?但是从整个黑砖窑事件,我们可以看到至少在基层,事实上是有我们一个关于底层的最基本的政策取向,叫什么呢?就叫“没政策”,换句话说,就是别出事就行。而在这样的一个取向当中,政府维持正义,给社会的底层以基本的保障和底线的这个责任被放弃了。当时南都的社论,“以国家的名义守卫文明的底线”,这一点应该是我们不断加以强调的。
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
|
作者:
孙立平
编辑:
李新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