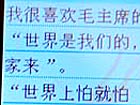媒体处理战争的创伤记忆需要有学术界首先是历史学界配合,学者的工作价值在于防止媒体的宣传简化和极端化。但是不能不承认,中日双方的学者与本国媒体的关系都非常不理想。构成阻碍的当然首先是BURUMA乃至水谷尚子这类人面对传媒表现出来的无意识的优越感,支撑这种优越感的是对于所谓历史真实的片面性和表面化的理解。比如南京大屠杀的数字问题一直是部分日本学者追究的问题,即使我们不在右翼的意义上即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意义上为这种追究定位,即使我们承认这种追究的动机是纯粹学术的,但是它毕竟把讨论的目标从南京大屠杀的残忍性转移到统计学上来了。在这一转移过程中,有一个重大的省略,就是对于中国人、日本当事人如东史郎、他国旁证如拉贝的战争记忆的不尊重。澄清历史事实当然重要,但是这种澄清工作是否意味着对情感、记忆乃至记忆的疏漏的简单否定?对于历史事件的精细考证,为什么一定要被置于感情的对立面?假如按照东史郎诉讼案的逻辑纠缠于细节的推理,历史变成了什么?事实上,普通中国市民对于南京大屠杀的关注,主要集中在日本侵略军屠杀和奸淫表现出来的兽性上面,这不是统计学所能够涉及的问题;这也是东史郎那一页日记的份量。即使这一页日记的原本已经遗失,即使东史郎因此而再次败诉,日本军队在侵华战争中的兽行依然是无法否认的。东史郎日记其他的部分记述了相同的令人发指的虐杀和奸淫的罪行,而且越来越多的中日知识分子已经揭示了大量的日军暴行的残虐程度,从日军进行细菌战时在普通中国农民身上进行活体实验,到强奸中国妇女之后再杀掉她吃她的肉; 20这些兽行如何能够被统计学的数字说明?这些无法数据化和实证化的“历史记忆”,是否应该在历史研究中获得应有的位置?它们是否也构成历史的“真实”?诚然,有些知识人正在对此进行揭示,但是他们不是历史学家,而是其他领域如心理学、精神医学的学者。假如历史学家以统计学为己任,至少也该了解自己工作的局限,如果以此为君临一切的“历史真实”,那么这样的真实无法面对复杂的历史局面,也无法面对活在今天的历史。
水谷作为一个尚未真正开始学者生涯的研究生,也许不足以代表日本的历史研究界,而且发生在她身上的问题不仅仅是统计学取代历史研究的表面现象。耐人寻味的是,水谷本人所从事的有关中日战争史的研究工作,她花费大量精力进行的“口述史”资料整理工作,本应该与东史郎在中国的活动构成某种呼应关系,从表面上看完全不应该导致她在《实话实说》现场所表现的那种令人失望的立场,这种对立对于我来说,至今仍然是一个谜;因而我只能把水谷本人的意图与她的行为所导致的后果分开来看,并且把讨论仅仅限于后者;21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水谷在《战争的记忆》里的表现以及剪接后显得相当温和的她与在场者之间的龃龉,恰恰极为典型地象征了中日部分知识分子之间围绕战争责任不能达成共识的要害之处。这就是割裂具体事件与它所处的历史和现实语境间的关系,孤立地追究“历史真相” 的实证根据的做法与过分诉诸于情感义愤而无法把问题推进到更深层面的做法之间的冲突,还有中日知识人因为不能相互对视而日益加深的鸿沟。在这一鸿沟背后,潜藏着现代学科建制本身的问题,潜藏着学者“言必有据”的姿态所粉饰的思想的苍白。事实上以“中国”和“日本”来区分这种认识历史的态度是很不准确的,因为水谷这样的学人也存在于中国的历史学界。就《东史郎日记》而言,正如本文第二节所论及的那样,它作为证明日军侵华暴行的证词其资料性远远不如《拉贝日记》,但是它作为从内部证实日本军队的暴力结构的证词,作为记录了战时普通日本人具体心态的第一手资料,其价值无法否认。而中国与日本的学者都未对这部日记的基本结构给予充分的关注,仅仅把它作为证实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加害者证词,这就错过了一个研究“活着的战争”的机会,把《东史郎日记》的主要价值消解掉了。与此同时,还应该注意到一个与知识界对待历史的表面化态度相呼应的现象,那就是同时发生在中日青年中的历史记忆的丧失。当水谷强调日本的教科书没有回避教授南京大屠杀的时候,她说的正是这种抹掉了历史记忆的“知识”,如同上文提到的《产经新闻》的那段体现着保守倾向的介绍性短文一样,所以对于水谷来说,了解了哪怕是一个注释,就等于了解了历史;《战争的记忆》中出场的另一位留学生则证明了这种概念偷换的存在。他说:这段历史在课堂上学过,但是东史郎和中国受害者讲述的“历史记忆”,对他来说仍然是第一次听到。而已经有记载表明,中国的年轻一代也正在与这种记忆保持距离22。当年轻一代的这种情感距离与传媒的情感攻势形成互动的时候,最大的危险就在于极具破坏性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和缺少主体性思考的知识性态度的简单结合。水谷本人的动机又当别论,她在电视上的姿态正象征了这种简单结合,而在中国与日本的很多青年身上,已经可以看到相同的倾向。
由于研究者对于媒体的轻视,更由于各种复杂的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张力,两国媒体不断复制的基本思维结构迄今仍然保持着令人吃惊的“超稳定状态”。就中国的媒体而言,“日本”作为一个整体,保持着不变的野蛮形象。尽管东史郎和他的支援者来华,作为有良知的日本人,他们在媒体上的倾诉也仅仅是加深了中国人对拒不认罪的“日本”的憎恶而已;而水谷尚子失败的表现,却使得她在事实上代表了她试图以自己的工作加以否定的今天的日本。可以说,东史郎和大量有良知的日本知识分子的工作,在今天的中国传媒里仍然无法撼动既定的“一勺烩”的日本形象。与此相对,日本的传媒也一直在复制着它的中国形象。这是没有民主、没有言论自由、不能面对历史事实,不断根据政治需要改变历史真实的形象。东史郎在中国引起的热烈情绪,被视为有组织的宣传活动,中国人民的感情创伤,被轻易地归入了政府的政治谋略。而在日本传媒的字里行间,时时流露着当年东史郎在日记里流露的种族优越,那就是中国没有历史真相,而日本却是一个追究历史真相的国家。
不能不指出,在水谷的论文里,也复制了这种日本传媒的逻辑。尽管她强调自己是一个历史学者,但是当她指责中国人对战争责任的认识“有错误”和描述自己在电视播出后接到的抗议乃至威胁电话的时候,不分析电视节目制作这一特殊的效果,就简单地把这一事件的反应推而广之地导向对中国整体状况的简单性评价。这种思维的短路固然与水谷本人的修养有关,但假如追问下去,我们不能不问一句,这种简单现成的结论是怎么来的?
与此相对,中国的学者中也不乏简单复制中国传媒思维模式之人。这使得中国的日本研究一直处在一个相当低的水准上,也使得中国知识界对日本战争责任问题的讨论要么知识化,要么情绪化。在现阶段,为自己的学术论文规定民族主义姿态是多数人共有的潜意识,而作为被害国与战胜国,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二战的思考其实并没有达到日本进步知识人的深度。日本知识界有关战争责任的追究基本上没有真正进入多数中国知识分子视野,不能全部归咎于日本知识分子没有对外寻求理解,也要归咎于这些中国知识分子对传媒式地追究战争责任之外的其他问题缺少兴趣。而与此同时,中国的传媒和知识界又在现代化的名目之下大力宣传所谓的“日本现代化模式”,日本的现代化与日本的侵略战争史被完全视为无关的两件事情。应该承认,《东史郎日记》所体现出来的日本社会的暴力性与日本人对中国的种族优越感,如今改变了形状却被中国传媒在“现代化”的名目之下加以合法化和接受,对此中国的研究者有着相当的责任。
学者为什么要研究历史?什么是历史的真实?学者如何与传媒相关?跨文化的对话如何才是可能的?仅仅在对围绕着东史郎所发生的事件中,我们已经得到了太多的教训。我没有资格在此扮演裁决的角色,作为也在从事日本研究的中国人,我感到的是自己面对这一复杂工作对象时的道德责任。那种以知识和资料来压制战争记忆的做法,那种以简单的民族主义情感代替严肃思考的做法,我将引以为戒。
| 您可能对这些感兴趣: |
|
|
|
作者:
孙歌
编辑:
刘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