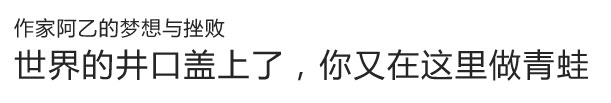
绝望时,警察艾国柱感到世界的井口盖上了,自己又在这里做青蛙。他就在井底计划着如何“走出镇,走到县,走到地级市,走到省会,走到直辖市,走到北京,走到纽约”。十年后,砸掉铁饭碗的乡下警察艾国柱在北京成为作家阿乙……

作家阿乙接受凤凰网对话。周东旭/摄
核心提示:凤凰网5·4青年节特别策划:“怪青年访谈录”之对话作家阿乙。阿乙原名艾国柱,出生于1976年,大专毕业后干过5年警察,投奔媒体,转战郑州、上海、广州、北京,做过9年体育编辑。2006年开始写小说,作品陆续出版。阿乙的小说场景多半置于小县城及乡镇,情感压抑,人物往往有着反抗而失败的宿命。本期对话聚焦于阿乙的人生选择,一个乡下警察是如何在多次挫败后,一步步实现自己的梦想,转型成为一个作家?一个作家,又为什么觉得“活着是一种幻觉”,他将如何实现“留下传世作品”的新梦想?
十多年以前,有一天,江西瑞昌一个乡下派出所的警察艾国柱,和副所长、所长、调研员四个人按东南西北四向端坐打牌,鏖战一夜后,所长提出换位子,重掷骰子。四人便按顺时针方向各自往下轮了一位。艾国柱就是在这一刻看到了他极度无聊的永生:20岁的他变成了30岁的副所长,30岁的副所长变成了40岁的所长,40岁的所长变成了50岁的调研员。
警察艾国柱决定出走。
十年后,出走的警察艾国柱变成作家阿乙,而上述牌桌场景成为阿乙笔下最得心应手的小说内容。警察艾国柱在现实中不存在了,却在阿乙的作品里一次次出现:一个压抑的青年,在一个憋屈的地方,做着自己不喜欢的事,没有任何理由,就是不喜欢。不愿意就此虚度一生,盘算着走向外面世界的一切可能。
这一算就算了5年。当时的艾国柱计划着“走出镇,走到县,走到地级市,走到省会,走到直辖市,走到北京,走到纽约”。
5年里,艾国柱一次次尝试,到处找工作,却一次次被挫败。他想做体育记者,但别人对他说,你最适合去找的工作是保安。当他最后决定脱下警服,也理所当然地被家乡人骂作傻子,警察是一个铁饭碗,居然有人宁愿砸了铁饭碗去外面做一个临时工。
父亲也不站在他这一边,在父亲看来,“你在外面也没有什么用,你看人家像你这么大年纪的,30好几,人家都有家有事业,你有什么,你就是一个流浪汉”。
阿乙回忆起这些挫败,感觉“就像一只鸡,你在展翅飞翔的时候,飞到一定距离的时候掉下来了,然后天上的大雁、凤凰都飞远了,你又走回鸡窝去了,你那种挫败感,你那种失落感很难以形容,不会哭,但是你心里面非常难受,你觉得整个世界的井口又盖上了,你又在这里做青蛙”。
但当他最终成功出走,并拿起笔来创作小说时,那令人压抑的5年警察生涯,却成为他进入文学世界的最锋利的武器。他将做警察时的压抑感全部注入自己的小说中,而这种压抑感又为他赢得了不少读者的共鸣。
谁没有压抑过呢?
十年间,阿乙按照计划“走到了北京”,去不去纽约已经不那么放在心上。出走时只想做一个体育记者,几经周转,成了一名小说家。生活已经超出了想象。
谈及现实,一样的琐碎,该上班上班。普通青年阿乙说,“父母还是希望你结婚,这种希望会变得越来越唠叨,因为结婚要买房,买房又要背债,背债你要还债,因为还债你要上班,就是这么简单”。
谈及社会,阿乙承认自己没有做知识分子的情结,对政治冷漠,他只想写作,不危害、打扰他人。
谈及作品,文学青年阿乙总是对已完成的作品不满意,他觉得“我现在所有写的东西,没有一个我觉得到达我心目中那种价值的50%”。他最害怕的,是“丧失写作的独立权”。
谈及未来,他固然可以用调侃的语气去谈论诺贝尔文学奖,却没有掩饰留下传世作品的欲望。他希望“五十年以后,还有我的十篇小说在流传”。
十年过去,因砸掉警察饭碗而被家乡人骂作傻子的阿乙,今天已经可以用作品来回应。关于梦想,他说:“只要那个东西在心里不死,只要你活得够长,就肯定会实现”。
对话主持:谭不 周东旭
对话实录:
阿乙:放弃警察工作大家都说我是傻子
凤凰网:几天前看到《江西日报》的一条新闻,记者是这么写的,说近日从瑞昌有关部门了解到,瑞昌籍作家阿乙正在角逐华语传媒文学大奖。这个说明瑞昌那个地方有人以你为荣。
阿乙:我觉得有关部门可能是我爸爸。他现在中风了,身体特别不好,多看一些我的好消息对他的身体好。
凤凰网:他会给你做各种各样的剪报吗?
阿乙:没有,都是我打电话告诉他,我最近有什么可能获奖,或者是我最近要去哪,或者作品在哪发表,不停地给他一些惊喜,因为我觉得他挺难的。半分钟可能走10米或者20米那样子,特别慢,整个手是残废的,右腿也是知觉有一点问题,就靠左腿拖着右腿走,他现在整个生活需要一些兴奋剂,所以我经常会给他一些,他肯定是感到有一点光荣,因为我出来混了。
我2002年不要警察的工作,从县城跑出来,大家都说我是傻子。一直到2010年,整个8年,我一直在郑州、上海、广州,最后跑到北京来,跑了很多地方,又没有存款,又没有房子,又有没有车子,又有没有媳妇。我一回家过年就烦,因为老同学或者是朋友他就会问你,你有车吗,你有房吗,你老婆哪的人,我说我三大件都不齐,总之他们就觉得很我傻。
我父亲的压力也很大,天天说你在外面也没有什么用,你看人家像你这么大年纪的,30好几,人家都有家有事业,你有什么,你就是一个流浪汉。我这两年才出来一些书、发表一些小说,包括获了两三个奖。我们当地那个县城,逐渐意识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一天找我去采访,我们老家人,他们没人读我的小说,也没人知道我写了什么,但上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他们来说那可能是一个县委书记,或者是县长才有资格的事情。他觉得这个还蛮不错的。
阿乙:你往下走,就是世界尽头
凤凰网:当你从警察岗位出来的时候,你父亲和你都没有想过你会成为一个作家?
阿乙:我当时的理想是做一个体育记者,因为我从小就比较喜欢体育。我爸爸是一个乡镇的药店经理,那个时候我常去给他们到邮电所领报纸、领杂志,因为我爸爸的那个单位定了一份叫《新体育》的杂志,我从小就喜欢看那里面的图片,所以长大以后就很想做体育记者。
所以我当时就去应聘,应聘了很多单位,最后去了《郑州晚报》做体育编辑,当时没有想到要写作。因为我觉得,作家两个字,文学家三个字,这样的一个称呼,就像天上的星辰一样,可望而不可及。你想一下作家在我们心目中都是什么,都是海明威,或者都是托尔斯泰、莎士比亚,中国的就是老舍、茅盾、鲁迅。你说你去做一个作家,跟他们在一个序列里面,你都觉得这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所以当时根本不会想到要成为一个作家,只是想做一个体育记者,其实是做了9年的体育编辑,没做过1天记者。
凤凰网:你说了一个很重要的词,可望而不可及,是不是目标是可及的,你才去做?
阿乙:我一定会定一个我达不到的目标去实现。我的目标,有时候看起来也很不合实际,特别想当然。但是只要那个东西在心里不死,只要你活得够长就肯定会实现。我现在36岁,我印象很深的是,我从警校毕业,分到我们那个乡村派出所。那个地方你再往下走,是没有地方可走的,就是你到了一个乡下,到了一个村,到一个村小组,村小组往下没有单位的,你在那个乡里面,你所在的就是一个小组,你往下走,就是世界尽头,没有办法往下走。但是你往上走有很大的空间,你可以走出镇,可以走到县,走到地级市,走到省会,走到直辖市,走到北京,走到纽约,你还可以去火星。
那个地方特别无聊,待不下去,憋死了。然后就立下一个愿望,要沿着那个路线,从那个乡镇派出所,要走出镇,走到县,走到省会,走到直辖市,走到北京,走到纽约。后来确实差不多是按照这个轨迹一路走过来的,其实是花了我现在这么多时间,其实差不多完成了。当年我在那个乡村里面,说我要去纽约,大家都觉得我是一个傻B。
凤凰网:小时候作文写的很好吗?
阿乙:写的不错,现在看来我不是什么文学家,但至少是个文学青年。我觉得有些想当然的东西,你今天可能达不到,但是有一二十年的时光,你就达到了,你不知道怎么就达到了,只要你心里有这个东西。
凤凰网:你在做警察的那几年里,是不是每天很晚都在计算,你离开之后怎么办,怎么办?想各种各样的路线图?
阿乙:我现在的生活都超出了我当时的想象。因为在那个地方就像坐牢一样。一个坐牢的人,对外面的天空,他会有很多想象。我在县城里面就会很酸楚地想,我未来如果在一个大城市,我应该怎么生活,我能想到的其实非常有限。

作家阿乙接受凤凰网对话。周东旭/摄
核心提示:凤凰网5·4青年节特别策划:“怪青年访谈录”之对话作家阿乙。阿乙原名艾国柱,出生于1976年,大专毕业后干过5年警察,投奔媒体,转战郑州、上海、广州、北京,做过9年体育编辑。2006年开始写小说,作品陆续出版。阿乙的小说场景多半置于小县城及乡镇,情感压抑,人物往往有着反抗而失败的宿命。本期对话聚焦于阿乙的人生选择,一个乡下警察是如何在多次挫败后,一步步实现自己的梦想,转型成为一个作家?一个作家,又为什么觉得“活着是一种幻觉”,他将如何实现“留下传世作品”的新梦想?
十多年以前,有一天,江西瑞昌一个乡下派出所的警察艾国柱,和副所长、所长、调研员四个人按东南西北四向端坐打牌,鏖战一夜后,所长提出换位子,重掷骰子。四人便按顺时针方向各自往下轮了一位。艾国柱就是在这一刻看到了他极度无聊的永生:20岁的他变成了30岁的副所长,30岁的副所长变成了40岁的所长,40岁的所长变成了50岁的调研员。
警察艾国柱决定出走。
十年后,出走的警察艾国柱变成作家阿乙,而上述牌桌场景成为阿乙笔下最得心应手的小说内容。警察艾国柱在现实中不存在了,却在阿乙的作品里一次次出现:一个压抑的青年,在一个憋屈的地方,做着自己不喜欢的事,没有任何理由,就是不喜欢。不愿意就此虚度一生,盘算着走向外面世界的一切可能。
这一算就算了5年。当时的艾国柱计划着“走出镇,走到县,走到地级市,走到省会,走到直辖市,走到北京,走到纽约”。
5年里,艾国柱一次次尝试,到处找工作,却一次次被挫败。他想做体育记者,但别人对他说,你最适合去找的工作是保安。当他最后决定脱下警服,也理所当然地被家乡人骂作傻子,警察是一个铁饭碗,居然有人宁愿砸了铁饭碗去外面做一个临时工。
父亲也不站在他这一边,在父亲看来,“你在外面也没有什么用,你看人家像你这么大年纪的,30好几,人家都有家有事业,你有什么,你就是一个流浪汉”。
阿乙回忆起这些挫败,感觉“就像一只鸡,你在展翅飞翔的时候,飞到一定距离的时候掉下来了,然后天上的大雁、凤凰都飞远了,你又走回鸡窝去了,你那种挫败感,你那种失落感很难以形容,不会哭,但是你心里面非常难受,你觉得整个世界的井口又盖上了,你又在这里做青蛙”。
但当他最终成功出走,并拿起笔来创作小说时,那令人压抑的5年警察生涯,却成为他进入文学世界的最锋利的武器。他将做警察时的压抑感全部注入自己的小说中,而这种压抑感又为他赢得了不少读者的共鸣。
谁没有压抑过呢?
十年间,阿乙按照计划“走到了北京”,去不去纽约已经不那么放在心上。出走时只想做一个体育记者,几经周转,成了一名小说家。生活已经超出了想象。
谈及现实,一样的琐碎,该上班上班。普通青年阿乙说,“父母还是希望你结婚,这种希望会变得越来越唠叨,因为结婚要买房,买房又要背债,背债你要还债,因为还债你要上班,就是这么简单”。
谈及社会,阿乙承认自己没有做知识分子的情结,对政治冷漠,他只想写作,不危害、打扰他人。
谈及作品,文学青年阿乙总是对已完成的作品不满意,他觉得“我现在所有写的东西,没有一个我觉得到达我心目中那种价值的50%”。他最害怕的,是“丧失写作的独立权”。
谈及未来,他固然可以用调侃的语气去谈论诺贝尔文学奖,却没有掩饰留下传世作品的欲望。他希望“五十年以后,还有我的十篇小说在流传”。
十年过去,因砸掉警察饭碗而被家乡人骂作傻子的阿乙,今天已经可以用作品来回应。关于梦想,他说:“只要那个东西在心里不死,只要你活得够长,就肯定会实现”。
对话主持:谭不 周东旭
对话实录:
阿乙:放弃警察工作大家都说我是傻子
凤凰网:几天前看到《江西日报》的一条新闻,记者是这么写的,说近日从瑞昌有关部门了解到,瑞昌籍作家阿乙正在角逐华语传媒文学大奖。这个说明瑞昌那个地方有人以你为荣。
阿乙:我觉得有关部门可能是我爸爸。他现在中风了,身体特别不好,多看一些我的好消息对他的身体好。
凤凰网:他会给你做各种各样的剪报吗?
阿乙:没有,都是我打电话告诉他,我最近有什么可能获奖,或者是我最近要去哪,或者作品在哪发表,不停地给他一些惊喜,因为我觉得他挺难的。半分钟可能走10米或者20米那样子,特别慢,整个手是残废的,右腿也是知觉有一点问题,就靠左腿拖着右腿走,他现在整个生活需要一些兴奋剂,所以我经常会给他一些,他肯定是感到有一点光荣,因为我出来混了。
我2002年不要警察的工作,从县城跑出来,大家都说我是傻子。一直到2010年,整个8年,我一直在郑州、上海、广州,最后跑到北京来,跑了很多地方,又没有存款,又没有房子,又有没有车子,又有没有媳妇。我一回家过年就烦,因为老同学或者是朋友他就会问你,你有车吗,你有房吗,你老婆哪的人,我说我三大件都不齐,总之他们就觉得很我傻。
我父亲的压力也很大,天天说你在外面也没有什么用,你看人家像你这么大年纪的,30好几,人家都有家有事业,你有什么,你就是一个流浪汉。我这两年才出来一些书、发表一些小说,包括获了两三个奖。我们当地那个县城,逐渐意识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一天找我去采访,我们老家人,他们没人读我的小说,也没人知道我写了什么,但上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他们来说那可能是一个县委书记,或者是县长才有资格的事情。他觉得这个还蛮不错的。
阿乙:你往下走,就是世界尽头
凤凰网:当你从警察岗位出来的时候,你父亲和你都没有想过你会成为一个作家?
阿乙:我当时的理想是做一个体育记者,因为我从小就比较喜欢体育。我爸爸是一个乡镇的药店经理,那个时候我常去给他们到邮电所领报纸、领杂志,因为我爸爸的那个单位定了一份叫《新体育》的杂志,我从小就喜欢看那里面的图片,所以长大以后就很想做体育记者。
所以我当时就去应聘,应聘了很多单位,最后去了《郑州晚报》做体育编辑,当时没有想到要写作。因为我觉得,作家两个字,文学家三个字,这样的一个称呼,就像天上的星辰一样,可望而不可及。你想一下作家在我们心目中都是什么,都是海明威,或者都是托尔斯泰、莎士比亚,中国的就是老舍、茅盾、鲁迅。你说你去做一个作家,跟他们在一个序列里面,你都觉得这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所以当时根本不会想到要成为一个作家,只是想做一个体育记者,其实是做了9年的体育编辑,没做过1天记者。
凤凰网:你说了一个很重要的词,可望而不可及,是不是目标是可及的,你才去做?
阿乙:我一定会定一个我达不到的目标去实现。我的目标,有时候看起来也很不合实际,特别想当然。但是只要那个东西在心里不死,只要你活得够长就肯定会实现。我现在36岁,我印象很深的是,我从警校毕业,分到我们那个乡村派出所。那个地方你再往下走,是没有地方可走的,就是你到了一个乡下,到了一个村,到一个村小组,村小组往下没有单位的,你在那个乡里面,你所在的就是一个小组,你往下走,就是世界尽头,没有办法往下走。但是你往上走有很大的空间,你可以走出镇,可以走到县,走到地级市,走到省会,走到直辖市,走到北京,走到纽约,你还可以去火星。
那个地方特别无聊,待不下去,憋死了。然后就立下一个愿望,要沿着那个路线,从那个乡镇派出所,要走出镇,走到县,走到省会,走到直辖市,走到北京,走到纽约。后来确实差不多是按照这个轨迹一路走过来的,其实是花了我现在这么多时间,其实差不多完成了。当年我在那个乡村里面,说我要去纽约,大家都觉得我是一个傻B。
凤凰网:小时候作文写的很好吗?
阿乙:写的不错,现在看来我不是什么文学家,但至少是个文学青年。我觉得有些想当然的东西,你今天可能达不到,但是有一二十年的时光,你就达到了,你不知道怎么就达到了,只要你心里有这个东西。
凤凰网:你在做警察的那几年里,是不是每天很晚都在计算,你离开之后怎么办,怎么办?想各种各样的路线图?
阿乙:我现在的生活都超出了我当时的想象。因为在那个地方就像坐牢一样。一个坐牢的人,对外面的天空,他会有很多想象。我在县城里面就会很酸楚地想,我未来如果在一个大城市,我应该怎么生活,我能想到的其实非常有限。

作家阿乙接受凤凰网对话。周东旭/摄
阿乙:外面不接受我时很挫败
凤凰网:你在做警察的那段时间里,你不想干,但你在那待了好几年,最大的牵绊是什么?
阿乙:我们家乡人说我是傻子,觉得我把这个铁饭碗扔了,其实我从一开始接受那个岗位的时候,我就不觉得它有多金贵,也没有多么重要,想舍弃随时都可以舍弃,因为这个东西我不喜欢,不喜欢的东西,你拿在手上没意思,就像你跟一个不喜欢的女人,你跟她生活一辈子是非常痛苦的。
为什么拖了?1997年到2002年,拖了5年才出门,才离开县城,就是因为外面不接受我,因为我的实力很差。21世纪的三件武器:英文,我二级都没过吧,好像是;计算机,2001年我才学会电脑;驾照,当年有过一阵驾照,开车的时候差点出事故,后来再也不开了,把驾照也扔了,什么都不会。我应聘的时候去天津、去南昌,就发现整个招聘现场,都是像你(指笔者)一样的,戴眼镜,都是有文化,有知识的,全是这样的,我眼睛1.5或者是1.2,我一点文化都没有,眼睛那么好,干吗呢?我就觉得很自卑,因为他们至少都是本科,还有硕士、博士都找不到工作,能轮到我?
有的单位招聘很不人道,他不管你多远,打个电话说你过来或者什么样的,你来吧。我以为来就是我来上班,结果发现除了我,有500多号人挤在一个大厅里,领那个什么,招聘表,一个个面试,面试的时候我一个人坐在这边,那边一下坐了十几个,不知道从哪来了,都是老教授什么了,问我一些问题,我早就已经溃败了,就想回家。
因为我的学历很低,只是一个大专文凭,而且我做的是警察。有一个我去应聘的单位跟我说,你最好做保安。我就想,我好歹也是穿正规制服的,做一个保安。当时觉得很受打击,但是后来我一想,你学的这个专业叫治安管理专业,你到哪儿去呢?你不会玩电脑,你不会玩这个,不会玩那个,所以当时就很挫败。
凤凰网:你当时找工作的时候,警察那份工作已经辞掉了吗?
阿乙:没有,哪有那样的,我肯定是稳重的。我去《郑州晚报》说起来是我不要工作,其实我是在那边试了差不多了,才痛下决心。公安局那边还蛮好的,说你还是考虑清楚回来,这个毕竟是有长稳的工作,那边只是一个临时工而已,你没有编制等于什么都没有,我说我根本不在乎编制什么东西,我宁可老死在外面。其实是给自己打气,因为你的退路全部都没了,后来他们就把我直接弄成一个自动离职,就没有后路了。那几年工作特别努力,生怕工作表现不好,万一被开除了或者是被辞退了,回也回不去,你在外面生活也没有房子,你也没有来源,怎么办呢,所以那几年的工作特别努力。一个东西一定要做到部门里面最好的,一定会把版面做到我心目中认为是很漂亮的,包括文字编辑,会做得很认真,很细致,做到都有强迫症,尽量让自己少犯错。有时候半夜里,突然会做噩梦醒来,觉得自己做的版,哪个地方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错误,大标题的比分是2:0,里边的比分是2:1,就会出现这种噩梦,因为那个时候职业精神很可嘉,不像现在这样吊儿郎当的,我爱上班就上班,现在职业精神下降了。
凤凰网:你之前在寻找出路的时候,你并没有瞒着你的家人、同事?
阿乙:我家里人都知道,其实我都想瞒,单位肯定是瞒的,家里的人肯定是知道的。我爸爸每天回来,我就跟他聊会天,然后我就看看电视睡觉,就是过这种生活。我的一举一动他们都知道,我要出个门,他们肯定就会说,他们就会知道你要去干吗,我不能说,我在外面有个女朋友,这是不存在的,所以我就会跟他明说。我父亲他非常希望我在当地从政,因为当时在公安局以后,就借调到县委组织部,其实叫市委组织部,是个县级市,我就不好意思提它是一个市了。
当时的那个情况还蛮好的,很可能隔一年就会调到九江市去上班,当时我觉得我这种性格和这种能耐,根本不适合从政,我不喜欢再继续做公务员。然后我就想做记者,做体育记者,有招聘信息,我都去投简历试一下,那个时候写了很多球评,就把这个当做我的资历,就这样有一些机会出门。我父亲就嘲讽,你看你这种文化,你这种水平,不是我说,你怎么能成功呢。
但是每次我走的时候,他可能都会很忧伤,觉得他不能再控制我了,所以他也很害怕我,一旦去了就不回来了,但是每次回来的时候,我就看到他对我笑,那个笑里面有很亲密的父子之间的那种溺爱,但是那个眼光里又有嘲讽,深刻的嘲讽。一看,你还是回来了,乖乖地回来吧。那个时候我看他眼光的时候非常挫败,因为我每次出门的时候,都是选择早上,朝着太阳行进。我每次回家的时候,恰好都是夕阳要落尽的时候。站在那里,快要天黑的时候,你看着父亲的眼光,略带嘲讽的那种欢迎,欢迎你回家,欢迎你铩羽而归,那个是读sha吗?
凤凰网:铩羽。
阿乙:对,欢迎你铩羽而归。没办法,晚上看到母亲,把你的被窝掖得好好的,给你煮好吃的,然后你就觉得,你就像一只鸡,你在展翅飞翔的时候,飞到一定距离的时候掉下来了,然后天上的大雁、凤凰都飞远了,你又走回鸡窝去了,你那种挫败感,你那种失落感很难以形容,就不会哭,但是你心里面非常难受,你觉得整个世界的井口又盖上了,你又在这里做青蛙。
凤凰网:也就是说你从警察岗位出来以后很多年后,你还是觉得自己没有成功到足以让父亲肯定?
阿乙:没有。我的父亲其实对我的一生,没有一个正面和肯定的评价,他对我的评价,当然他认为是一个好孩子,这是他的一个策略:他要让我永远知道,他对我不满意,他就这样鞭策我,我做得再好,他也会说这个地方有毛病。所以我的性格到现在,其实已经养成了这种性格,我对我自己的作品其实是非常不满意的,我现在所有写的东西,没有一个我觉得到达我心目中那种价值的50%。

作家阿乙接受凤凰网对话。周东旭/摄
阿乙:写作是因为我对地表上的东西很有感触
凤凰网:你决定要写作,是对自己之前的那种状态不满意,所以才去通过写作来建立自己吗?
阿乙:我是这么想的,因为我把体育界做厌了。
凤凰网:厌到什么程度?
阿乙:我觉得像中国足球,我做中国足球编辑做了很多年,来来回回换一个主席,不就是那么回事吗,换了阎世铎的时候是那么回事,到了别人还是那么回事,你看最近不是又有人做了吗,都是一回事,然后搞得国家队都不出线,包括某个具体的运动员违规,怎么处理,最后怎么从轻发落都是一样的,包括怎么后来踢假球,你会发现这个圈子在不停地循环往复,极其肮脏,极其没意思,然后你每天还在那,怀着你的理想主义,给他们做这些事情。我就觉得没意思。
我头几年做报纸版面的时候,会把版样给收藏起来,或者是把报纸收藏起来,你看这上面编辑艾国柱(阿乙原名),校对是谁谁谁,你看这就是我的作品。但是回头我发现,在公交车,还有各种交通工具上,人家看报纸的时候,一看是昨天的报纸马上就扔了,所以我后来就在想,我其实在每个版面上花了很多心血,基本上把它当成一个艺术品去做,但报纸的那个东西,结束得特别地迅速。就像冰棍一样的,当天吃,第二天再吃就化了,或者是一个水果,第二天就腐烂了,它是有保质期的,报纸的保质期顶多就是一天。所以用做十年作品的决心,去做一天的版样,我觉得就这的很划不来。什么东西能让你的东西更长远,就是写作,甚至不是写专栏,就是写作,写小说,写诗歌。我曾经优先去写诗歌,我写了大概一年多诗歌,写得我自己还觉得还蛮好的,现在看来,就跟流行歌词差不多。
凤凰网:当时会拿给别人看吗?
阿乙:我不会拿给别人看,我当时就是自己在那里摸索。其实我读诗读得特别多,后来我看到一个人比我小,我是1976年的,人家是1983年的,小这么多,他写的诗我看了一下,自惭形秽,从此就断了写诗,觉得我不是那块材料。
凤凰网:你就觉得这条路走不通了,你就不走了。
阿乙:诗歌是那种很清高,很干净,很透彻的东西,(诗人)灵魂里面没有渣滓,像孩子一样的,他们可能在高空中飞翔,而我是对地表上的东西很有感触,这个跟小说很吻合。后来我才写小说,比如说我对警察抓小偷,我奶奶和我妈妈长达几十年的婆媳战争,我对这些东西很熟悉,很敏感,写诗歌挫败了转向写小说。
凤凰网:写小说从来没有挫败过?
阿乙:挫败啊。
凤凰网:第一次写小说是什么时候?
阿乙:应该在2006年就开始写了。2006年在北京,30岁,然后在2008年开始认真写,其实2006年到2008年这个阶段一直在试验摸索,然后饱受打击。
凤凰网:哪方面的打击?
阿乙:比如说我把这个作品贴到论坛里头去,被很多人嘲讽。我也不好意思去直接投稿。
凤凰网:什么论坛?
阿乙:到处都有文学论坛,那时候有的,反正我都会贴。我觉得有一帮傻B就是这样的,喜欢通过嘲笑别人来建立自己的优越感,其实我觉得这些人大多数不过尔尔。真的厉害的人,他根本没有工夫来嘲笑你。我在那一块受到了很多打击,那个时候之所以没有被打击死,我还是自己知道,我心里面还是有分寸的。我看很多外国小说,我知道有一些大师,他写的小说,有好的小说里也有差的小说,我写的东西并不见得就比他差的小说差。
阿乙:警察生涯有质感 城里人摸不透
凤凰网:现在反过来看,你做警察的这段经历,对你后面的写作还是很有帮助的?
阿乙:我当年很讨厌做警察,因为我不适合做警察,我比较瘦弱,觉得警察也没什么,在社会上有面子,但是我自己不喜欢,不过后来就发现有所失就必有所得。我喜欢做体育,我做了9年体育编辑以后,发现这9年里的生活就像一块没有多少矿产资源的矿,怎么去开发它,都写不出来什么东西,但是警察生涯我只做了5年,我就觉得那个生活特别有质感。就像你看片子也是一样的,你看一部中国喜剧片或者是家庭生活片,可能你不感兴趣,但是你放一个片子,是美国的西部片,你会突然觉得特别有质感,因为那个东西,那个空气,包括那个景色,包括人的那种性格,都会很极端,在你的心中会突然显现出来。但是你在一个筒子楼里头,或者在一个写字楼里头,你就很难想象。人的性格在写字楼里很难显现,在写字楼里很少看到凶杀案,在派出所里面,你看到进来一个人血淋淋的,你说一个血淋淋的人有小说质感,还是一个白领的人有?白领都像在韩国整过容一样,连笑容都是一样的。
我觉得可能跟电视文化有关,电视上有一些明星,有一些政要,或者有一些公众人物,他在慢慢地使一种标准统一化。这些统一化的东西,会慢慢侵蚀到白领身上,白领穿衣服,就逐渐地像吴彦祖,或者是像陈道明,简约而不简单,慢慢就靠拢了。大家的风格都差不多,一身西服,一件衬衫。你看不到一些像你在派出所看到的,特别棱角分明的人,他们穿的是什么东西,他穿的衣服上的每一个细节,都显现他这个人的收入水平,他老婆是不是跟他离婚了,所有的细节都在证明他的性格。后来写小说的时候,经常会回到那个时候。因为那块你觉得有东西可抓,后来在城市里面你抓不准,摸不透城市人的心。
凤凰网:但你未来写作的生涯还很长,警察生涯的体验写完了怎么办?
阿乙:我现在一直在试图摆脱小众作家,老是想摆脱那种小众的写作范围,范围扩大写到省会城市,就发现有危险。就是我刚才说的,捕捉不了,我对城市的建筑物,我没有那种敏感。对空调,对桌面的上的这些东西都没有敏感,但是如果一到乡下或者是小镇里面,那些东西我只要看一眼,我就敏感,我知道它那个桌子,为什么椅子摸了很多槽,为什么有蚂蚁走,为什么下午的时光那么慵懒,显得特别无聊,人为什么会在冬天里烧煤球,为什么下雪。在城市里,这些东西我都感触不了,我不知道为什么。
凤凰网:怎么办呢?
阿乙:还是退回去。可能以前有些素材用光了,其实还是有很多资源,慢慢去细挖还是有的。像我一直避免去写亲人,以后是不是也要写一点点。我的很多亲属有故事,有到50多岁还离婚,去投奔爱情,到最后也比较凄凉的,也有那种发誓要去上海,成为一个悲剧的人也有。还有我爸爸自己,奋斗了一生,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中风了,我想写一个关于他的。
我写小说,以前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我有情感在里头。我的情感不会写出来,但是在我的字里头会有。因为我当时在小镇老是想跑,那种压抑感很强,所以我写小镇的时候,压抑感会带进去。看到我作品的人会说,里面有那种压抑感出来,就是因为我自己一写到那一段回忆的时候就很压抑。
后来一旦离开那个小镇或者是县城的时候,那种压抑感就不存在了,那种情感其实是丢失了。以后可能会写你我旁边的情感,那种情感如果带进来了,即便写一个遥远的故事,可能也会很好。比如说我要在《当代》发一个小说,叫《阁楼》,讲了一个白骨案。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叫慈溪白骨案,我是去浙江出差,有一个是我的读者就跟我讲了,他说他有一个熟人,就是杀人犯,是一个瘦小的,1米5几的女人。
她母亲有一天在打扫发生的时候打开阁楼,发现里面有尸骨。她母亲以为是动物尸骨,就打电话给她,她当时不知道怎么没接,又打电话给她哥哥,她哥哥也没接,她母亲就跑到派出所报案了,派出所一来,就发现这是人的尸骨,然后发现尸骨旁边还有西服,西服里还搜出名片,名片就是什么副厂长,名片上的人就是这个女人的初恋男友。到最后把那个女的叫去一问,原来这个男人10年前就被女人给杀掉了。为什么杀掉,因为这个男人,就是这个死者威胁她,说你跟别人去拍婚纱照了,你是我的老婆,还是别人的老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然后她就被纠缠的不行,最后就杀了,杀了以后把他放在阁楼里头锁起来。
有两个细节蛮好玩的,为什么10年,臭味没人知道?她家旁边就有一条臭水沟,臭水沟特别臭,就掩盖了,到事后出来以后,大家才议论,就说怪不得这些年这么臭,其实大家就是马后炮。还有一点就是问10年以后,为什么这个女人不把这个尸骨给移走,为什么一直放在这儿?这个就没有讲。后来我去不停地研究这个原因,我才知道,这个女人从来不会骑自行车。你就想她不会骑自行车,她也不会骑电瓶车,也不会骑摩托车,她什么交通工具都不会,她就没办法办这种事情,她需要一个交通工具,这个又不能找别人帮助,所以一直放在阁楼上,而在她出嫁以后,她每天中午回到这个家里来吃饭,回到她老娘这里来吃饭,这是一个很悬疑的故事。
到最后的时候,为什么要杀这个男人,就是因为这个男人纠缠她很深,肯定是这样的,两个人是恋爱关系,你跟别人去拍了婚纱照,你视我为何物,被男人纠缠,然后她就把这个男人杀了。但是为什么杀这个男人,后来我一直在想一个谜底,这个女人她母亲是一个中学校长,然后是她母亲介绍的,还是谁给她介绍的,拍婚纱照的老公,是一个干部,这样是门当户对的,她自己也是一个有正式工作的人,而她这个初恋男友是个农业户口。你注意这四个字农业户口,你就想一下,从她很小就要商品粮,就是城镇户口和农业户口的事情,我想到这个地方就特别忧伤,这里面带着我的情感。
我的母亲是个农业户口。所以在高三以前,我一直是农业户口,敏感到让人羞耻。就像一个黑人,他没办法向一个白人姑娘求爱。一个黑人对一个白人的谦卑,就是一个农业户口对城镇户口的谦卑,它会让你心里充满压抑和羞耻。
比如说一个黑人和一个白人,两个年轻人从小在一个地方长大,然后黑人考上了纽约某个学校,然后那个姑娘还在农场里面,不知道干吗,就跟过去的生活一样,她反而受了一点欺负。然后这个黑人拿着一大束鲜花回来,向这个白人姑娘求爱,这个黑人以为他已经获得了某种资格,有资格爱这个白人姑娘,而那个白人姑娘还是一样的。根本不可能,根本不可能喜欢你,也不可能接受你,这是一种固有的,只有在中国会出现这种户口文化,就是户口性格。所以我能体验到,为什么那个姑娘会在男人纠缠她、质问她的那个晚上会行凶,解决掉她的初恋男友。
她也有羞耻感,她不能说我接受你这个农业户口,你是个退伍军人,你是一个农业户口,然后我跟父母说,每个同学都是要么嫁给一个政府的干部,要么嫁给一个当地的工商局、税务局或者银行的,只有我嫁给一个农业户口的,我羞耻,所以她就动了刀子,我是这么理解。我心里面竟然为这个女人哭,也在为那个男人哭,全他妈是为了当年的户籍制度哭,有羞耻的情感在里头。我为什么会羞耻,就是因为这个东西深深地陪伴我,从很小的年纪到高三,我始终就活在“大家都是世袭贵族”的圈子里头。
我的母亲很谦卑,因为她是一个农业户口,她很谦卑。她觉得是她祸害了我们这些子女,觉得她自己没用。为什么是她没用,她出生的时候,她也不知道她是这个样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一直想不清楚。曾经有那段时间,是可以买商品户口的,我就有点愤怒。我身上有比较强硬的一点,就是我觉得羞耻的东西,我宁可它在我身上。我是一个大专文凭,我就是一个破警察,出来做保安就做保安,这些东西我也不会去弄一个什么文凭,或者弄一个本科,或者弄一个什么,这种东西我从来不要。
我当时在派出所办户口的时候,那些人来我这儿办农转非,欢天喜地,一种土鸡变凤凰的快感,在他全身洋溢起来。我也很忧伤。

作家阿乙接受凤凰网对话。周东旭/摄
阿乙:我们活着就是一种幻觉
凤凰网:你提到的这个例子里,新闻报道已经很翔实了,给小说的空间在哪儿?
阿乙:我很少看到一篇报道,是从这个人出发。大家很可能是从某项制度出发,从公众出发,很多新闻是这样的,它并不见得是从单个的人出发,而是从这个事件会不会对公众产生危害,这个角度出发,很少会关注到个人的事。
凤凰网:你本身讨厌户籍制度,在写小说的时候,会不会把它写得很可恨。
阿乙:不会,我写东西不是为了去骂某些东西,我只是把这个东西讲出来,讲这个东西它就是这回事儿。我小说的任务不是要探讨户籍制度是怎么来的,怎么结束的,怎么发展的,不会探讨这些东西,我的探讨就是为什么这个人,因为户籍制度,他会遭遇这种事情,为什么被人给碎尸。
凤凰网:你背后的表达,仍然是一种情感的表达。
阿乙:对。
凤凰网:你需要通过这个作品来宣泄你的内心?
阿乙:写一个人的时候,你必须要对他的命运进行展示,我展示的不是户籍制度它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我展示的是一个农业户口他的命运。
凤凰网:说到命运,就感觉到你写的很多作品里头,人物一直在反抗命运的安排,最终往往失败,很宿命。
阿乙:对。
凤凰网:你自己也在反抗,但是现实中可能没有那么绝望。
阿乙:我没有那么绝望。但是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活着就是一种幻觉,我们现在在这儿对话,我看到你,你看到我,都是真实存在的,我会觉得你是一个永恒,我也是一个永恒,就觉得这个茶水什么都是永恒,只是因为我们活着。但是有时候我会想,我们活着其实是一个幻觉,死才是真实。我走在路上就会想,这个地底下埋了多少死去的人,他们在整个人类历史的长河里面,5000年或者是上亿年里面,他们所占有的不过是60年的时光、80年的时光,很小的一部分。剩下的所有历史都跟他没关系。所有的剩下的这些,对他来说都是黑暗,午夜一样。
我们从1970年代出生,到2020年代或者2040年代我们病故,剩下的所有时间,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片黑暗,关我们屁事。大部分的人是很绝望的,你只有这一生,马上就走完了,走完了你就没有了,没有了你不会留下名字,什么都不会留恋,也没有人祭奠你,就这么简单。基本的事实就是这样。我写《意外杀人事件》,就是因为我们当地县城里面发生的一起这样的命案。我们那个县城里面特别好玩就在这里,一个人死是因为他实在是病得不行了,他老得不行了,该死了,他拖了很久才死,大家觉得他的死就是很正常的,大家都觉得自己不会死,因为你每天看到的人都是活人,你每天吃饭都吃饱了,你也有事情做,打打牌。
好像从原始社会,你们就一直这么生活,还会往下生活一千年,你不会觉得周围有死。偶尔有些送葬的,你觉得这个人是该死的,因为他拖了好多年,90岁或者80岁死的,大家都觉得自己是一个永恒的。有一天。就在我们的县城里面,有一个火车经过,有一个人在火车上得了旅途精神病,他跳车,跳下来没摔坏,走到县城里面,好像又发作了,弄了一把水果刀,不管是谁,一路刺过来,就在一条主干道上,刺了7个人。这7个人有好多都死掉了,我到医院还看到了,死的人都是被直接插心脏要害,跟没死一样的,眼睛这么挺着的。
整个县城一片慌乱,跟敌军入侵一样。这个人用一把水果刀,等于把所有县城的人都弄得一下子明白了真相:人原来是会死的,即使你可以把它归咎于意外。这7个死者有更多的可能性是不会死的,比如说有的人在出发之前他是来讨债的,他讨了以后,那个人说你等一等,我去借钱给你,比如说借个300、500给你一点钱,结果他就没有等,他就直接走到街上来了。如果他等一下呢,他不就死不了吗。或者他走到公共厕所,他不进那个公共厕所,不上那个厕所,直接走,不就走过去了,还上那个厕所,一出来,正好碰见了,结果呢。
那一段时间整个县城的人都是人心惶惶,大家晚上很早就会回家,街道上也没有人,很早就把小孩带回家,然后把门关上。整个县城的人被这一个精神病给提醒了,是极度荒谬的一件事情,但是大家一下变的特别透彻,就知道人是会有死这种事情的,不会活得懒洋洋的。那天晚上大家都是拼命发誓,我也在拼命发誓,找到自己的女人,就是当时的女朋友就说,会爱你一生一世,要守护你,不让你受到这种残害,要保护你。
大多数人在县城,那天晚上都是这样的,都是抱着自己的妻儿,害怕又有这样的事情。但是隔了一两个礼拜之后,这种惶恐慢慢散去了,恢复正常以后,大家又开始在那种活在幻觉中。就是我所说的活在幻觉中,大家又忘记自己会死。我不是要提醒大家会死,我只是觉得死这个东西是永远存在的,你到了60岁、80岁,你没有意外的话,你也会死的。
凤凰网:你觉得小说家的责任,就是要把幻象弄破灭掉吗?
阿乙:不能这样说的,每个人有他自己的思考方式,我只是把我所想到的东西写出来而已。

作家阿乙接受凤凰网对话。周东旭/摄
阿乙:我很害怕丧失写作的独立权
凤凰网:你认真地去想过写作是为了什么吗?
阿乙:我从来没有认为我写作是为什么人服务,也不是为了什么人道主义服务。我觉得你一旦写作,你要是为了某一个东西去写,无论这个东西是多么正义,多么伟大,我觉得这个写作肯定是可疑的,意味着你丧失了对写作的自主权。你就变成了一个,说白了,就是跟餐馆的服务员是没有区别的人。我为了环境保护主义写这个东西,那不就是说人家要点这个菜,你把这个菜端过来吗?那样的话你会丧失你的自主权。
凤凰网:你会有意识不去取悦任何人?
阿乙:其实很难办得到,但是这个东西要警惕。写作的话,你不能完全取悦你的读者,但你的文本是要跟读者交流的,而不永远是给自己看的。在给读者看的过程中,交流过程中,必然有些东西你是要丧失的。但是我老是警戒自己,不要去取悦,我很害怕丧失了写作的那种独立权,我很害怕变成了一个为别人写作的人。来回拿捏这个度。
凤凰网:刚刚听你谈了这么久,像死亡、绝望或者出身卑微,这样的一些主题,你觉得这可能是你的写作生涯中一个永恒的主题,还是只是暂时的,今后会不会有变化?
阿乙:其实我这几年里的写作,充满了各种尝试。但是大家就觉得这个人写东西怎么这么灰暗。可能是有一种习惯性的东西在里头,不知道是好是坏。写温暖、写幸福的难度非常之大,写悲伤和痛苦,就像我这种成就不大的,或者是能力不够的人,写起来就会得心应手。因为好写,有质感,有东西可写。比如我写晚上非常痛苦,我听到每个声音都在嘲讽我。火车开走了,肯定就是把我遗弃在这儿了,把我的爱人带走了。或者是听到什么声音,母亲的声音,怎么这么烦,整个你都能感受得到。但是幸福,你会怎么写?我爱你,我好幸福,我们生个孩子吧,我们吻了又吻,吻了又吻,然后我们幸福地生活下去。几句话你就讲完了,有什么好写的。
凤凰网:你未来是不是打算做个全职作家。
阿乙:你总是要做别的事情,你会分心。
凤凰网:你换了很多份工作,你有压力。
阿乙:其实是来自父母的要求。因为他还是希望你结婚,这种希望会变得越来越唠叨,因为结婚要买房,买房又要背债,背债你要还债,因为还债你要上班,就是这么简单。所以我现在在积攒收入。未来比如说一两年就不用考虑还债这个事情,基本的生活费也有,再考虑买自己两年,可能也只是赎回来一年左右(用来全职写作)。我今年不知道会不会辞职,应该不会辞。
凤凰网:你以后还是打算写长篇为主吗?长篇确实比短篇好卖一些。
阿乙:我不知道,我写东西是这样的,我不会考虑它的销量,我是考虑这个故事合理强度。
阿乙:大部分的读者其实是容易被操纵的
凤凰网:你觉得你的读者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阿乙:我不知道,大部分的读者其实是容易被操纵的。
凤凰网:被什么操纵?
阿乙:被一些概念操纵了。有人我这个小说是存在主义,有人定位我是侦探悬疑小说作家,我觉得读者是容易被操纵的,因为现在的媒体环境就是这样的,就是把一个复杂的事情简单化,让你为几个标签努力。我写作的时候,我是喜欢把一个作品当成工艺品、艺术品。我始终最渴望的一种写作状态是,我写出来的作品没有一句废话。
凤凰网:你会去网上看读者对作品的评价吗?你的新书可能比上一本所受到的非议多一点,你自己的心态有什么变化?
阿乙:我就在网上生活,我怎么不看呢。但心态没有变化。我很少为自己的作品做很多辩护。
凤凰网:看到批评之后会有什么反应?
阿乙:起初的时候会看到一些不好的评价你就觉得想跟他理论一番,后来算了。批评有些地方合理,把我当年有一些偷懒的地方指出来,我就想以后去再版的时候,我就把它改过来,没有再版的时候我自己也会把它再修改一遍,到时候就打印一份给一个人就行了。《下面我该干些什么》这本书里面,存在有一些漏洞,最后有很多人提的意见,我觉得很对,就是说它到后面的部分语言已经不合乎小孩的身份。
凤凰网:你在微博上,还推荐了网上的一个读者对你的批评。
阿乙:那个人跟我说了,他说他看不惯封面上的那些营销的词语。其实我读书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这些东西我自己也不喜欢。
凤凰网:作品封面被包装,你会觉得跟你初衷不太一样。
阿乙:我不太在乎这个事情。我在图书公司上班以后我就知道,一万册的书,这个图书公司也赚不了几百块钱,何苦呢?你不能说这个出版公司老是用腰封来吸引你,问题是如果什么都不做,连几百块钱都赚不了,到最后亏了几千块,他有意思吗?他的公司就要破产了,真的很难的一件事情,特别是民营出版公司,所以我一听到他的做书利润这么低,我就在想,为什么当时他还在做书,为什么不直接做房地产算了。
凤凰网:你在微博上挺活跃的,但是好像很少看到你参与一些所谓的公众话题的讨论。
阿乙:我是这样的,没有公众性。我是这样的,我喜欢研究自己的一块领域的一个中心,我喜欢自己写作。我的目标很简单,当然写作上也有野心。
凤凰网:没有做知识分子的情结。
阿乙:没有,一点都没有。
凤凰网:不关心政治,不关心这个世界上所谓大的事情?
阿乙:不关心,而且特别冷漠。
凤凰网:冷漠?
阿乙:对,非洲人现在还在饿死呢,我们在谈话的时候的就饿死了三个儿童,我猜的,或者某个地方正好在什么有三个人触电死了,我一点都不流眼泪,就是冷漠。比如说我们正在谈话的时候,飞机掉到太平洋去了,也没见到我流眼泪,这个事情是冷漠的。我觉得有很多事情太过多情,反而伪善,我是这么觉得的。否则你从见面开始,每一秒钟都有10个人在死,每一秒钟都要哭十次,都是我们人类,那怎么办呢?那你就哭吧,哭不完的,所以我就希望我自己以后也是做这种人的,我尽量不危害别人,尽量我不去影响(打扰)别人。

作家阿乙接受凤凰网对话。周东旭/摄
阿乙:我希望50年后还有我的作品在流传
凤凰网:你对茅盾文学奖有渴望吗?
阿乙:其实我对奖里边没有特深的那个,我对奖的渴望来自于对金钱,比如说我知道诺贝尔奖好像是有1000万美金。
凤凰网:100多万美金。
阿乙:那就是1000万人民币,我是这么算的,如果我拿了诺贝尔奖,就是做一个梦,就是拿了以后,我就可以马上把房子,我现在的房子你知道是什么,大开间,一居的大开间,然后来一个亲人就没法住。我就想买一个别墅,联排的别墅。
凤凰网:1000万,联排的恐怕也买不上。
阿乙:没事,你到时候拿这个奖,走几个台就行了,你再忽悠一千万进来,比如说你做老板吧,我给你代言,你生产一个什么不害老百姓的药给你代言,然后上了那个平台之后,诺贝尔瓷砖什么什么的。然后就那个你给我1000万,然后买个别墅,岳父岳母、爸爸妈妈都住在一起,从此也尽了对你们的孝心了,让我自己又多了些舒服,否则我总是欠他们的,不忠不孝的。每天看到老爸身体那样的,你说我怎么办,我又不能很好地照顾他。其实有时候想有钱还是好事,但是写作又不是为了钱,要是真为了钱的话,我可能早几年前就可以动手了,去钻研一下畅销书是怎么写的。
凤凰网:如果抛开得奖不说,你未来写作上的野心在哪?
阿乙:我想五十年以后,还有我的十篇小说在流传。比如说,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之类,到现在20年。刘心武的《班主任》,过七八年以后,就下去了。如果有一篇到了100年以后(还在流传),我就觉得我很光荣了。我有恐惧,就是因为我总是想着我们那个县里面,从古到今,一个名人都没有。我不是说我想当名人,就是一点可留下的东西都没有,没有留下的任何文艺上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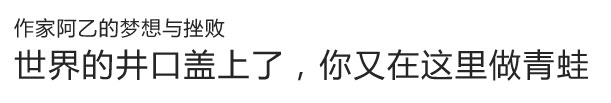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凤凰网保持中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