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 报人 一书生
2014年05月22日 05:29
来源:北京青年报
会议刚结束,我就收到罗孚先生的小儿子海雷兄发给我的一个短讯:“父亲已经在今天早上平静离开我们,特此敬告各亲友。罗海雷”。阅毕这个噩耗,顿感震惊万分。这位多灾多难的老作家、老报人,这几年来虽因病渐至孱弱,却以顽强的生命力“扛住”。他的老友们一个个零落而去,但他在家人的悉心照顾下,依然与病魔抗争着。上海学林出版社的周清霖兄等一批武侠文学界的朋友们本想在五月十日专程来探望罗先生,不料竟也不能如愿。这对大家而言,都是一个难于排解的痛惜与遗憾。
原标题:作家 报人 一书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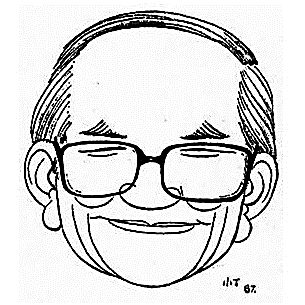

◎孙立川(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编辑)
罗孚,原名罗承勋,1921年生于广西桂林,香港资深报人。1971年,罗孚在桂林加入《大公报》后,先后在桂林、重庆、香港三地《大公报》工作,曾任香港《大公报》属下《新晚报》总编辑。2014年5月2日,罗孚在香港病逝,享年93岁。
五月二日上午,我们在《大公报》开会,商量藉《大公报》成立112周年报庆,举办一场纪念新武侠文学诞生六十周年的论坛,邀请两岸四地的武侠文学研究者、文学界朋友坐與“论剑”。席间,我们自然谈到了罗孚—这位被誉为“新武侠文学的‘催生婆’”的《大公报》老报人罗承勋。要不是因为他缠病在身,应邀他来出席这场讲座,他是当之无愧的“盟主”。
会议刚结束,我就收到罗孚先生的小儿子海雷兄发给我的一个短讯:“父亲已经在今天早上平静离开我们,特此敬告各亲友。罗海雷”。阅毕这个噩耗,顿感震惊万分。这位多灾多难的老作家、老报人,这几年来虽因病渐至孱弱,却以顽强的生命力“扛住”。他的老友们一个个零落而去,但他在家人的悉心照顾下,依然与病魔抗争着。上海学林出版社的周清霖兄等一批武侠文学界的朋友们本想在五月十日专程来探望罗先生,不料竟也不能如愿。这对大家而言,都是一个难于排解的痛惜与遗憾。
海雷兄后来告诉我,罗先生是五月一日中午离开医院的,出院前医生又为他做了检查,认为他可以回家了。也许是他想回家了,五一节是假日,劳累了一生的他也到了该好好休息的时候。晚上,他安然入睡,于凌晨在睡眠中平静地逝世,没有痛苦,没有惜别,永远地安息在他所热爱的“岛居”的香江之畔。虽然,人终有一天要离开人世的,但这位九十三岁的老作家的逝去,仍然引起文坛的反响与震动。报刊、网路上有许多关于他的介绍与评论,虽然其中多有讹误与不确之传闻。
他将梁羽生“赶鸭子上架”,成就了新派武侠小说的传奇
罗孚先生早年即投身《大公报》,以青年才俊而成为报界后起之秀,1948年南来香港,在藏龙卧虎、人才荟萃的大公报系脱颖而出,他参与创办《新晚报》,后任总编辑,以“知识性”、“趣味性”为标榜,成为香港左派报纸的文化重镇。其作者与编辑都是一时之选的文化人,阵容鼎盛,最出名的有“唐宋金梁”,唐就是笔名“唐人”、以《金陵春梦》等小说闻名的严庆澍(今香港著名导演严浩的父亲);宋是笔名“宋乔”的周榆瑞;金是笔名“金庸”的查良镛;梁是笔名“梁羽生”的陈文统。
六十年前的一月中,澳门举行了一场香港武术界打擂台比赛,一时间各界议论纷纭。罗孚灵机一动,力促他的广西老乡陈文统写作武侠小说。陈文统素喜谈宫白羽、还珠楼主等旧武侠小说,每与对面而坐的查良镛对弈或聊天时,皆眉飞色舞,罗总编看在眼里。
要陈文统初试牛刀,又见他犹豫不决,罗孚遂来一个“赶鸭子上架”,先登一则预告:本报将于后天(一月廿日)正式发表武侠小说,云云。陈文统迫于无奈,遂以“梁羽生”之笔名创作了《龙虎斗京华》的新武侠小说,结果一炮而红,每日连载皆吸引读者无数。他亦越写越有劲头,遂又写作了《草莽英雄传》、《七剑下天山》等。
同时,陈文统又向罗孚推荐,说“小查”写武侠小说也是一大能手。于是,罗孚又找查良镛先生商谈,力促他亦投身创作。在梁羽生创作武侠小说一年半之后,金庸也以《书剑恩仇录》而鸣于武侠文学界,且一发而不可收也。可以说,“金梁”这二位武侠小说家,均因罗孚的“撺掇”而成就了一段传奇。
2001年11月27日,我陪梁羽生去参加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举办的“早期新武侠文学研讨会”时,梁羽生先生在演讲中指出:“我觉得新派武侠小说的兴起是由于历史原因加上机遇。机遇指‘吴陈比武’(注:香港太极拳派掌门人与白鹤拳掌门人在澳门打擂台之事),碰上罗孚的异想天开,抓机会准而正确;恰好他手下有梁羽生和金庸,其他人手下不一定有像此二人的……”这一段话可圈可点。
他被认作“新派武侠小说”的“催生婆”,却对赞歌迭起之风潮不以为然
然而,我始终认为,罗孚被人认作“新派武侠小说”的“催生婆”,却对武侠文学后来的大红大紫不想太过“沾光”。
在香港,他推动武侠文学开启了一个新路径,利用契机而有意外之结果,这不仅是梁、金始料之不及,也是他从来没有想过的。尤其是后来,数学家华罗庚、政治家邓小平、廖承志及蒋经国等,都喜读金庸或梁羽生的小说,不可谓不成功矣!但到了新武侠名震海内外,尤其是九十年代以后、新武侠文学如日中天之时,他又对此赞歌迭起之风潮不以为然。
他不仅以曲笔写出一些自己的真话,甚至不惜与金庸的研究家们进行笔战。他认为无论新武侠文学取得多大的成就,也不应与五四新文学的业绩相提并论。对有些人扬金抑梁也不苟同。
2004年中秋,梁羽生应广西师大邀请,去桂林接受该校颁予的名誉教授之荣衔,我陪梁羽生伉俪一齐去桂林,听说罗孚也同一航班回到桂林探亲访友,梁羽生夫妇都很高兴。不料出发前突听说罗孚先生改为下一班机才抵桂林,那一个航班又晚点。广西师大文学院的一批青年老师就与我在那里等了半天。
罗先生住下后就赶过来同我们见面。我问罗太怎么突然改了航班,她悄悄告诉我,说是梁羽生到桂林肯定场面很热闹,他还是避一避为好,是不想趁热闹之意。其实他对梁羽生有着很深厚的感情,将之引为文学上同道与知己,他对梁羽生在诗词、对联的造诣更是欣赏不已。
我记得2006年9月,天地图书有限公司成立三十周年之际,梁羽生应邀来港参加纪念活动。那一天,金庸、梁羽生与罗孚先后到来,这三位新武侠文学的老前辈多少年后第一次出席一个公开的活动并亲切交谈,温馨而又感人,忙煞了多少人手中的相机,这也是他们三位老人最后一次集体亮相于公众的视野之中。
此后不久,金庸邀请了罗孚夫妇、梁羽生夫妇及大公报的同事一齐吃饭。罗孚则相约在梁羽生返澳洲之前,由他做东也请各位一聚。为了此事,罗先生打了几次电话给我,要我居间代为联络、落实时间。
不料过不了几天,梁羽生先生突然中风入院,这一场充满期待的重聚就成了永远的遗憾。这不是一饭之恩的应酬,而是三位老报人的又一次握手言欢。如今罗孚先生又作古了,九十岁的金庸先生想起二位老友,情何以堪乎?
移居美国之前,他把所藏的四千册图书全部捐给了桂林老家及广西师大图书馆
罗先生长期主持《新晚报》,为人谦和有礼,海内外文学界、艺术界有众多朋友,可谓:往来皆鸿儒,谈笑无白丁。他是公认的收藏大家,尤喜近现代书画。他收藏的齐白石、黄宾虹、林风眠等大家的画作,都是佳品。要转让给公共博物馆等,从不漫天要价,有君子古风,与时下的为“钱”而收藏的风气决然相反。他将周作人的《知堂回想录》手稿无偿地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我也是此事的见证人之一。当年就是我与周蜜蜜陪同李荣德兄一行去见罗孚先生的。
罗先生对于书籍的热爱一点也不亚于那些文物书画,尤其是晚年或身体违和之时,他或罗太时常会打电话给我,开一张书单,让我帮他买书。
1996年年底,罗孚移居美国之前,他将所藏的四千册图书全部捐给了桂林老家及广西师大图书馆,彼时他已上了年纪,却还要亲自打包,找物流公司,自掏腰包将这些书送到内地去,除了那套四十年代出版的红封套《鲁迅全集》和《周作人文集》。三年前他还曾指着书架上这套红封皮的《鲁迅全集》对我说过:这套书随我由内地辗转来港,多少年来都是陪伴我的最爱!
有一件“书事”鲜为人知,我觉得有责任将之说出来。大约是1996年某日,罗先生约我饮茶。他说老作家叶灵凤先生生前喜收藏一些旧方志。其中有一本清代编印的《新安县志》,其实就是香港与深圳的地方志,香港当时与深圳全境属新安县。曾有英国商人想以重金欲收购此书,但被叶先生婉拒了。他认为此书乃香港被割让之前的史书,证明香港与祖国本为一体,且此刊本是各种存本中最好的一部。
后来,叶先生请罗孚先生陪同他将这部善本连同一批贵重之书捐献给了广东的图书馆。罗先生说九七回归是多少代人念念不忘的事,能否让我介绍深圳的出版社来出此书?我当即遵命与有关出版社交涉,对方也满口答应,却如泥牛入海,杳无音讯。
一晃过了快十年,2005年,罗先生又与我重提此事,说还是希望我能完成他的嘱托,由天地来出版此书。我为罗先生的这种拳拳之心所感动,就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将此版本校补,并在各方朋友的帮助下,将之以线装书形式重印。吾师饶公宗颐欣然命笔题签,终在香港回归十年的2007年底剞劂出版。虽毫无报酬,但于我却获益良多。
看到这部装帧古雅的二十卷《新安县志》,罗孚先生开心地笑了。可以说,没有罗孚先生的极力推动,这本方志也许将束之高阁,无人问津。从这件事上,我看到了罗孚先生以身许国的高尚情操,也实现了他对叶灵凤先生的深沉怀念之情。
第一次同罗先生见面,他毫无架子,亲切而幽默
我与罗孚先生的结识也缘起于《新晚报》。改革开放之后,香港的亲友将自己每日必读的《大公报》、《新晚报》收集起来,托人带给我们“延伸阅读”,我最喜欢阅读的是《大公报》的“大公园”文学副刊,《新晚报》的内容更吸引我的兴趣。
在八十年代之初,我写了一篇文章,经在港工作的陈可焜老师投稿到《新晚报》,不久之后,该文就发在了罗孚先生主持的《新晚报》上。我也就开始给《新晚报》写稿。记得有一篇是写弘一法师在泉州与青年黄永玉交往的稿子,却没了下文。后来看报才知罗孚此前被抓将官里去了,也就不再投稿了。
那一年十月,我去了日本留学。1993年年初,我由日本来港工作,与罗孚先生同一个月回港。老作家楼适夷先生之前曾多次对我提及罗先生在北京与他们一班文坛朋友的交往,楼老的儿子楼爱军兄就邀我同去拜访他。
这也是我第一次同罗先生见面,他毫无架子,亲切而幽默。我提起当年投稿之事,多谢他对我这个素昧平生的后辈的提携。他说:“那是我们有缘分吗?可惜的是弘一法师的稿,我全然没印象。要有,我肯定会用,我很钦佩弘一法师。”
我与罗孚先生的长子罗海星兄也很熟稔。1998年秋去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参加“金庸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国际研讨会之后,转道旧金山,主要想去拜候暌目多时的罗孚先生一家。海星兄是热心人,他开车接送我,安排我入住汽车酒店。罗先生翌日执意要来酒店看我,然后一起去拜候柳亚子先生的哲嗣柳无忌教授。柳教授与我偶有文通,罗孚先生就先同他约好,我们七八个人开了二架车到斯坦福大学的老人公寓去。
罗先生称柳教授叫“无老”,我们也跟着叫开了。无老已经九十多岁,老伴去世了,一个人住着一套偌大的大屋。他拉着我的手说了许多话,罗先生说:无老对你那么亲切,你好有福气。多少年过去了,无老也已辞世,而那一天的情景却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
其实,罗孚先生与柳亚子先生曾结下一段文字缘。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彼时,罗先生负责重庆《大公晚报》副刊“小公园”。该年10月,为纪念鲁迅逝世九周年,他向柳亚子先生约稿。柳先生果然如约赐稿,不仅寄来二首七律,还有一篇长文,这在当时可是大手笔,让罗先生足足高兴了好几天。
他成为许多国内文艺界、学术界大儒、学者们最好的知音
罗先生被人称为中共在港“统战”文化人的高手。他的温文儒雅和真诚待人获得许多当时不认同中共的文化人及学者们的赞赏。对于内地那些文艺界的大儒们,罗先生向他们邀约了大量的来稿,尤其是“文革”中受尽苦难的文化师匠们。在他珍藏的书画秀作中,我们可以看到沈从文、丰子恺等人于1975年赠给他的书法与信札。
改革开放之后,几乎全中国的著名文学家、艺术家都有文章在《大公报》及《新晚报》上发表,这对于劫火余生的这批老学者、老作家及老艺术家来说,不啻是久旱获甘露,那种欣慰之情实无法用笔墨来诉诸,这也充分体现了《大公报》“书生办报”的优良传统。
这些大大小小的动作引致一些思想极左的人的忌恨,但罗先生不在乎他们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指责,依然我行我素。他为能呼应改革开放的思想解放运动而雀跃。他成为许多国内文艺界、学术界的大儒、学者们最好的知音。后来滞留北京十年,他依然继续在这个“文友淘”中与他们诗酒唱和,结交了更多的朋友。
我与罗孚先生的交谊始于投稿,无论在香港、美国,这二十年来,“书”成为我们交往的媒介。1994年至1996年间,我在《明报月刊》任编辑,时常因编他的文章而有所交往。1998年,他编辑《香港的人和事》,约我写了一篇《人间国宝饶宗颐》的长文。他被迫退出报界,潜心于写作,以“柳苏”“丝韦”的笔名撰作有《南斗文星高》、《艺苑缤纷》等著作。近些年中,我又充任他的《北京十年》、《北京十年(续)》、《罗孚说周公》等三本书的主编,以及罗海雷撰写的《我的父亲罗孚—一个报人、“间谍”和作家的故事》的责任编辑。往来中,我也更为了解他传奇的一生和坎坷的经历,从心底里更为钦佩与尊敬他。他是一位真正的作家、老报人和宽容的迂书生。
有人曾说,如果罗孚只是一心做报纸,不去做所谓的统战,那么他的结果可能完全不一样。但历史不能假设,他属于组织的人,必须做这样的事,就像潘汉年那样。他没想到的是这种危险不是来自敌方,而是中了自己阵营背后射来的黑枪和暗箭。
罗孚先生走了,永远沉默了,但却未能盖棺论定,他的冤案至今未获正式平反,可是,他的磊落,他的真心诤言赢得了许多中国文化人的尊重。罗先生九十三年的长寿中所经历的人和事,为香港新闻及文化史留下太多的故事和建树。将来的历史学家们一定会为他秉笔直书,历史也一定会还他一个公道!![]()
29岁小伙恋上62岁老太 称做梦都梦到她
04/13 08:36
04/13 08:36
04/13 08:38
04/13 08:37
04/13 08:37
网罗天下
频道推荐
智能推荐
中科院院士丁奎岭任上海交大常务副校长
0条评论2018-10-30 13:11:10

凤凰资讯官方微信
视频
-

李咏珍贵私人照曝光:24岁结婚照甜蜜青涩
播放数:145391
-

金庸去世享年94岁,三版“小龙女”李若彤刘亦菲陈妍希悼念
播放数:3277
-

章泽天棒球写真旧照曝光 穿清华校服肤白貌美嫩出水
播放数:143449
-

老年痴呆男子走失10天 在离家1公里工地与工人同住
播放数:165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