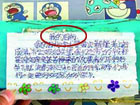傅桦被押到长春的当天晚上,审讯人员让他看了张广涛的录像口供。傅桦知道自己已卷入一个比想象中还要复杂得多的漩涡,局面很难有挽回的余地了。
傅桦最后也被送进长春市第二看守所,刑拘决定书上写的是:涉嫌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
傅桦回忆,张广涛在被抓前约一个月曾到京和他见过一面,谈起过李申已出事,让傅多加小心。傅听说此事后,心里顿觉不妙,“我觉得这个事情就复杂了,我不希望卷进去。”
尽管出事前已有让人心惊肉跳的征兆,傅桦还是没有想到,两年前的长春之行,在两年后会让三个人以极其尴尬的身份在同一个看守所里比邻而居。
几天后,傅桦的羁押期限被延长,理由是刑诉法规定的“结伙作案”法定理由。这时他才知道,他这个案子,居然是吉林省公安厅直属公安局有组织犯罪侦查队直接办理,也就是说,在警方看来,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涉黑”。
彼时的傅桦更不会知道,就在张广涛来京之时,两年前和傅桦一起去长春采访此事的报社同事姚春,也已经陷身北京市收容教育所。姚春其实早已在2006年5月从该财经日报跳槽到了另外一家报社,2007年3月,因嫖娼被当场抓获,被处劳动教养6个月。
傅桦被命令坐在一张审讯椅上,面对坐在对面高台子上的警察,这位前中级法院法官有几分苦涩,他试图调整自己的角色,又时时陷入梦魇一般的迷惘。
他承认先后收了李申15000元,真正收入囊中的只有5000元,另外10000元是帮对方办事、将见报稿件重新上网的居间费用。但这一数额并不能让办案方满意。于是28天的审讯里,傅桦的口供中,这个数额依次变为15000元、15000(25000)元,最后是40000元。
傅试图辩解,又觉得没有用处,“五千和四万有什么区别吗?这涉及到你认罪态度老不老实的问题!”
“镣铐的嘈杂声”
真正迷惘而又滑稽的日子是在看守所。
傅桦回忆,进去以后的那天晚上,“等到警察走了以后,同监犯人马上过来教育,一顿拳头,我就抱住头蹲在那儿挨揍。后来老大说,别打了,先问问他怎么进来的?于是抱着头走到老大跟前,大概说了一下情况。”
“老大问,那你这个记者以后还能写吗?我说写是能写,但是他们不让我写。‘他们不让你写管什么事儿?我们让你写!我们有什么冤屈你敢不敢写?’我说那如果老大说要写我可以写。‘那行了,都别收拾他了,留在咱们这边可以写写东西了。’于是就不收拾了。”
“我一介书生,因为‘涉黑’进去了,现在居然被黑社会老大救了,这一瞬间我真有一种很滑稽的屈辱。”
开始的恐惧和屈辱感过后,免除了部分皮肉之苦的傅桦,开始习惯和接受这种从未尝试过的新奇体验。牢友们很快就给个子瘦小的傅桦取了个外号“小北京”。这个来自四川的“小北京”暂时无法给大家“书写冤屈”,于是就发挥他乐观幽默的特性,在看守所里摆开了龙门阵。
“天天在里边大家都比较憋闷,我采访那么多事儿,就说说北京,给他们讲讲迎奥运。这个时候才觉得人性的东西在逐渐复苏,意识到你不是一个犯人、不是一个工具、不是一个行货、不是任人宰割的羊,你的大脑和灵魂还是属于自己的。”
甚至干活也是一种权利,走动也是一种权利。“在那里边大家都是坐板,是不能动的,能动就是一种权利、一种享受,所以大家都抢着擦地板。擦地板这活儿牛啊,那简直是幸福啊。所以我出来以后对人生的态度已经改变了,就觉得所有的东西都是幸福的,只有不自由的时候才不是幸福。”
“‘咣铛’一声铁门开启,每一次声音对大家来说是一个希望,也是一个绝望。铁门响了,里边就有一个人被召唤出去,但那个人不是你。不断有人被召唤,那个时候被提审都是很幸福的,因为提审你可以到外面空间去啊,回来的时候有人还悄悄地高兴,哎,我今天提审的时候又忽悠了三次烟,这是很值得骄傲的。”傅桦回忆。
“后来我出去提审的时候,我就要了支烟,虽然我不抽,悄悄地塞到口袋里带了回来。那个老大可高兴了,哎不错啊,你还想到咱兄弟们了。那个时候大家是平等的,包括你也是以心比心嘛。老大就说‘小北京’将来还要写东西呢,不能把他饿坏了。”
放风是最大的乐趣。傅桦回忆,有一天出去时看到旁边一个石台阶隐隐约约有字,也不敢吭声,悄悄地转到那边去,那时候没有眼镜,蹲下来仔细一看,是写得非常漂亮的十个字: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啊呀,我那时候就觉得生活真美好呀,头上就有两只燕子。每一次我们出去放风首先第一件事情是看看燕子怎么样了,然后一看燕子回来了又走了,唧唧的那种声音,感觉好像有小燕子了,觉得生活真是很美好。”
到7月份后,傅桦被调押到吉林省看守所,这是个主要羁押官员和经济犯的地方,“四个人一间,每人一张床,有点像那种二星级饭店了”。
|
编辑:
李志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