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聪和沈峻风云穿行过
2016年06月23日 01:49
来源:北京青年报
事前做案头工作时,许礼平曾对“沈崇事件”有个小结:1946年12月24日晚发生在北平东单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伍长皮尔逊强奸案,引发全国五十万学子和千百名教授的“冲冠一怒”,以一个19岁北大先修班女生沈崇的遭遇而影响大局,迅速发展成为全国性的群众抗议运动,最终加速国民党政权的收场。许礼平由此问沈峻,当时几十万学生示威游行,皆因你而起,你害怕吗?已有斑白发丝的沈峻答道:“不害怕,学生的行动是正义的。”
原标题:丁聪和沈峻风云穿行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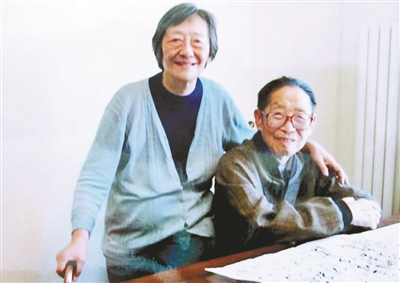
病中的丁聪和沈峻(吴戈摄)

丁聪所绘沈峻和儿子丁小一
◎本报记者/陈国华
首次回应“沈崇事件”
“你驳他,他驳你,没完没了。我一概不理”
2012年5月8日上午,60岁的香港文史学者许礼平携带从拍卖场得来的“沈崇法庭自白”手迹复印件,忐忑不安地来到北京城西边的一个餐馆。他等待的正是1948年发生在北平的“沈崇事件”当事人——漫画家丁聪的夫人、85岁的原外文出版社资深老编辑沈峻。
几十年来文化圈中悄悄地传说沈崇即是沈峻,但一直没有人正式访谈、核实过。许礼平心中自然知道其间的冒险和唐突,见到沈峻后先递上好友、出版人林道群转交的600元港币稿费,然后东一句西一句闲聊沈峻的家事。怎样开口呢?许礼平坐在餐桌边纠结万分,一个念头老是强烈地缠绕在脑子间:老太太85岁,再不问,怕会变成终生遗憾。
多年后许礼平向北京青年报记者坦承,那天向沈峻求证前,并没有预设几套方案,只能随机应变,先看看她见到此手迹有何反应。
“我出示这些材料的那一刻,的确有点紧张。”许礼平回述道,沈峻看到餐桌上摆放的当年自己手迹的彩色复印件,压低嗓门问,“哪里搞来的?给我的吗?”双眼泛着几乎觉察不出的淡淡泪光,面色为之一变,神情凝重而镇静。“看到沈峻如此反应,却让我放下了心头大石,确认沈崇真身后,其后的访谈都很顺利。”
事前做案头工作时,许礼平曾对“沈崇事件”有个小结:1946年12月24日晚发生在北平东单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伍长皮尔逊强奸案,引发全国五十万学子和千百名教授的“冲冠一怒”,以一个19岁北大先修班女生沈崇的遭遇而影响大局,迅速发展成为全国性的群众抗议运动,最终加速国民党政权的收场。许礼平由此问沈峻,当时几十万学生示威游行,皆因你而起,你害怕吗?已有斑白发丝的沈峻答道:“不害怕,学生的行动是正义的。”
针对社会上、网络上的一些有关沈崇传言,譬如“从延安派来”、“制造事件”等等,许礼平问道:“当时跟共产党有联系吗?”沈峻回答:“没有,我当时十九岁,什么都不懂,我家的背景都是国民党的。”她进一步表示:“当年国民党贴出大字报小字报造谣,早已被当时的学生驳得体无完肤,很快就没有声音了。现在有些人,只不过重拾当年造谣者的牙慧而已……你要知道,那个时候国民党是统治者,控制着国家机器,如果我是八路,早就被抓起来了。”
许礼平建议不妨亲自写文章澄清,以正视听,沈峻高声说道:“不,我不理。你驳他,他驳你,没完没了。我一概不理。”
一席话说完,许礼平如释重负。“沈峻以当事人身份回答诸问题,坦白直率,解决了许多关键疑问,可以说是为历史定案。”因为顾及亮出录音机,会使沈峻说话有所保留,许礼平此次并没有带去录音设备,访谈结束后生怕有遗漏,他立即回到酒店房间,赶紧拿出采访本凭着记忆补记。
问及访谈后沈峻有没有什么叮嘱?许礼平回答说:“没有。她当时不一定知道我会写文章的,而我当时也不确定要写此文的。”他后来据记录稿写成《倾人之国的佳人——记沈崇自白》一文,刊发后引发广泛关注,读者们首次正式从报刊上获知“沈峻即沈崇”的信息,也知道了一位弱女子及所代表的学生群体在暴行之后的刚毅和团结。
文章发表后,许礼平托老友转呈给沈峻,没有听到她有什么不良反应。两人第二次见面时,老太太态度依旧和气,谈笑风生,讲了老友郁风诸多趣事。从过于晦暗的历史隧道寻觅而来,感受到一个存在于史书记载中、真真切切的普通人物,许礼平忍不住地一再感慨:“要问我对沈峻有何突出感受?那就是她性格爽朗大气,阳光充足,相处如沐春风。真是女中豪杰的典范。”
当然,也有一些相识、不相识的朋友批评或评估文章的发表,认为应该尊重隐私权。许礼平理解这些朋友的生气理由,认为隐私和史实平衡的问题确实值得探讨。但他执著地认定,如果等到沈峻大姐不在才发表的话,又会引来许多问号。他说:“拙文发表后,沈大姐的死党、闺蜜都觉得帮了大忙,有力反击了近年社会上诸种奇谈怪论。”沈峻好友董女士看了文章草稿后,希望早日发表,她郑重地拜托许礼平:“这是好事,现在还历史的真实比以后要好得多。”
被老友们竭力回避的忌讳
“被暴风雨冲刷,身上有一种坚硬的壳”
“陈(四益)文丁(聪)画”模式存在了二十五年,堪称读书界的一大奇迹。《瞭望》原副总编辑、杂文家陈四益与丁聪合作“亲密无间”,也与丁聪夫妇结下深厚的私交,无话不谈。友人从邮箱传来许礼平写“沈崇事件”的文章电子版,他就马上给沈峻打电话询问,只是想证实是否获得她本人的认可。
沈峻在电话中说:“他(指许礼平)做了很多准备,把那些材料都给我看了,比较客观,所以也就把事情同他谈了。”至今陈四益还记得沈峻平静的说话语气,他告诉北青报记者:“沈崇事件已是历史公案。沈峻看到某些文章很反感,与其不说、乱说,还不如客观去说会更好。那段悲惨遭遇,是她毕生之痛。有什么必要,又有什么权利,由另外一些人凭借一些不可靠的花边新闻去撕扯一个受难女子的灵魂。”他与沈峻相熟,但跟许多老友一样从未问过“沈崇事件”,“内心创伤的东西,何必揭它。”想不到此次被来自香港的学者捅破了。
翻译家杨宪益的大妹杨敏如1946年为学校老师,“沈崇事件”爆发后,持进步思想的学生都来找她发泄,房间里弥漫一种挥散不去的青春愤怒。小妹杨苡当时在南京中央大学借读毕业,曾经目睹南京抗议大游行的情景。很久以后杨宪益暗地里告诉她们,“沈峻就是沈崇”,叮嘱她们要对外保密,并说了一句:“这个女同志真了不起。”
“沈崇事件”之后,改名后的沈峻考取上海复旦大学外文系。老诗人邵燕祥的夫人谢文秀那几年也在复旦新闻系就读,她回忆说:“当时复旦女生不多,我知道她在复旦待过。为避免提及不愉快的往事,相识这么多年,我从来不问她复旦哪一年的?也绝口不提复旦。”
“文革”的混乱形势却造成“沈崇事件”信息外泄,对当时在对外文委工作的沈峻形成可怕的外力压迫。80岁的外文局老编审陈有升告诉记者:“外文局造反派战斗队乱七八糟,有派性斗争。有一天在大食堂突然贴出大字报,公开写沈峻的名字,说她是‘吉普女郎’,是非颠倒,要弄臭她,造她的谣,揭她的伤疤。”陈有升记得,当时食堂是“大字报海洋”,那张大字报贴在食堂角落里,一下子把“沈峻即沈崇”的信息公开,在场的人起哄特别多。
翻译家荒芜1972年从河南五七干校回到北京,住在当时的学部文学所三楼上。女儿林玉描述说,通往楼顶阳台的门在我们屋里,父亲的老朋友和我的年轻朋友经常在大阳台聊天,有安全感。“有时我们说到沈崇事件,坊间传言很多,我妈还批评我们说‘妄议长辈’。历史事件对我而言太遥远,但我能切实感受到沈阿姨这一代女性,都是在特殊境遇中锤炼出来的,被暴风雨冲刷,身上有一种坚硬的壳。”
十几年前,有人采访五台山一尼姑,那尼姑冒名是“沈崇”。陈有升、吴寿松作为沈峻单位的老同事,看到文章后非常气愤,认为文章内容完全是“谬论”,他们各自给有关单位写信反映情况,未见回复,又接着给中央部门一位领导直接发信,直到有了初步处理意见。
几十年间老友们竭力回避这个忌讳的问题,生怕触及难言的伤痛。十多年前上海某报社一副总编去采访沈峻,事先有知情人劝他不要问“沈崇事件”,但副总编还是在最后时节提问了,沈峻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那已经成为过去了,不要提它了。”
北青报记者在采访中,却意外发现沈家后代是最后知道“沈崇案”人物信息的。沈峻大妹的儿子、外甥戴尹说:“沈崇事件知道很晚,家人没人说,小辈不知道,但隐隐约约地有感觉。大姨沈峻去世以后有报道,涉及沈崇,我爱人给我打电话,说‘好像说的是我姨’。真的是去世后才知道这么回事,以前跟我姨也没聊过。”戴尹把网上文章转给在美国工作的表哥、丁聪沈峻的独子丁小一,他也说:“不知道怎么回事。”
戴尹办理沈峻后事时,外文局老干部处的人说:“你姨的名字是进入党史的,毛主席文章中提到此事。”
采访时下着小雨,云彩暗淡,戴尹眺望办公室的窗外,半天后说了一句:“沈崇案过去这么多年了,说说也无妨。”
困苦中的坚韧
“受点苦,没什么的”
抗战时成名的漫画家丁聪经历了多年战火磨难、颠沛流离之后,五十年代初有了安定工作,出任北京外文出版社《人民画报》副总编辑,热情高涨地筹划编辑部事务。收集很多丁聪史料的学者李辉举例说,当时听闻出版人邵洵美因生计困难要卖掉设备,丁聪马上到上海找他,为新单位买下当年世界上最好的德国产印刷机器。
丁聪的妹妹丁薇是沈峻的大学同学,那一年丁薇从上海来北京游玩,沈峻来找她,也就顺便认识了丁聪。两人相恋后,老友、文化部副部长夏衍欣喜地宣布:“你们年底结婚,我给你们办酒席……”1958年沈峻生下儿子丁小一,丁聪被划为右派,只得悄悄地在产房外看了小儿一眼就被发配北大荒。
林玉的父亲、翻译家荒芜也在外文局划为右派,同丁聪、吴祖光等坐一趟火车离开北京。林玉清晰记得那个苦涩的日子:“1958年3月11日他们离开的,在东郊火车站上车。”林玉的两个哥哥去车站送行,看见中直机关一千几百名右派分子带了行李在站台排队。多年后才知道,那天他们并没有走,而是在站台附近的一个大仓库里,头对头、脚对脚地住了三天,学习《人民日报》社论。“听哥哥说,父亲他们在站台上还打招呼说笑,全然不知前景如何。后来监督劳动中的饥寒几乎要了他们的命,方才知道北大荒的厉害。”
林玉存有两张北大荒850农场的旧照片,是丁聪在北大荒“难友”杨崇道集藏的。照片上大家疲惫地站在夏收田地里,赤着上身,短裤残破,人人干瘦。林玉为老辈心疼地叹了一口气:“这张照片都不好意思拿出来给人看。”而另一张四人合影照片中,唯有丁聪一人还坚守斯文模样,穿着短上衣和长裤。杨崇道告诉林玉:“其实丁聪没坚持多久也不行了,衣服破了也一样没得穿。”
1962年丁聪摘下右派帽子,返回北京,与妻儿团聚没几年,“文革”中再遭冲击,又被下放干校。戴尹从小就随着外婆住在大姨沈峻家,与表哥丁小一一起长大。说起“文革”的家庭遭遇,他自然最忘不掉的是外婆的呵护和从容、大姨夫大姨困苦中的坚韧:“大姨那时说,丁聪1957年提意见被划右派,家中有亲戚在台湾,我们家是标准的黑五类。外婆是林则徐家族的后人,对我们哥俩很疼爱,她见过大世面,风雨中真是淡定。”那时丁家住在西城区祖家街的两小间平房,先后有三四拨红卫兵来抄家,砸掉丁聪爱听的老唱片,拿走丁聪收藏多年的心爱画册。“十几个红卫兵很凶,外婆没有吓坏,护着我们坐在那里不说话。她担心我们害怕,等红卫兵走后就安静地收拾乱成一片的房间,正常做饭菜。身在外地的大姨大姨夫操心北京家中情况,托人带信寄信,信件都得敞口,不能沾胶水。后来他们穿着打满补丁的旧衣服回北京探亲,看看我们小哥俩儿不缺胳膊不缺腿就很高兴。”
丁聪后来转去文化部大兴黄村干校劳动,在猪场当饲养员。在同辈人的回忆文章中,多写到丁聪与造反派的艰难周旋和种种挨斗的不堪,但在戴尹的小时记忆中,浮现出来的大姨夫却是一个乐呵呵、尽责的老猪倌形象。“我和表哥去过猪场,见到姨夫穿着旧棉袄,脚上是一双大雨鞋,胳膊套上套袖,吃力地把一大桶猪食倒进槽里。他整个打扮像农村老大爷,见人爱笑,同事们都叫他‘小丁’。”丁聪坐在简陋的大通铺上发愁地嘟囔着,‘没吃的没吃的……’他设法从食堂找出一把猪油渣,分给两个饥肠辘辘的小孩咀嚼。
“文革”中每逢美术界开批斗大会,丁聪从来是陪斗的边缘人物,变得谨小慎微。1974年他总算从文化部干校回城,在东四八条参加一个月的文化部过渡学习班。美术馆老同事洪天珉对丁聪的缄默不语印象最深:“那一个月就是学文件念社论谈感受,从稻田劳动回来,我们小辈的还很兴奋,从早说到晚。而丁聪他们思想包袱相对沉重,发言极少,别人催促,他就说,‘你们先说,你们先说。’”
丁聪和郁风等被发落到美术馆,闲挂在那里。洪天珉愤懑地说:“丁聪斜背一个黑色帆布的长带书包上下班,与业务游离。当年美术馆领导热衷于搞政治运动,不去很好发挥丁聪他们的作用,对他们才华的忽视至今都不能原谅。”
“文革”中丁聪沈峻很少同孩子们聊到政治,1978年右派帽子摘掉后,两代人终于可以敞开心扉说几句。20岁的戴尹提及当年划右派的情形,对丁聪说:“您太敢说真话,必然会出问题……”丁聪认真地说:“都不说,那怎么行?”然后,他缓慢地补充道:“我们也是为了国家好,才提点意见。受点苦,没什么的。”
时至今日,戴尹自然理解丁聪的一片苦心。他沉吟一会儿说:“那时节,这些家长生怕因为他们这些年不公平的遭遇,担心我们想不开,反而做我们的思想工作。”(下转B6版)

凤凰资讯官方微信
视频
-

李咏珍贵私人照曝光:24岁结婚照甜蜜青涩
播放数:145391
-

金庸去世享年94岁,三版“小龙女”李若彤刘亦菲陈妍希悼念
播放数:3277
-

章泽天棒球写真旧照曝光 穿清华校服肤白貌美嫩出水
播放数:143449
-

老年痴呆男子走失10天 在离家1公里工地与工人同住
播放数:165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