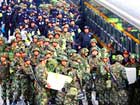一
许多年来,阅读中国文学史之类的著作,遇到文人们年纪轻轻地便被帝王们杀害的章节时,我的胸中便会有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似的难受。至明代初年,触目皆是鲜血淋漓的文人之厄时,物伤其类的愤懑情绪就更加强烈了。
半文盲出身的朱元璋当上皇帝之后,想出了三点对付文人的办法。一是笼络,于洪武六年开设了文华堂。二是高压,颁发了“士大夫不为君用者罪该抄杀”的诏令。三是加密文网,从一字一句上对文人的诗文吹毛求疵,寻找迫害的证据。元末明初的文人,如王冕、戴良、倪瓒、杨维桢等人,皆或直接或间接地死于朱元璋之手。王冕在明代建立之前被朱元璋所得,留在军队之中,忽于一天夜间暴卒。戴良于洪武15年被召至京师,坚决不当朱元璋的所授之官,于第二年自杀于寓舍。当朱元璋得知倪瓒不愿为己所用且有洁癖时,就想出了一个下流的办法,把倪瓒投于厕所之中,使其恶心而死。杨维桢不应朱元璋的征召,并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一句“高山肯为秦婴出”,朱元璋闻之,便说“老蛮子欲吾杀之以成名耳”。杨维桢自知不免,遂自缢身亡。
二
明代建国之初,青年诗人高启还是十分兴奋的。毕竟,战乱之苦是不用再受的了。虽然元末的社会现实使高启写出了不少诗歌,正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是也。但他肯定还是向往着过上太平日子的(“宁为太平犬”这句古诗,意味十分丰富。中国人的价值之低,由来已久)。对于那位马脸的皇帝,高启一开始还是表现出了一定的赞佩的。他在《登南京雨花台望大江》的最后写到:“我今幸逢圣人起南国,祸乱初平事休息。从今四海永为家,不用长江限南北。”并且,高启还接受了朱元璋的任命,当上了一个翰林院国史编修的官儿。但时间不长,高启便对朱明政权产生了厌恶。朱元璋在政治上的高压政策,使高启具有了如履薄冰的恐惧感。这在他的《步至东皋》一诗中有所表露。诗云:“斜日半山明,幽人每独行。愁杯逢暮惨,诗意入秋清。鸟啄枯杨碎,虫悬落叶轻。如何得归后,犹似客中情。”在这种心态之中,高启对于提拔他为户部侍郎的诏令,固辞,归隐于他的老家青丘。高启这样做,是很符合他的个性和品格的。他的《青丘子歌》,便是他自由洒脱性情的自然流露。高启说他是王云阁下的仙卿,说他不肯折腰为五斗米,不肯掉舌下七十城。这样的人物,是不适合当官的。可是,朱元璋这个伙计与元代的皇帝不同,士人们的隐居使他难以容忍。对于高启的辞官不做,他当然是十分的恼火了。此外,他对高启的那首讽刺宫庭淫乱的诗也是早就心怀不满的了(高启的诗为《宫女图》,云:“女奴扶醉踏苍苔,明月西园侍宴回。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于是,他就利用苏州知府魏观改修府治案,把高启牵扯进去,将其腰斩于市。是年,高启仅仅38岁。
与高启同为明初诗文代表人物的刘基,其命运与高启相比,也没能好到哪里去。元亡之前,刘基的诗文就已经写得很好了。他诗文兼善,寓言文尤为超拔。他本可以以诗文自娱优悠卒岁以至得享天年的,却偏偏在朱元璋迫逼下,硬着头皮出山,成了军师之类的人物。刘基不只是一个书生,对于军事,他也十分内行。我曾看过他写的一本《百战奇略》,感到其中充满了智慧。帮着朱元璋打下天下之后,对于朱元璋隐秘的内心世界的洞悉,他有着政治家的敏感。因此,他的忧生之嗟,比高启来得还要强烈。入明以后,他的诗作的题材变窄了。变得心灵内敛,惴惴得很厉害了。他的《感怀》一诗这样写到:“结发事远游,逍遥观四方。天地一何阔,山川杳茫茫。众鸟各自飞,乔木空苍凉。登高见万里,怀古使心伤。伫立望浮云,安得凌风翔。”他为了全身避祸计,称老退隐于故里山中,但还是没能幸免于难。64岁那年,朱元璋听信与刘基有宿怨的胡惟庸的虚妄之言(胡惟庸说谈洋这个地方有王气,刘基想据为自己的墓地),剥夺了刘基的奉禄。刘基心中大惧,入京谢罪后居于京师。不久,胡惟庸为相,刘基便忧愤而死。刘基的死因,还有另外一说,说是刘基是被胡惟庸毒死的。
除了上述作家之外,明初尚有杨基、张羽、林鸿、刘崧、袁凯、孙贲等人,大多被朱元璋迫害得死于非命。对付手无寸铁的文人,朱元璋这个流氓的屠刀真是锋利无比。
三
高启、刘基这一大批文人凋谢了,残酷的现实吓破了文人们的小胆。他们知道了皇帝的厉害。他们开始慢慢地变了,变得老实了、听话了,变得“不知不识,顺帝之则”如一条小狗一只猫咪了。于是,统治明代文坛几近百年的台阁体,就在渐渐地孕育着了。台阁体的执牛耳的人物,是三位姓杨的大臣,杨士奇、杨荣、杨溥是也。这三位伙计为人的基本的东西,从杨荣迎接野心得逞的朱棣进入南京时说的那句话上,就可以了解到一个大概了。当时,朱棣气壮如牛,昂首马上,“荣迎马首曰:‘殿下先谒陵乎,先即位乎。’”——这两句来得真是太漂亮了。朱棣是什么人,立即就听明白了杨荣的本意是想让他先去谒陵,然后再去即位。自此,成祖皇帝便对杨荣青眼相看了。杨士奇、杨溥两位,也先后得到重用。明英宗初年,三杨以大学士身份辅政。这标志着文人与皇帝的关系达到了一种亲和的程度。应该说,这种亲和,是被皇帝的淫威所吓出来的。这种关系表现在诗歌上,情形是这样的:三杨虽然推崇唐诗,但只着眼于“以其平和易直之心,发为治世之音”(杨士奇《玉雪斋诗集序》)。他们写作了一批“圣谕”、“代言”、“应制”之类代替皇帝说话的东西。在散文写作上,他们学习、摹仿欧阳修散文的平舒柔婉的风格,写了不少“墓志铭”、“神道碑”、题序等等应酬捧场的作品。他们的诗文,由于皇帝们的喜欢和提倡,从永乐以至成化、弘治(1403至1505)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人不深受影响。于是,便出现了从上到下人人只会写一些内容上歌功颂德、粉饰太平,艺术上平庸呆板、毫无生气的诗文的沉寂局面。文人们,变得千人一腔、万人一脑了。
我很想能把三杨的诗文找到,看一看他们是如何地给帝王们搔痒、拍马的。可惜,搜遍书房里百十本明代的书籍,就是找不到。光文学史之类的著作,我手头就有七、八种之多,但没有一种引用三杨诗文的。像博学如郑振铎先生,在提到三杨时,也只是简单地介绍一下了事。文学史家们在引用作家的诗文时只选优秀之作的做法,只能给读者一些正面的信息和判断,不利于全面地了解文学史上的复杂现象。正在愁闷之际,在一本刚出版不久的文学史中,见到了这样一节文字,大意是说官礼部尚书、太子太保兼文渊阁大学士的丘仲深,写过一部名叫《伍伦全备忠孝记》的传奇。此剧情节全是伦理概念的图解,毫无生活气息可言。踏破铁鞋,终于找到了一篇“台阁体”台阁大员作品的题目,也算是慰情聊似无吧。
三杨等人,都是高官厚禄而且长寿。其中,杨士奇79岁,杨荣70岁,杨溥74岁。三人几乎都比高启多活了近四十年的时间。
四
历史是无情的。三杨虽然生时得意、顺遂,但死后,死了几百年之后,就没法与高启、刘基相比了。高启虽然只活了38岁,但将其诗歌放在有明276年的历史长河当中与别人相比的话,也称得上是优秀之作。刘基的散文,至今仍放射着深刻的思想光芒。这,也许就是一种历史的公平吧。
|
作者:
武俊岭
编辑:
梁昌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