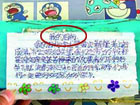1974年,郭锄非得到正式平反,平反结论上写着:“经复核调查研究,原判反动标语,不是郭锄非所为。故决定撤销原判,改判郭锄非无罪,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少年时代的精神创伤给我儿子留下很深的烙印,从此,他胆小怕事,怕当官的。现在,有人为了控制我,还利用我儿子这个弱点,让他来求我,不要对他的工作产生影响。
抓了我儿子之后,1972年6月27日,我也被抓起来了,罪名是“非法堕胎”,判处“劳动教养三年”。我实际上被关了13个月,在河南省新郑县和长葛县交界处的陉山劳教场。
幸亏我丈夫在外面替我申冤,1973年7月19日,我活着走出了陉山劳教场。这年10月27日,我收到了郑州市革委会公安局给我的平反决定,恢复我的名誉,回原单位工作。
可是,我和我的家庭在“文革”中受到的迫害,并没有因对我的平反而结束。到了1979年12月5日,我才看到了郑州市中医院给河南省中医院的函,这时,我已经调到了河南省中医院。这个函终于给我彻底平反了:“我院于1979年3月对受到四人帮迫害的同志进行了平反。高耀洁同志虽已在院大会上平了反,但由于她调走,今特函,对高耀洁同志进行平反,恢复名誉,对受株连的子女亲属恢复名誉。”
离开手术台走上讲台
有了公款消费,有了“三陪”,性病传播就有了生长的土壤。我发现了这个问题后,从1994年开始,就到处去演讲,去做宣传。
我终于又有了工作的机会,又从郑州市中医院调到了河南省中医院,我感觉又有了活力。20世纪80年代,我所在的科室已经是远近闻名,成了没有挂牌的“恶性滋养细胞肿瘤治疗中心”。慢慢出了名,我们河南省中医院第一附属医院也出了名,病人多了,医生少了,人手紧,我有一次9天9夜没离开病房,后来,我晕倒了。
1983年,我和科室获得了河南省二级成果奖,我也获得了晋职、晋级和各级领导的重视。那几年,我们医院的病人非常多,我们得到了一些荣誉。1984年,我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中西医结合大会,被授予了一枚奖章。我是“九三学社”社员,这年又在北京参加了第四届社员代表大会,邓小平、胡耀邦都参加了会,接见了我们。
1988年,我被评为郑州市劳动模范,又当上了河南省第七届人大代表。我退休的时间因为医院人手紧,也一推再推,1990年,我都63岁了,还在工作。
1990年7月15日,我又到医院上班,晚上,退休人员聚了一次餐,宣告我正式退休了。饭后,我又到病房看了下,默默无声地走了,说实话,我舍不得这些病人,但我这一走再没回去过。
我退休之后,本意想写一些东西,总结一下40年的临床经验,可是,不断有人找上门来,希望我能到小诊所去挂牌,去坐诊,给很高的价钱。我都一一拒绝了。在郑州西郊,竟然有人挂出牌子“高耀洁教授在本所坐诊”,我带着记者去抓,可能事先暴露,扑了空。
1992年春节后,河南省当时的一位女副省长找到我。她说1995年要在北京召开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要我写一篇论文,在参加大会时用。于是,我开始在河南全省范围内,对几千名女性的健康进行调查。
通过这次调查,我发现:城乡接合部妇女发病率高;性乱使女性发病率高。我们检查了7个监狱,其中女子监狱的性犯罪在押的女人,性病发病率为92.7%.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做了深入了解。
我发现改革开放几年后,出现了一个特殊群体,她们像城市健康躯体上的肿瘤,俗称“三陪女”,活跃在歌舞厅、夜总会、美容院等地方,从事色情服务。
这时,我听说豫东一带流传着一首打油诗:“吃喝嫖赌胆包天,贪污受贿心不悬。只因手中有巨款,某君今日又升迁。”有了公款消费,有了“三陪”,性病传播就有了生长的土壤。
我发现了这个问题后,从1994年开始,我就到处去演讲,去做宣传。1995年的半年里,我就讲了十几个大学,仅是三八节那天,我就在三个大学里演讲,宣传预防性病知识,那时还不懂艾滋病,所以,也就把艾滋病和性病放在一起讲了。
我退休后,没有去私人诊所,却争到了讲台。我认为我们女性更应该提高卫生保健知识,劳累了我一个人,让大多数人受益,这很值得。
游医曾威胁杀我全家
对这种人,当时我就想,我要一直干下去,哪怕我本人遇有不测或者我的家人为此出了意外。
1998年1月24日,河南省文史馆举办迎新茶话会,我是文史馆馆员。时任省长的马忠臣要来参加,我得知消息后,连夜写了一封信和调查报告,痛陈当时的游医黑幕,呼吁省长关注此事。第二天,我当面把信交给了马忠臣。
我在信中说:根据我亲身调查,发现我省各地市仍有大量游医,利用他们手中骗来的钱,收买了某些医院的领导,承包租赁医院的科室,摇身一变为“性病专家”等。
我与游医的接触不是一次了,除了那次带着记者堵乱用我名号的诊所落了空之外。1997年的秋天,一个年轻人差一点因为乱治病而染上性病送了命。我是一个致力于妇科病防治的妇产科医生,我很疑惑,我们的社会难道有这么多性病患者?又有那么多治疗性病的专家?我当时就认为,这已经是全国性的一场灾难了。
从退休后,我与游医、假药的交锋就开始了,从1990年起,我走上了一条漫漫十年的“性病游医打假”路。
我在那年秋天就开始暗访了50多家所谓的性病门诊,我扮成病人家属,走街串巷,光打车费就花了3000多元钱。所见所闻令我不寒而栗。
我给省长的报告引起了重视,第二天,马忠臣就作出了批示。1998年3月30日,省政府召开全省整顿医疗市场的电视电话会议,打击假药假医假郎中的活动在全省展开。
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一些不知其身份的人打电话到我家:“再多管闲事,要你的老命,不仅杀你,还要杀你全家。”个别的媒体负责人也说:“老太太乱告状,让我们损失了数百万元广告费。”
我的小女儿也受到了牵连,她原在一家医院工作。为此,工作也丢了。我明白了,游医后面有保护伞,但我不会向这些丑恶势力屈服。
1999年春天,我再次上书河南省长,痛陈游医的危害,要求取缔性病游医,治理非法医疗广告。这年8月13日,河南省政府再次召集省公安厅、省卫生厅、省工商局等有关部门,研究集中整治游医、非法医疗广告的问题。
我经常听到全国各地患者打来的电话,听着他们在电话中带着哭腔的控诉:“高老师,我让性病游医害苦了。”这一切,让我意识到性病游医肆虐的范围不是河南一个省,于是,我又投书中央、省领导和各大媒体揭露性病游医及其支持者。
那些医药骗子真多啊!他们像苍蝇一样嗡嗡乱飞。他们又千方百计不择手段搞来与我的合影,妄想借此说明他卖的药是真的,以便欺骗病人。对这种人,当时我就想,我要一直干下去,哪怕我本人遇有不测或者我的家人为此出了意外,我只希望净化医疗环境,让老百姓受的痛苦再少一些。
|
作者:
喻尘
编辑:
李志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