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姐的微笑
2015年10月25日 13:04
来源:羊城晚报
不过后来愤慨很快变成了惭愧,因为当我转头看那歪果仁时,他也是满脸微笑与空姐交流。微笑是相互感染的,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板着脸,却责怪别人的脸上为什么没有笑容。前段时间去巴黎访学,巴黎街头给我留下的一个深刻印象是,“路人”都是微笑的,路上遇到陌生人,迎面走来时多会友好地微笑。平常再“冷漠”的人,面对一个友好的笑脸,可能也都会情不自禁地露出笑脸。
原标题:空姐的微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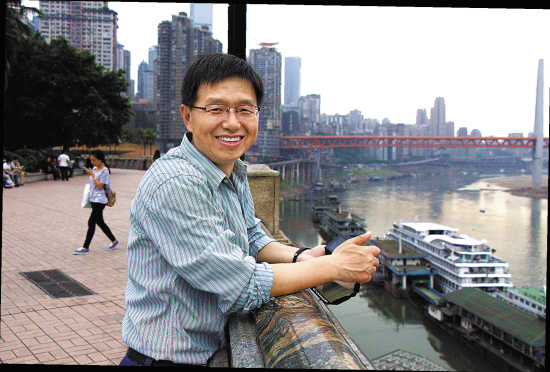





【拒绝流行】
曹 林[时事评论员]
空姐的微笑
坐某公司的航班出差,空姐发午餐,给我发餐盒时我有点儿不高兴,因为空姐好像很冷漠,一点笑容都没有——印象中,该航服务态度不是很好的吗?空姐不应该笑对乘客吗?接下来的观察让我更加不满,旁边坐着一个歪果仁,那空姐给这歪果仁发餐盒的时候满脸微笑。我心中立刻非常鄙视地吐槽了一句:这也太崇洋媚外了!
不过后来愤慨很快变成了惭愧,因为当我转头看那歪果仁时,他也是满脸微笑与空姐交流。微笑是相互感染的,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板着脸,却责怪别人的脸上为什么没有笑容。前段时间去巴黎访学,巴黎街头给我留下的一个深刻印象是,“路人”都是微笑的,路上遇到陌生人,迎面走来时多会友好地微笑。平常再“冷漠”的人,面对一个友好的笑脸,可能也都会情不自禁地露出笑脸。
“路人”在我们的语境中常常是一个冷漠的形象,习惯的搭配是“冷漠的路人”,这种冷漠不是哪个人的错,而是互相传染的。
我们习惯把责任和问题推给别人,然后把自己当成无辜的受害者。习惯把别人当成导致问题的原因,而忽略了一个关键因素,自己其实也是问题的一部分。黄色标题党泛滥,媒体说是为了迎合读者,读者说是被媒体误导,问题在谁呢?显然不是单向的,而是媒体的恶趣味与读者恶趣味的互相传染和强化。
【别处生活】
胡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镜与灯
美国康奈尔大学英语系M.H.艾布拉姆斯(M. H. Abrams)教授今年4月辞世,其作于1953年的《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The Mirror and the Lamp)以两个令人印象深刻的隐喻,对比古典的模仿再现与浪漫主义的创造,从而在文学批评史上树立了不朽的地位。
这里的镜,意指文学以某种模拟的方式像镜子一样反映真实世界;这里的灯,指作者的内在灵魂发出的光芒可以照亮世界。艾布拉姆斯强调浪漫主义在感性上构成一个转折点,浪漫主义者开始以新的方式思考诗歌,调用植物、喷泉和水流的比喻来形容创造过程。
为什么这个转折是重要的?因为它把文学批评的焦点由读者转向了艺术家。文学不再被理解为对宇宙的普遍反映,而毋宁是对人性的个性表达。这种对主体性的强调,摧毁了旧时的理想化反思的被动性。
在文学艺术史上,镜子永远比灯多。然而,是灯真正撑起这部历史。一个诗人,一个艺术家,或者一个哲学家,只从自己的内心和决心出发,对时风视而不见,照亮的却是整个自然。这样的艺术家是冒险者,逆流而上,独排众议,捍卫个人观念到不顾忌政治正确性的程度,时温与己无关,流俗是其敌人。
在当今这个充斥意识形态的时代,遇到“灯”是一种侥幸。加缪在1948年说:“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人被平庸而凶猛的意识形态推来推去,已经习惯了对一切都怀有羞惭之心。”你立刻能感到这里是一个独立的心灵在表达自己,一种自由而自豪的精神在发言,那是一盏燃烧的灯,而不是一面温柔的镜子。
【横眉热对】
杨小彦[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
郭沫若的字拍出千万元天价
刚刚过去的广东崇正拍卖已故前副总理谷牧“九腾书屋”收藏作品,创下广东二十年来拍卖的最高纪录,给已经疲惫不堪的广东艺术市场打了一针优质鸡血,称赞声充盈于耳。笔者也到现场,目睹激动人心的举牌时刻,尤其是郭沫若“建设”二字书法,居然由原定250万到300万元,最后拍到了1400万元,加上手续费,高达1700万元。真是令人咋舌,让现场不少人大跌眼镜。
业界对此热情,自有其道理:一、当年高官收藏,都是真东西,赝品较少;二、当年中国艺术市场尚未充分发育,画价不高,画家送的自是好东西,很少粗糙之作;三、收藏者热爱艺术,品味自高,所收者,是上品中的上品。如此一来,作品受到大家追捧,实在正常。
有意思的是,中国内地的艺术市场一直在讨论,为什么我们没有藏家,只有炒家。上述拍卖又一次证明,真正的藏家还是有的,但那只属于权力收藏。其实,有炒家也不是不好,也应该算是一种收藏,一种通过拍卖进行交换而获得升值的收藏。只是,在这里,拍卖其实是一种资本运作,掀翻了收藏的本意,让收藏变成资本游戏的另类方式。这样的收藏,颠来倒去,还能叫收藏吗?
其实,历来收藏都和权力有关。西方艺术史上有保护人与赞助者的时期,十五世纪著名的米开朗哲罗和达·芬奇,今天看是伟大艺术家,那个年代他们只不过是美第奇家族的保护对象,其作品也大多为这个显赫家族而创作而收藏。
历来大抵如此。
【含英咀华】
黄维樑[香港学者、作家]
金庸:运财侠士
金庸先生开始写武侠小说在60年前,今年有一些团体为此庆祝60大“寿”。金庸影响深远,其粉丝纷纷满布天下的汉语社区。我想起1970年代初留学美国时与此有关的旧事。
就读的俄亥俄州立大学,图书馆中文藏书丰富。架上的煌煌《金刚经》等佛教经典,整齐肃穆;有“调素琴,阅金经”句子的《陋室铭》等古典文学书刊,也是岸然整然。唯独一堆金庸作品,不成威势,甚至有点散兵游勇的样子。
与东亚语文部的主管交谈,才知道金庸小说借阅的人多,书籍疲于应战,而显得军容不振。俄大图书馆在美国的大学图书馆中,最早实施计算机化,借阅数据易得。主管说,金庸的武侠小说,经常为人借阅;借阅量不但高踞中文书籍之冠,在馆里所有图书中,也名列前茅。我这才理解,此“金”经不同彼“金经”。这“金”经有实质的金钱效益:学校对东亚语文部的购书拨款多寡,有书刊使用率高低的考虑;“金”经里的侠客拉高了东亚语文部书刊的使用率,成为运财侠士。
当年俄大的华人师生,大概有二三千人,加上若干华人师生的家眷,这些颇为高级的读者,在《书剑恩仇录》、《射鵰英雄传》、《笑傲江湖》、《鹿鼎记》里得到阅读的乐趣、得到历史文化知识、得到感情的共鸣、得到人生智慧、得到清通流畅的中文,成为留美生活的宝贵收获。
粉丝向来众多,金庸作品定会长寿。
【如是我闻】
陈玉慧[旅欧台湾作家]
我的表演课
廿二岁那年春天,站在巴黎街头,看着一群唐氏病症演员表演哑剧,这就是我当时下定决心学表演的主因。
我进了沙许马旦学院以及全球闻名的贾克乐寇(Jacques Lecoq)学院,我和贾克乐寇本人学到许多至为宝贵的表演真理,我觉得其实是人生真理。
我生平第一堂表演课必须表演等待。我坐在舞台的阶梯上,就真的在等待,我不知等了多久,然后我对空空的房间很生气地喊了一声“可恶”,就开门走了。老师说我演得非常好,我得意了许久。
我的第一个正式的角色是在校外演出,是户外的戏剧形式,大冬天又下雪,我穿得少又薄,必须向从车站下车一路走来的观众搭讪和拉客,我不是唯一的妓女,我们共有十来个人,但只有我是东方面孔。
仅仅是妓女,也人人演得不同。我学到的便是,西方演员动作比较大,而我自己只有面部表情,动作根本没放开。我也想过,也许,东方人比较含蓄?后来我才知道,含蓄是一回事,但表演含蓄是另一件事。
我在表演学院的学习过程是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光之一,我战战兢兢地上课,为什么?因为我是害羞之人,表演根本不合适我,但因为我坚持学习表演,我才知道,自己永远不会做一名演员。
我在台湾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大学教授表演课,那一两年我都在教学生学习模仿及时间的掌控(Timing)。我常告诫学生,你必须先相信自己,别人才可能相信你。我也说,表演是一种非常抽象的艺术,人人都在表演,但真正的表演则太少了。
【所见略异】
李建军[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一本极端的小说
最近,因为要写《苦难与自由:重估俄苏文学》一书,我重读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这是一本极端性质的小说,会让人产生严重的道德自卑感。
小说中的洛普霍夫为了成全妻子与朋友基尔萨诺夫的爱情,先是制造自杀假象,然后远走他乡。你看,这哪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事情?拉赫梅托夫的“独特的原则”就更极端:他滴酒不沾,不接触女人。为了磨炼自己的意志,他甚至采取比斯巴达式的训练更残酷的方式来折磨自己。有一天,他的房东大娘安东诺夫娜惊讶地发现,拉赫梅托夫身上沾满了血,床上的毡条和床下都有血:“原来毡条上扎着几百枚小钉,钉帽在下,尖端朝上,从毡条中露出将近半俄寸长,拉赫梅托夫夜里就睡在这些小钉上。”然而,作者却将这些“新人”看做是俄罗斯的拯救者,将他们比作“茶里的茶碱,醇酒的芳香”,说他们“是原动力的原动力,是世上的盐中之盐”。
很多年来,一想到拉赫梅托夫的“独特原则”和“血床”,我就很绝望,对自己就很不满:唉,要做这样的“盐中之盐”,实在太难了呀!
现在,我想明白了。拉赫梅托夫这等人,作为文学形象来看,是理念化的,作为实践者来看,是鲁莽的。因而,将他们视为作者的浪漫主义想象的产物,就OK了。
【不知不觉】
钟红明[上海《收获》杂志副主编]
那些未曾面世的
上海为几家杂志编写大事记,同事搬出《收获》合订本开始梳理,1957年7月24日创刊号,三百多页,钱君匋先生设计,可翻到第三期版权页,编委就有变动,原来谁谁当了右派,消失了。
细节会留下时代的印痕和证明。
读到《百年靳以》中靳以先生的女儿章洁思一段文字,说到她家书架上摆放着靳以主编的15期16本《收获》,因为1959年的第2期《收获》有两个版本,前一个版本没有公开出版:“这一期只装了十二本,后即将郭老《蔡文姬》抽出改刊老舍同志的《全家福》。靳以1959.5.6”——这本《收获》连杂志社也无存。
当时郭沫若的《蔡文姬》已经排定印刷,忽然却接到郭沫若办公室打来的长途电话,说还要修改。于是只能匆忙把老舍先生的《全家福》填补上去。当时《收获》属于中国作协,在上海编辑、铅字排版打纸型,然后送去北京印刷。这一下,几位编辑和靳以忙得彻夜不眠。
这么大的动静,郭沫若非改不可的是什么?很想知道。
还有1966年第3期《收获》也未曾面世,杂志社有目录,有封面照片,但这一期并没有出现在市场上,因为,“文革”开始了,《收获》陷入第二次停刊。![]()

凤凰资讯官方微信
视频
-

李咏珍贵私人照曝光:24岁结婚照甜蜜青涩
播放数:145391
-

金庸去世享年94岁,三版“小龙女”李若彤刘亦菲陈妍希悼念
播放数:3277
-

章泽天棒球写真旧照曝光 穿清华校服肤白貌美嫩出水
播放数:143449
-

老年痴呆男子走失10天 在离家1公里工地与工人同住
播放数:165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