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缺乏现代技术支持的情况下,传统帝国是如何实现对山城的有效控制的呢?物质资源匮乏、教化程度偏低的山城又是如何应对帝国权力的呢?山城研究的特殊性及其在全球史视野下的意义由此可见一斑。
2016年4月1日下午,由台湾大学上古秦汉史读书会、明清制度与地方社会工作坊主办的“帝国、边疆、山城——区域史研究座谈会”在台湾大学文学院历史系会议室举办。会议由台湾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阎鸿中老师主持,德国图宾根大学汉学系副教授黄菲、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研究员李仁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游逸飞、台大人类系兼任助理教授黄川田修四位青年学者做专题演讲。
在区域史研究框架更趋细腻、历史学研究提倡多学科交叉的背景下,他们运用方志、碑刻、族谱、简牍、考古遗存等不同的史料,探讨了四个中国历史上的深山小城在选址、资源、交通、军政、历史认同、族群互动等领域产生的问题。
“山城”作为一种帝国边疆,与传统意义上和邻国接壤、由帝国新近开发拓殖的“边境地区”有一定的区别。它们在地理上不一定远离政治核心区,却因为交通条件的局限使得它们与世隔绝。在缺乏现代技术支持的情况下,传统帝国是如何实现对山城的有效控制的呢?物质资源匮乏、教化程度偏低的山城又是如何应对帝国权力的呢?山城研究的特殊性及其在全球史视野下的意义由此可见一斑。而“边缘”转而影响“中心”的研究角度,也是传统中国史研究没有充分挖掘的,由边地山城的建制、运作来讨论帝国中心的发展动态,正是这样的一种尝试。方志、谱牒等史料侧重反映基层社会史变迁,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则让研究者深入民间,与会的几位年轻学者无论从研究的题材还是方法上,都颇为前沿。
黄菲:明清东川府地景改造中随意而为的风水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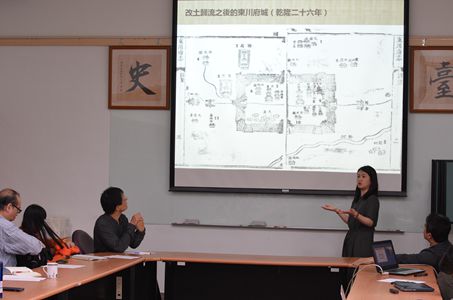
(德国图宾根大学汉学系副教授黄菲报告东川县景观)
首先作发言的是黄菲,她研究的是明清时期云南东川府的地景改造问题。东川府位于昆明市东北部,是彝族六祖分支的所在地。它长期不在帝国的直接统治范围内,明中后期仍由当地的禄氏土司进行管理。至雍正四年(1726)改土归流,它被归入云南省,帝国的力量才逐渐进入。乾隆三年(1738),清朝在此开采铜矿,考虑建城事宜。最先参与计划的官员崔乃镛认为,要在这个被认为是“东故夷獠窟”的地方建立新城,就要舍弃原本的土司驻地,另辟新址。由于滇东北时常面临沼泽扩张、洪水泛滥水的问题,新城被选址在了一个半坡上。根据崔乃镛的风水知识,城池要分成上下半城,所有比较重要的官方建筑都被规划在了山坡上,以彰显天朝权威,而民居、庙宇则应放在下半城。有趣的是,城池规划大功告成之后,崔乃镛就被遣调至他处了,继任的王至、饶梦铭两位官员完全没有落实前任的规划,而将官府、管理铜政的机构都设在了山下平地处,而将万寿宫、商业会馆等民间设施建在了来往不便的半山腰。这说明帝国在边陲城镇的地景设置上并没有固定的模式,天高皇帝远,东川又不同于京、杭这些有传统城建基础的古都,建立新城的风水讲究往往依从于官员个人的喜好,有很大的发挥空间。
在东川府的地景布置上,另值得注意的特征是强烈的军政色彩和杂糅的民族分布。雍正八年(1730)崔乃镛平定当地土司叛乱,请示时任云南巡抚的鄂尔泰有关建城的风水知识,却得到了与当地风水师率先处理土地分配不均、缓和阶层冲突的主张完全相反的命令:加固军事要塞,重视边城在平定叛乱时的应对能力。因此才建成了后来规模更小、布局更加紧凑的东川府城。在城内的田地分布上,多元民族互相交融、汉人彝人比邻而居的情况也很普遍,可见严格的民族隔离政策并没有在南方边区有效开展,清朝在保护满汉等主要民族权益、维护民族关系内部平衡等问题上并不著意,只要求这个“蛮夷之邦”能够维持铜矿运输和政治平稳就好。东川府有壮丽的红土风貌,由中国传统文人风景模式演变而来的“东川十景”,也几乎设立在铜运沿线。东川府在镇边、采矿上的单一城市定位,由它被纳入帝国统治而得到进一步的强化。
李仁渊:福建屏南县的文明改造中帝国如何在场
接下来报告的是曾翻译罗威廉(WilliamRowe)《中国最后的帝国:大清王朝》一书的李仁渊。他以福建屏南县为研究中心,把这座清朝雍正时才建立的新县城中帝国力量的渗透过程做了前后梳理。屏南地区深居福建内陆,本隶属于古田县。此处山多地少,村庄沿河而建,规模非常有限。它的人群变动也很大,人口迁移性强,在明代就经历了复杂的社会变动,文明开化程度很低,官方称之为“夫比匿凶人,结纳无赖,非以强食弱,便以大欺小”。雍正十二年(1734),为加强对福建东南山区的控制,清朝开始在古田县细划行政区,但因交通不便,驻扎官员始终没有进入屏南地区。乾隆元年(1726),首位清朝官员沈锺赴任屏南。他在《屏南县志》中这样描述初来的情形:“每夜猛虎聚于墙外,人烟寥寥不过四五十矣。”尽管有所夸张,但荒蛮程度可以不难想见。
屏南县的改造是以科举为核心、培植地方士绅的过程。沈锺首先开放了屏南的考试名额,用以培养官府可以动员的生员力量,并藉此团结地方势力。从他的生员分布来看,基本均摊给了附近的地方大族势力。此后,他又以“本地籍贯”、“寄屏人士”的划分标准,解决了古田、屏南童生考试争夺籍贯的问题。此举成为他日后遭致地方势力排挤的导火索。尽管沈锺最后因没有处理好官府与地方的关系被弹劾罢官(以致他穷困潦倒、客死他乡),但是兴科举、重教化的风气却在此地保留下来,并成为帝国与山区维持连结的唯一纽带。如地方实力派张步齐通过与官方的合作,在福建内陆贩卖食盐起家,迅速崛起,继而修建祠堂、缮写族谱,成为一方缙绅。这一“文明化”过程与南方诸省,尤其是清代在台湾的开发有许多类似之处。报告人李仁渊指出,通过比较清朝势力进入前后,地方的社会结构、阶层分布、历史认同、记忆型塑等问题,可以清楚地看到国家是如何产生影响力、如何在一个边远山城实现在场(atpresence)的。官方与地方势力的你来我往权利互动,亦有较为普遍的价值。
帝国以科举影响边陲的代表性与内在限度
笔者认为,屏南县这座“山里面的新村庄”,是康雍以来人口激增大背景下,南方各地山区移民垦殖的缩影。屏南县以科举为核心的改造,是帝国在传统地区团结现成的士绅阶层、在新开扩地区培养新的士绅势力以维持儒教型国家的基层统治的典型手段。其中所产生的暴乱频发、官弱民强等问题,亦不过是这种进度缓慢的间接统治建立之初所必然遭遇的情况。

(台大历史系教授、台湾史著名学者李文良 沈雪晨摄)
两场报告之后,台大历史系教授李文良等老师提出了这样的疑问:难道沈锺之前,屏南地区完全没有官方的影响?以科举的进入与否来衡量是否过于单一了些?李仁渊回到道:现有的史料基本是清朝进入以后官方所修的方志,以及各大家族进入文明开化以后自己为自己编的族谱,仅从文字材料记载上看,科举的兴办确实在边区开发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另外,所有做族谱的人都知道它们一追溯祖先就顺接到炎黄尧舜显然是无中生有,但族谱何时开始出现乱接祖先的现象仍然重要。它显示了一种文化资源在何时得以产生,它既有外来的华夏文明认同,也有内部家族发展壮大的需求,两者只有结合起来,才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族谱叙事。并且在细节的操作上,也可以解读出许多资讯。从这个角度来看,分配生员、兴办学校确实是在前近代恶劣的技术条件下,对帝国对边陲几种不多的影响手段。
游逸飞:里耶秦简里的先秦湘西“边城”
接下来的两场山城研究报告都偏向上古史的阶段。游逸飞关于湖南龙山里耶古城的研究十分重要,是因传世文献不足、出土文献稀少,能以当地出土的简牍来研究秦汉城镇的案例显得尤其珍贵。湖南龙山里耶古城位于湖南西部,是沈从文笔下一座典型的湘西边城,至今从长沙出发,还要坐上十几个小时的大巴才能到达。它在秦汉是洞庭郡迁陵县治所所在地,兼负着湘西四大商镇和秦代金、铁、锡开采矿城的功能。从里耶秦简的断简残编里,游逸飞解读出秦代迁陵县有县官三人、人口一百九十余户、规模只有一座学校大小等资讯。以许宏的《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一书中对上古城市的分类来看,里耶古城虽只有一座军事堡垒的大小配置,却承载了地区贸易集散的功能。由于交通高度依赖水路,政令的到达十分缓慢,地方官在行政处置上有很大的发挥空间。在户口收编的记载中,民族融合的现象十分普遍,苗人、濮人被收并的现象很普遍。
城东北郊的墓地分布问题是以往报告人的研究焦点。如图,中央红点为里耶古城,其东北绿点为麦荼战国墓地,西南与清水坪西汗墓地隔水相望,考古发掘者认为麦荼战国墓地里有楚人、苗蛮与濮人,清水坪西汉墓地内有秦人。游逸飞则认为,麦荼墓地的时代可以延期至汉代,它一直被使用,只是埋在其中的族群随时代有所轮替,它背后牵涉到政权转换和人群转移的大问题,非常值得继续探究。另外,简牍中所记载的有关秦朝对外地人、本地人的不同政策,显示出秦在统治六国故地顺应当地习惯法、尊重传统行政权力的倾向,它很好地解释了为何春秋以来到西汉结束的长时段内,里耶地区政权相对平稳、叛乱稀少的历史现象。

(里耶地区墓地分布 游逸飞制)
黄川田修:山东归城的上古巨型遗址令人惊叹

(黄田川修在现场 沈雪晨摄)
最后一位学者黄川田修报告了他前两年的研究《山东龙口归城先秦城址——试读早期中国社会结构》一文。他是当今以考古学、人类学的观念来处理中国上古史问题的典型人士。这篇文章的缘起是他2002年首次去山东龙口市考察,目睹了西周至春秋遗留下来的归城遗址。作为一个日本人,他被保存完好的高高夯土城墙震撼了,在西周时期,此地相较中原已是遥远的边区,那为何出现这样的大遗址呢?
根据此地出土的青铜所具有的精致器型和良好材质做出的考古学分析,黄川田修认为归城是上古时期中原王朝与北方夏家店文化交换青铜的重要流通地。公元前两千年左右的夏家店下层时期,辽河流域产生的铜、锡、锌向各地出口,经大连入渤海,在烟台登陆,过归城入临淄再辗转流入今天的河南地区。由于归城附近缺乏其他规模相当的遗址群,也没有出土任何规格高雅的青铜器,因此他断定归城的统治集团,很可能是从中原的华夏系统国家迁移过来的,外来的统治阶层通过庞大的军镇建设和礼器配置对这一“非中国地区”进行控制,以此垄断这里的交通和矿产。作为周王朝意志的体现,归城的案例证明上古时期的华夏系统国家的扩张边界,黄川田修希望以此回应日本学界提出的“中国早期王朝”概念中有关多元华夏文明起源的问题,以及杜正胜提出的“城邦国家”概念之间的连结关系。

(日本东洋学、考古学专家今日设想的上古中国社会发展模式 黄川田修制)
笔者认为,以上两位学者以较少的材料做了分析上古边城形制、与中央关系的尝试,虽仍就一些具体历史细节的还原上感到困难重重,却不忘回应有关中国上古史的论述中最核心的大问题,十分值得肯定。黄川田修还指出,学者通过自己积累器物的类型学知识制作考古编年的方法,可以用以同文献的记载互为对照,以此在老问题上得出新的发现。相较起来,明清史研究的学者就显得被繁浩的基层史料束缚了,这样不仅容易将历史学研究的眼光局限于某一狭窄时间段和地域中,陷于单一孤立的历史案例,而忘记了对普遍性的、大范围内的问题做出回应的必要,且容易忽略文献以外的器物类型、风土民情所蕴含的历史信息,这样一来,即便走出了书斋,目之所及仍不过是书,而无法进入历史学研究所真正需要的田野中去。
会议心得:在田野中寻找历史?
在此次会议的总结部分,四人各自谈了对此次研讨会的感想。他们都感到彼此研究的问题有所重叠,均以帝国的边陲——山城为切入点,以此研究它与帝国中心的互动。他们都受到了历史人类学方法的影响,所不同的只是关注的时代有所不同。以往的研讨会常以断代来划分会场,研究不同历史时段的学者无法交换意见,因此能给予互相的启发都相对有限。另外,还有学者提出,在研究云南、福建明代以后的情况时,欧洲人的旅行笔记亦是可以参考的史料。
然而,此次会议在研究的方法和主题上虽称得上时髦,却显示出当前历史学研究存在的一些问题。以两位明清史研究的学者为例,首先,接触大量的方志、族谱等基层社会史料固然可以辅助还原过去重视不足的社会史变迁,却容易忽略推动古代历史发展最重要的先导性因素——思想观念。尽管宋以后,平民阶层不断崛起,文化大众化倾向日趋显著,但古代社会的精英性格仍是基本不变的。方志、族谱的编纂修订者因缺乏与帝国精英的互动,在地方或家族史的书写中能够呈现的帝国经营理念有限,仅从这些文献里,是不足以体会清朝何以要将帝国统治的触角延伸至前朝从未涉及的地区的。历史学家将视角仅限于此,便无法解读出帝国在维持自身正统性、扩张疆域范围、伸张天下型国家治统与道统的复杂考量,也会与深受宋明理学熏陶的明清学者型官僚拉开距离,从而无法将区域的历史进程同帝国的演变发展做全面互动的考量。
其次是由此而来的,在地方史研究中缺乏对历史学理论架构的回应,因之无法建立更具涵盖性的解释框架的问题。比如像东川、南屏这样新兴城市的开拓,对于施坚雅(WilliamSkinner)以四川盆地为模型提出的传统中华帝国六角形城市结构,具有丰富的补充意义。它们或深居内陆,或远在边疆,或以传统儒教手段整合,或凭简单的军政控制,并不能与周边的都市群形成有效的往来。它们在帝国中处于何种位置?发挥了怎样的功效?在接下来的现代国家转型面临怎样的处境?这些都是可以注意却没有被充分讨论的地方。缺少了这些解释框架,研究难免陷入琐碎信息的采集,或是对一个人们闻所未闻的山城进行旅游简介的境地中去。
最后是关于田野研究的方面。当历史人类学已经成为一种时髦,历史学家下田野就不再是针对文献材料不足时所作出的适当补充,而成为整个历史学研究的先导性方法了。不得不说,在学习他者语言、深入掌握当地人生活形态、建立一个异域社会完整模型的能力上,历史学家远不如正统人类学者;在展现对人情世故的细腻观察、表达对乡土生活的深厚情怀上,历史学家又绝不像是文学作家一样敏锐深刻、洞悉人性。深入田野固然有很大的好处,但当它变成你用来说服对某一地区闻所未闻的人的唯一理由,就显得苍白无力起来。无论如何,对历史学来说,田野仍应是一种补充和辅助,否则就会丧失学科的最大优势——对史料的掌握和分析、对过去人群思想观念的体认和理解。
(凤凰历史特约通讯员沈雪晨独家报道)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凤凰网保持中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