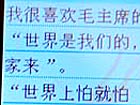使馆的同志们来到凯悦旅馆时,大约是凌晨5时。大家都不肯回房间,坐在前厅里等候使馆那边的消息。我想,经过这突如其来的灾难的震撼,又感受丧失亲爱的同志和朋友的苦痛,目睹自己赖以生存的使馆遭到摧残,拖着紧张拼搏之后疲惫不堪的身躯,当前最需要的是精神支撑。我把同志们召集在一起,对大家说:今天我们的使馆遭受浩劫,这样的事情以前谁都没有经历过,对每个人都是第一次。既然灾难已经降临,我们要挺起胸来,迎接这一挑战。同志们,使馆被炸塌了,但是我们的意志不能垮。党中央、祖国人民非常关心我们。中央已经决定派特别小组乘专机前来处理善后事宜,接回烈士的遗骨,伤员也将回国内治疗,部分同志可能回国休整。我要求大家回房间休息,明天大家都要打起精神,还有许多善后事宜等待处理。
在我的劝说下,同志们陆续回到房间休息。而此刻,最让我揪心的是武官任宝凯仍下落不明。刚出危楼时,我听武官处的同志说,他们从楼上向下突围时,听到了任宝凯的声音,估计他已经出来了。可是,在营救同志的时候,却不见他的踪影。同志们猜测,他可能受了伤,已被送到了医院。我们分别给几个收治中国使馆伤员的医院打电话,都说没有此人。使馆里没有武官,伤者里也没有,那就还有一种可能:牺牲了。但是,没有弄清事实之前就不能下结论,也无法向国内报告。国内有关部门已经再三来电话催问武官的下落。
为了弄清事实究竟如何,在当时使馆已被封锁的情况下,只有到急救中心太平间去查。我带上翻译,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郭志嘉开车,前往急救中心。
虽然已是凌晨,整个城市仍笼罩在黎明前的黑暗里。我们在漆黑的街道上穿行,没有灯光,没有人影。郭志嘉是学塞尔维亚语的,是南斯拉夫通,对贝尔格莱德市很熟悉,否则在这漆黑的夜里是难以辨别东南西北的。
我们来到急救中心,向值班的负责人说明来意。他回答说,要到太平间找遗体,必须经院长批准,院长7时半来医院上班。我看了一下表,还不到6时。我急了,说我们不能等,今天是特殊情况,请你马上打电话给院长,允许我们即刻到太平间探查。值班医生答应打电话给院长,但告诉我们说,即使把他叫醒,他驱车赶来仍需要时间,请我们在会客室稍等。我决定利用这个时间去看望一下伤员。医生带我们走进急诊室,我们看到医生已经对伤员做了紧急处理。曹荣飞眼睛蒙着绷带,昏昏入睡。刘锦荣满脸绷带,跟我说话时仍感到呼吸困难,伤口疼痛。郑海峰头部和颈部都缠着绷带。只有刘新权说,这里他伤势最轻,只是脚扭伤,很快会恢复的。屋子里很黑,借着微弱的烛光,勉强能看清伤员的脸庞。我带着十分沉重的心情离开急诊室。
回到急救中心的会客室,院长还没有来。再三催促,院长终于来了,并把我们领到太平间的走廊。但管理人员不让我们进去,说不方便。他们进去寻找,并稍事整理,把三位烈士的遗体放在小车上推了出来,他们是邵云环、许杏虎和朱颖。这是悲惨的死,壮烈的死,英雄的死。几个小时前,我们还曾相见,我们还曾谈论时局,而现在竟是阴阳两隔,竟是诀别。我的心,像被一只大手攥紧,是疼痛,是酸楚,是挣扎,是休克。此刻,我无暇多想,痛哉死者,惜哉生者。我还心系着有生还希望的一个下落不明的人。太平间的管理人员告诉我,除了这三人外,太平间里再没有死亡的中国人。那就是说,武官还在使馆里。我马上用手机把查看到的情况告诉在使馆前守候的李银堂,让他请消防队员帮助进楼内寻找。我们马上赶回使馆。
天阴沉沉的。虽已清晨,几缕吝啬的晨曦从云层里透出,黑暗仍在游荡,不甘消退。我们来到使馆楼前,警报尚未解除,守护使馆的警察仍然把守着门口,不允许进出。我告诉他们,我们的武官还在楼里,生死不明,我要进去找他。消防队员也过来阻止我们。我请他把头盔和手电借给我,我要亲自去找,准备闯进去。这时,在楼前守候的李银堂参赞告诉我,消防队员在楼里发现了一个人,还活着。他们说,你们即使进去,也背不出来,还是请急救车来。他们立刻和急救中心联系,急救车风驰电掣而至。不一会儿,从里面抬出一个人,正是武官任宝凯。我马上走上前去,看见躺在担架上的武官满面尘土,没有伤痕,呼吸却很艰难,嘴和鼻子里呼出很多泡沫。武官还活着,武官没有死!急救车载着他向急救中心疾驰而去。
| 您可能对这些感兴趣: |
|
|
请选择您看到这篇新闻时的心情
[查看心情排行]
| 感动 | 同情 | 无聊 | 愤怒 | 搞笑 | 难过 | 高兴 | 路过 |
| 已有0位凤凰网友参与评论 | ||
|
作者:
潘占林
编辑:
蔡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