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奎松革命的真话

“说真话”不是我的研究特点,而应该是一切历史研究的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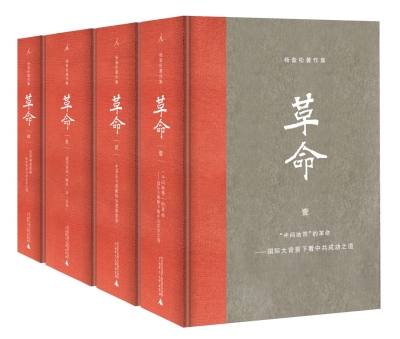
杨奎松著作集:革命
作者:杨奎松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2年7月
页数: 2644
杨奎松
革命的真话
作为顶尖的中国现当代史研究学者,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杨奎松的言行,向来备受海内外学者和读者的关注。近日,杨奎松推出了研究中国现代革命的四本著作合集——《杨奎松著作集:革命》。杨奎松同时宣布,在这部总结之作推出后,他对于中国革命的研究将从1949年以前过渡到以后。而这样的研究转型,无疑将让他再度成为学界的关注焦点。3日,读+通过电子邮件专访了身在美国的杨奎松教授。
记者欧阳春艳
实习生刘露
关于著作
“离开了国际大视野,不了解近现代中国革命背后苏联作用的情况,就不可能了解中国革命。”
毛泽东的﹃中间地带﹄
读+:这次出版的《革命》一书,其实是您4部著作的合集。您的著作还有不少,仅选择《“中间地带”的革命》、《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和《西安事变新探》这四本书结集,是出于怎样的考量?这次再版,在内容方面有什么新的修订吗?
杨奎松:选择这四本书主要是技术上的考量。一是它们都是研究同一个时期、同一个问题的成果;二是它们都是专著,不是论文结集,体例一致;三是它们都经过修订,亦即都比较成熟一些;四是它们都是还在市场上发行的书,不是新版,也不是新修订的书,否则按规定就要重新送审。最初这套书中还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一书,由于该书需要修订,即需要重新送审,最后还是取消了。也因此,这四本书再版,除了技术上或文字方面的问题需要处理者(特别是《恩怨》一书)外,内容方面没有新的修订。
读+:有人把您的《“中间地带”的革命》称为民间版中共党史,您认同这种评价吗?“中间地带”这一提法是您自己的创意吗?
杨奎松:我认同。《“中间地带”的革命》一书,基础是我在人民大学任教时给研究生上课的讲稿。我当年拟稿的初衷,就是想换一个不同于官修中共党史的角度来讲述这段历史。“中间地带”不是我的创意,是我取意毛泽东1946年提出的一个概念。它当初的意思是说中共革命有它自身的规律和需要,作为介乎美苏两强之间中间地带的革命,不必完全依照美苏的意志行事。
读+:研究中国革命,人们更习惯于将它视为由内因促成,并由中国人独立完成的一项事业,但您在研究中却一再强调应该把中国革命置入更为广阔的国际视野中来看?
杨奎松:我的这几本书里都回答了这个问题。无论是中共的形成、发展与成败的经过,无论是毛泽东在中共党内逐渐成长到最终崛起,也无论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分分合合,包括像西安事变这样表面看起来只是国民党内部地方派系和中央势力间个别冲突的小小的案例,都无不是在地缘政治和国际大背景影响的条件下发生的,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与中国毗邻的苏联及其共产国际的作用与影响。事实上,离开了国际大视野,不了解近现代中国革命背后苏联作用的情况,就不可能了解中国革命。
读+:有人说,美国革命是最理想的革命,流血很少,破坏力小,留下的遗产丰厚而稳固;但也有看法认为美国是个极端的特例,美国不可复制,美国革命更是不可复制。您怎么看?
杨奎松:任何革命就像任何历史事件一样,都是有条件的。因为历史上几乎没有任何革命可以拥有和别的革命完全一样的条件,因此任何国家的革命恐怕都很难复制。美国革命的最重要的背景条件是它是由来自欧洲的大批移民构成的,具有复杂的族群、文化、政治关系的13块英国和西班牙殖民地共同发动的。因为都是移民,因而具有共同的对自由权的追求与向往;因为是13块殖民地自愿结合的共同反抗,因而这种结合中必须保证每块殖民地参与方的平等地位和自主权利。英国虽然是欧洲主要列强国,它的兵力用来对付一两块美洲殖民地的反抗尚可,用来对付结合起来的13块殖民地这一庞大力量,自然没有可能了。凡此种种条件,当然无法复制。
关于“党史”
“党史并不是真讲历史,而是旨在研究正统理论资源,反映官方意识形态,指导中国一切近现代史研究,包括指导中国政治理论研究。”
作为现当代史的
中共史
读+:您一直不认为自己是一名党史学者,强调自己是一名历史学者,您认为两种称谓的区别在哪儿?
杨奎松:长期以来在大陆的所谓“党史”,从来是特指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不含国民党,不含其他党派的历史。只不过,这一“历史”并不是真讲历史,而是旨在研究正统理论资源,反映官方意识形态,指导中国一切近现代史研究,包括指导中国政治理论研究。也就是说,它和历史研究其实没有什么关系。我强调自己是历史研究学者,原因就在于此。因为我研究的是中国现当代史和作为其中一部分的中共史,如此而已。
读+:现在思想界兴起一股民国热,不仅民国人物广受推崇,也延及典章制度。您怎样看待民国这段历史?民国留给当今的遗产和资源是什么?当下这种对于民国的缅怀乃至向往,您怎么看?
杨奎松:民国史虽然延续了中国晚清以来的屈辱、落后与混乱,但它同样也延续了中国的种种传统及其社会文化。民国历史虽然处于中西文化交融,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西化的转变过程中,但民国中精英人物无不在为保留和延续传统中华文化而努力,并且产生了大量今人只能望之兴叹的中西文化合璧的代表人物。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将这一传统延续与文化传承逐渐中断,造成了严重的历史断裂。今人对民国及其民国人物的缅怀乃至向往,很大程度恐怕是反映了对现实文化现象的不满与遗憾。
读+:在您的研究中,您经常会选择从历史人物入手,比如您对孙中山、毛泽东、蒋介石等等,都有独到的观察与见解,但似乎您对这些历史人物的评价也会惹出争议?如果可能,可以在这里用简短的微博体,给我们说说您对这几位历史人物的评价吗?
杨奎松:第一,他们都是中国近代的革命者;第二,他们都曾在中国近代革命过程中起过举足轻重的历史作用;第三,从孙中山,到蒋介石,到毛泽东,三个人继往开来,他们的成功与失败,其实反映了中国革命三个阶段的重要历史特点。
关于“真话”
“我用历史研究的方法去还原真相,其实这是我的工作职责所在。”
不是不信?
不轻信
读+:您对现在仍然比较热门的口述历史,似乎持怀疑态度?
杨奎松:不对。口述历史对今人了解历史的大量细节和鲜为人知的幕后情况,对于历史研究者体会历史场景,其实是一种很好、且不可多得的补充。只不过,口述历史和历史人物的回忆录一样,都不能轻信,必须要综合第一手史料加以印证,以便去伪存真。
读+:在研究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时,您甚至对毛泽东本人的有些回忆也表示不能完全相信?
杨奎松:科学研究早已证明,任何人的记忆都是有选择的,没有人能把什么事情都记下来,更不用说他不喜欢、不想记的事情了。政治人物的回忆更会有很强的选择性,而且常常会受自己情绪或意念的影响,发生误记。我在面对毛回忆中的说法的时候,既不会轻信,也不会不信。我的办法是找当时的第一手史料和其他相关人的回忆资料比较分析,用其可信者。
读+:很多人评价您的历史研究,最大的特点就是“说真话”,这是您的研究准则吗?
杨奎松:这应该不是我的研究特点,而应该是一切历史研究的目的,即要把历史上真实的一面努力呈现出来。我用历史研究的方法去还原真相,大家以为我有什么不同,其实这是我的工作职责所在。
关于写作
“多读书,多读各种不同说法、不同角度看历史的书。读的书越多,对事物的鉴别力就会越高,至少会变得不那么盲从。”
无人知晓?
历史就失去意义
读+:您坚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写作,有些著作甚至有“侦探小说”的感觉,但也正因为如此,有些人对您作品的权威性、学术性产生了质疑,您如何看待这些不同声音?
杨奎松:我还真不知道我的哪本书会给人以读“侦探小说”的感觉,我知道不少读者对我的写作还是不很满意,认为写得太深太专业了。但在历史学界,我想我大概还算得上比较注意让研究成果变得通俗易懂的学者之一吧。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认为历史研究着力于揭示真实的过去,就是要让广大读者了解,否则就失去了意义。把历史写得诘屈聱牙,变成只能给极少数专业学者把玩的东东,不是我的目的。
读+:现在的中学历史课本,似乎有不少内容都和学界的研究成果背道而驰,因此不少中学生进入大学重新学习历史之后,会产生很大的颠覆感。作为一名大学教授,同时作为一位历史学者,您对年轻人有何建议?
杨奎松:我对年轻人的唯一建议就是多读书,多读各种不同说法、不同角度看历史的书。读的书越多,对事物的鉴别力就会越高,至少会变得不那么盲从,知道一件事情可能会有不同的说法、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观点,不那么容易轻信。
读+:大家都认为您在这样的年纪就在历史研究领域取得如此成就,非常不易,能透露一下您未来的研究打算吗?
杨奎松:这个年纪取得这样的成绩,在其他学科算不了什么。历史研究取得成绩比较困难,在于我们大部分的时间其实不是在写作,而是在国内国外,在一个一个省、市、县地跑档案馆,查找资料。一篇论文的资料往往可能来自好几个省的档案馆、图书馆,或者是找许多当事人访谈过。很多历史学家,一辈子也不过就出了一两本书、两三本书,原因就在资料的查找和爬梳太困难了。我下一步的研究仍旧会继续在中国革命史的范围内耕耘,但主要的精力将会放到1949年以后。
记者欧阳春艳 实习生刘露
7月22日,一场有关《杨奎松著作集:革命》的新书座谈活动在北京798艺术区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举行。这场以“直面中国革命”为题的活动,吸引了诸多中外学者和史学爱好者前来座谈,为的是从杨奎松这里出发,直面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革命”。在现场,学者雷颐直言:“杨奎松在学术上最大的贡献是把党史从法学变成了史学。”
事实上,作为海内外公认的研究中共党史的顶尖学者,杨奎松的历史研究之路曲折而又充满传奇色彩。
1976年周恩来去世后,年仅23岁的杨奎松因为一首“黑诗”,卷入了“四五事件”,也因此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并入狱半年之久。1977年,杨奎松出狱,参加了高考,进入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专业学习。“这个党史专业,并不是史学的一个门类:既非史学,也非政治学,被划在政治理论专业,毕业时学位证书上却写的是‘法学’学士。”杨奎松由此走上了历史研究之路,“因为党史的学习,使我对许多历史问题发生了兴趣。”
大学毕业后,杨奎松进了中央党校的《党史研究》杂志做编辑。在这里,杨奎松有机会进入保存党史资料最重要的单位——中央档案馆,这对他后来的研究无疑起了重要作用。
整个1980年代,杨奎松的主要精力都放在查阅搜集各种文献史料上面,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电脑可用,他光是手抄卡片就做了数万张。将近十年的资料积累与研究,使他在后一个十年,接连发力。从1991年开始,他接连推出了五六部专著,轰动了学界。
有读者将杨奎松称作中国现当代史学界的“福尔摩斯”。杨奎松也曾承认,自己研究历史的一个极大的动力是“破案”。他说:“历史研究有点像刑警破案,通过种种蛛丝马迹,深入发掘拓展,找到更多的线索,运用逻辑分析和推理,把所有能够掌握到的历史碎片串连拼合起来,最后常常能够发现一幅让人吃惊的历史画面。”
杨奎松坚信,抛开历史中的恩怨是非,我们要发现历史真实并非没有可能。因此,他的研究常常会引起一些争议和深思。比如谈及抗战,他认为抗战史的宣传和介绍不能“报喜不报忧”,只讲团结抗战,不讲磨擦冲突,只讲过五关斩六将,不讲关公走麦城;再如孙中山当年和日本人谈合作的史料被外国学者披露出来,他就冷静指出,在历史著作中以“爱国”或“不爱国”作为一种道德尺度,用以评判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政治斗争各方的是非优劣,是一种极不科学的做法……
除了寻找历史的真实,杨奎松更注重现实的关怀。他常说:“我非常关心的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社会怎么来的,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一切,我们所面临的这一切,无论成功的地方,失败的地方,所有这些状况到底是怎么来的。要回答所有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要先回到历史当中去。用大量的史料来分析、讨论历史是怎么发生。如果没有一个深入的讨论,我们没有办法回答当下所存在或者所发生的,包括我们今后可能会存在发生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我的志向是希望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重新写一遍。但经过了30年的时间,我也就刚研究到1950年代。下面,我将全力以赴地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在《革命》的首发式上,年近六旬的杨奎松透露心愿。
为您推荐
算法反馈精品有声
热门文章
精彩视频

凤凰资讯官方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