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青年:敢不敢换种活法?

“中国最著名的屠夫”陆步轩用了23年的时间,来摆脱自卑心理、回归北大的讲堂。身价40亿的“土猪大王”陈生也曾卖过菜、卖过白酒、卖过房子、卖过饮料。如果不按常理出牌,与流行的成功学逆行,如今的青年一代又能否承受这自主选择的代价呢?
陈曦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学生/凤凰评论特约评论员
“2011年,他是一个PHP工程师,和弟兄们奋战到午夜为了新浪微群2.0上线;2013年,他离开IT业,华丽转身成一个水果店老板。几个月后,眼镜摘了,人变白了,连头发都长出来了。”这位叫徐佳的年轻人,因为毅然选择换一种活法而火了。
“毕业即失业”的恐惧、“剩女”的焦虑和“凤凰男”的自卑,不辜负长辈殷切期望的负累有如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头顶。校园里高谈阔论的理想和激情,也在接触现实的那一刻被社会这所学校驯服。在个体力量难以与社会压力相抗衡的时候,精神生活去道德化的调侃与戏谑便是向外部世界妥协的必要调节了。
他在自己的微博里解释道:“做程序员做了五年,由于头儿的栽培提拔,也由于几分运气,终于评上了相当于架构师的职级。看着职级上面的title,不禁热泪盈眶。这么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奈何物随心转,境由心生,我却想追寻一下另外一个自己。现在我辞职了,在卖水果。”如今他水果生意红火,有时间游泳,知道每天应该花点时间让自己静一静,少一分喧嚣,多一分思考。央视新闻的官方微博在转载后提问:“追寻一下另外一个自己,你有这勇气吗?”
【敢换一种活法的人不会太多,还总是备受煎熬】
“我给母校丢了脸、抹了黑,我是反面教材”--时隔23年,北大中文系校友陆步轩第一次接受母校的官方邀请站上讲台,说完这第一句话,几乎哽咽。而据《中华工商时报》的报道,陆步轩的眼镜肉铺一年可以赚20多万,挣得比母校北京大学一个普通教授都多。
另一位受邀与陆同台演讲的陈生则说:“北大学生可以做国家主席,可以做科学家,也可以卖猪肉。”他1984年从北大政治经济系毕业,放弃体制内的“铁饭碗”主动下海经商,如今已成为身价40多亿的“土猪大王”。
陆步轩和陈生都是相当长时间的社会新闻人物,而且都是因为“北大高材生+卖猪肉”模式为人所知。2009年8月,陈生邀陆步轩到广州,提出开办“屠夫学校”。一个是中国最著名的屠夫,一个是中国土猪大王,两个“卖肉佬”一拍即合,由陈生出资办学,陆步轩为屠夫学校编写教材,内容涉及市场营销学、营养学、礼仪学、烹饪学等学科,联手成立了中国第一家培训专业刀手的“屠夫学校”,希望培养出来“通晓整个产业流程”的“高素质屠夫”。
从文科状元、北大高材生到屠夫专业户,在陆步轩的个人历程跌宕起伏的同时,社会舆论的价值评判标准也摸索着从“读书无用论”到“行行出状元”的转变。
人类学家阎云翔曾指出:中国社会的生活理想正在日趋扁平化和单一化。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认为上海和北京的生活方式是好的,必须设法改变自己以便过上北京、上海式的生活。他指出:“由于大众媒介的影响,一位生活在边远山区的农村姑娘对于消费的认知和大城市里的女孩子没有多大区别,但是,二者实现消费欲望的手段和可能性却有天壤之别。渐渐地,中国人的生活理想变得越来越扁平化,名牌、奢侈品成为一大批人定义自我的途径。同时,实现这种日益单一化的理想的途径又充满激烈竞争,等于亿万人争过一座独木桥。最为明显的是,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大学生都希望成为白领,特别是到外企工作,但现在的大学生纷纷去做公务员,回到体制内。相比之下,欧美人对‘好生活’有着更加多元的理解。”
陆步轩用了23年的时间,来摆脱自卑、回归北大的讲堂。陈生卖过菜,卖过白酒,卖过房子,卖过饮料。
徐佳在微博里则有这样一段话:“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我不去想能否赢得爱情,既然钟情于玫瑰,就勇敢地吐露真诚。我不去想身后会不会袭来寒风冷雨,既然目标是地平线,留给世界的只能是背影。我不去想未来是平坦还是泥泞,只要热爱生命,一切,都在意料之中。”徐佳说这是小时候读汪国真的诗,至今记忆犹新。
如果不按常理出牌,与流行的成功学逆行,如今的青年一代又能否承受这自主选择的代价呢?
【从“人生路越走越窄”的喟叹到“谢室友不杀之恩”的戏谑】
1980年5月,一封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这位23岁的年轻人并不期望从编辑同志那里得到什么良方妙药,只是在走过一段“起于无私的源头而最终以自我为归宿”的思想长河后,将她“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的思考结果披露出来,愿意让全国的青年看看。因为她相信“青年们的心是相通的”。
让年轻的潘晓感到从希望到失望再到绝望的原因无非是:“我相信组织。可我给领导提了一条意见,竟成了我多年不能入团的原因……我求助友谊。可是有一次我犯了一点过失时,我的一个好朋友,竟把我跟她说的知心话悄悄写成材料上报了领导……我寻找爱情。我认识了一个干部子弟。他父亲受”四人帮“迫害,处境一直很惨。我把最真挚的爱和最深切的同情都扑在他身上……可没想到,”四人帮“粉碎之后,他翻了身,从此就不再理我……为了寻求人生意义的答案。我请教了……可没有一个答案使我满意。”
这些问题困扰着23岁的年轻人,也困扰着80年代的中国社会。这篇读者来信最终在1980年的夏天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内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
那些曾经困扰潘晓的问题,在如今的新新青年们看来,也许会一脸无所谓地说,“人生的路越走越窄,这是个问题么?”
周星驰的《大话西游》热映之后,“爱一个人需要理由么?不需要么?需要么?……”成为少男少女之间的经典桥段。对于“一切皆能调侃”的80后、90后来说,爱都不需要理由了,其他还算什么问题?在复旦投毒案之后,对于青年一代个体间关系的深思,很快就演变成一场“谢室友不杀之恩”的戏谑与狂欢。
每一代人的青春往往跟时代背景、跟社会的发展阶段同构。美国也曾有“迷惘的一代”、“垮掉的一代”。海明威在小说《太阳依旧升起》中塑造了“迷惘的一代”(Lost Generation),指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包括海明威在内),他们因为战争的创伤对生活失去信念,但并未因此而失去对人性的渴望。而其后“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或称疲惫的一代)则完全不同。这个二战后出现在美国的一群松散结合在一起的年轻诗人和作家的集合体,以玩世不恭、浪荡公子为典型特征。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丧失了对人性的最基本的理解。“垮掉的一代”这个标签原本表达了公众对他们的失望和不满,形容词“beat”一词有“疲惫”或“潦倒”之意,然而杰克·克鲁亚克却将其与音乐中“节拍”的概念相结合,赋予其新的含义“欢腾”或“幸福”。这样,连失望和不满、疲惫与撂倒,也是无所谓的甚至是“欢腾”的事儿了。
诺曼·鲍德赫雷茨是专门研究“垮掉的一代”的重要批评家。在1948年他出版的《一无所知的波西米亚人》一文中他如此评价“垮掉的一派”:“50年代的这些玩世不恭的人们是文明的敌人。他们崇拜原始主义,他们崇尚天性、活力和血腥。这是来自弱势群体的精神反抗行为。”
梁文道曾撰文分享他与这种“玩世不恭”正面交锋的经历:“在香港出版社负责面试年轻人的时候我问过他/她们:你有什么嗜好?他们会说:‘睡觉’。Ok,那我说,你平时的休闲是什么?‘睡觉’。啊?‘睡觉’怎么能成为嗜好呢?对于我这一代人很难理解的。我继续问:那你要来我出版社工作,平时看些什么书?‘我不喜欢看书。’‘可是我们是要出版书的。’他说:‘那我出书就好,出书不一定就要看书,我出书是要给别人看。’”
“这些答案匪夷所思的地方在哪里?前十年、二十年,年轻人可能会说谎,他/她可能不大爱看书,但是他/她可能会说:我最喜欢《战争与和平》,莎士比亚,《红楼梦》等等。但现在的年轻人是不骗你的,很坦白。换句话说,他不觉得这是问题。”梁文道分析道。
梁文道认为,台湾、香港、日本已经走入一个相对稳定、甚至衰老的社会,而大陆还在往前,窗户很大,我觉得这会影响年轻人对自己的看法,对未来的看法。“香港回归之后香港年轻人现在接触到很多大陆来的年轻人,奇怪的是,当他/她发现这些大陆来的同学或者同事,那么努力,那么有志气,那么优秀的时候,他/她不会想说我和你们拼了,他/她会说,那我就算了,好累。”
【拿什么来拯救你,被成功学绑架的青春】
事实上,大陆的年轻人也正一步步走上相似的道路。
“新世代青年将成为压力最大的一代青年”--《新世纪中国青年发展报告2000-2010》的研究显示,当代社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教育压力、就业压力、购房压力、婚姻压力、成家压力等全面交织,来源于社会各方面成本的激增,使得新世代青年是在各种压力交织中成长发展的一代。“不成问题”不等于“没有问题”。如今的80后、90后遇到的生存困境甚至比潘晓严峻得多。
年轻的潘晓中途辍学后,被分配在一家集体所有制的小厂里。而2013年的大学生们却正在遭遇“最难就业年”——“全国今年将有普通高校毕业生699万,比去年增加19万,再创历史新高。在毕业生求职高峰期中,中文、历史、哲学等人文社科类专业明显遇冷。到目前为止,广东2013届毕业生签约率仅30%,较之去年同期下降了10个百分点,就业形势较2008年更为严峻。”《经济学人》更是以“失业的一代”为封面报道,指出全球失业青年的总人数几乎相当于美国的总人口。两相比较,潘晓的那个“集体所有制的小厂”简直是求之不得的“铁饭碗”了。
从“美人爱英雄”、“佳人爱才子”到“宁愿在宝马里哭,也不在自行车上笑”,从“书中自有颜如玉”到“有多少‘凤凰男’的心灵孤独荒凉”--唯利是图的择偶观,是当代中国年轻人为人诟病的另一面。
在“自由恋爱”的旗帜下,爱情之路越走越窄,婚姻似乎越来越直奔交易而去——以最小成本换取最大收益。恋爱、结婚失去了价值上的神圣感,“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成功故,一切皆可抛”。
“我的人生是一栋只能建造一次的楼房,我必须让它精确无比,不能有一厘米差池。”这是近期的影院宠儿《致青春》中,男主角一直强调的一句话。他放弃了初恋以及不错的工作机会,为了所谓的“成功”出国留学,甚至为了得到绿卡而结婚又离婚。若干年后的他终于明白自己“事业的成功是用做人的失败换来的”。
电影中塑造的男主角是标准的“凤凰男”,虽然家境贫寒但读书用功、上进心强、成绩数一数二。时评家十年砍柴认为,城市长大的“孔雀女”与“凤凰男”种种矛盾的根源恰恰在于社会流行的“成功学”。十年砍柴回忆起自己刚在北京定居的前几年,“担心妻子瞧不起农村来的父母,担心自己的成就让父母失望,有时候对老家亲戚一些求助电话很恼火……”“很多‘凤凰男’,一旦走向社会,特别是成家后,会发现自己实在太平凡了,平凡到在一个普通市民面前也可能会有自卑感的地步。”
奇怪的是,批评年轻人自由恋爱、唯利是图的长辈们也恰是“每逢佳节就逼婚”的主力群体。有多少心灵孤独荒凉的“凤凰男”,有多少“宁愿在宝马里哭也不坐自行车”的虚荣女,不恰是丈母娘和婆婆逼出来的?
“毕业即失业”的恐惧、“剩女”的焦虑和“凤凰男”的自卑,不辜负长辈殷切期望的负累有如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头顶。在这种境况之下,涌入体制内、争得“铁饭碗”成为了工具理性权衡的结果。校园里高谈阔论的理想和激情,也在接触现实的那一刻被社会这所学校驯服。在个体力量与社会压力难以抗衡的时候,精神生活去道德化的调侃与戏谑便是向外部世界妥协的必要调节了。
为理想而坚持?为爱情而等待?为独立自主而特立独行?“算了,好累”。
不如花几十元到影院里缅怀一下青春。短短几天,《致青春》的票房已过3亿。缅怀青春的人用消费青春的方式,加速了青春的“终将逝去”。 转载请注明出处


带女儿练摊 讨到公道又如何?
他们欠下的法治债、感情债,不只什刹海练摊的9龄童这一个。他们欠下的,是整个社会。这是一个按身份站队的时代,不是以法理站队的时代。[详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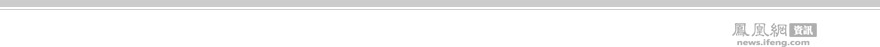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凤凰网保持中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