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曼德拉:成就伟大的牢笼

曼德拉在他不自由的国度里所居住的“牢笼”已被幻化为浴火重生的浪漫场所,并演变为成就所谓伟大却又缺失核心意义的符号,其间对于今日中国人最具意义的镜鉴反倒是对“暴力革命”思维的根本否定。
葛霖 凤凰评论特约评论员
“南非终身名誉总统”“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纳尔逊•罗利赫拉赫拉•曼德拉(Nelson Rolihlahla Mandela)先生于南非当地时间12月5日逝世,部分具有官方背景的中国研究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将他描述成一位具有宗教性“圣徒”气质的非洲民族主义者。
20个月前,曾释放曼德拉并宣布解严的南非最后一任白人总统弗雷德里克•威廉•德克勒克(Frederik Willem de Klerk)在一次演讲中声称曼德拉“一点也不像今天广泛描述的那个慈爱又圣洁的形象”,国内某官方新闻网站将这篇译自《每日电讯报》的消息命名为《南非‘黑人’前总统称曼德拉无情又不公平》,这个有趣的常识性错误足以管窥肤色与种族在中国式评价机制中的重要作用。1993年10月15日,曼德拉与德克勒克因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制度而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然而今日中国却绝少有人了解这一事实。
当部分中国“公知”欢呼昂山素季恢复自由的同时,他们的反对者纷纷激烈指出昂山素季的父亲是与日本合作的“缅奸”……这种现象无疑是今日中国许多社会讨论不能完成的根本——参与者们往往极易冲动并且没有一个公认的知识话语平台,更缺乏一如曼德拉式的建构者。
在中国由社会变革胜利者制定的历史逻辑中,是否英雄的核心判断标准是行动以及行动带来的效果。迄今仍被保留在义务教育历史教科书中的唐代起义者黄巢,曾因滥杀无辜而为其身后1000年的历史评价所不齿,但他在今天的某些语境下却仍然可以被歌颂为一个可敬的英雄。而黄巢的“题菊花”诗中曾有“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的表述,堪称成王败寇思想主导下对政治利益狭隘认识的真实写照。
1964年,杭州师范学院学报一篇署名“杭景秋”的题为《南非种族歧视的根源是阶级压迫和剥削》的文章中声称“南非人民懂得只有用暴力革命来反对殖民者的暴力镇压,才能获得解放,1961年底以暴力斗争为主要手段的‘民族之矛’诞生了”,在远隔中国万里的南非,那里的暴力组织再一次被赋予基于效果的期许,而忽视了作为“主要手段”的暴力。曼德拉是“民族之矛”组织的总司令,次年(1962年)8月,时年43岁的曼德拉被捕入狱,南非政府以“煽动”罪和“非法越境”罪判处他5年监禁。1964年6月,他又被指控犯有“企图以暴力推翻政府”罪,改判为无期徒刑。由是,曼德拉开始了他长达27年的牢狱生涯。
1989年8月4日,时任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先生在津巴布韦哈拉雷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呼吁“立即释放南非黑人领袖纳尔逊•曼德拉和其它政治犯”,是时,国际社会对地跨亚非两洲的中国与南非都抱有强烈的好奇心。恰在此时,曼德拉从“总司令”到“政治犯”身份的蜕变,让中国人习惯的评价体系无所适从,当曼德拉走上了一条完全区别于海尔•塞拉西一世以及穆巴拉克之流的道路,当面壁而不图破壁的坚忍与力行被更多中国人所了解,“圣徒”以及对曼德拉纷至沓来的赞美变成了主流。这种评价亦为西方所接受。
时至今日,我们仍然不能基于现象准确指认撒切尔夫人对曼德拉“恐怖分子”称谓的转变契机,但在被越来越多中国人所接受的所谓西方价值观中,曼德拉的地位业已上升到普通政治家所不能企及的高度。
《每日电讯报》持续着对曼德拉关注的热情,该报2012年的一篇文章提及“到上世纪80年代末为止,非洲一直是冷战的辅助战场。国际上对于曼德拉事业的支持———包括英国的‘释放纳尔逊•曼德拉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是取决于他作为一个既不效忠东方、也不效忠西方的折中人物的形象”,这种评价似乎与其非洲民族主义者的历史定位有所冲撞,但不失为一种解读的视点。
对于曼德拉的判断,在能动与被动之间究竟哪种认知方式更为客观尚有待讨论,但在1999年南非政府开始推行“公平就业法”、“黑人经济振兴法案”后出现的两次白人移民潮却不得不让人深思。2003年前后,“黑人经济振兴法案”实施得如火如荼,大批有技术、高学历的白人或失业、或无法升职而选择移民。另一类白人既无特殊技能又没钱,没有能力离开南非,甚至最终无家可归。 正如《路透中文网》2008年7月17日的报道,“虽然曼德拉在调解种族关系方面扮演了重大角色,但他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弥赛亚。”分析家认为,曼德拉的历史地位源于他出色的领导力和权力协调能力,从而避免了种族隔离末期的内战,团结各种族建立一个新民主国家。但他执迷于人民而忽视政策。
“在我过去的生活中,我已经把自己献给了非洲人民的斗争事业。我反抗了白人专制,我也反抗了黑人专制。我抱有民主和自由社会的理想,希望大家在这样的社会里和睦地生活在一起,享有平等的机会。”
在现代性、后殖民主义、非洲这些宏大的概念面前,曼德拉所持有的不可更易的目标变得弥足珍贵,在现代性给出的可能路径中,曼德拉的尝试因其忍耐、自省而节制的特征逐渐对其之前的暴力诉求形成了颠覆性注脚——这种表述在非此即彼的中国语境中难以被真正理解。
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人虽然愿意相信一个将自己四分之一人生幽闭于牢笼中的黑人领袖,但却对中国社会转型中的各方行为共识而感到担忧。一个个勾践式的中国政治失意者极力发掘自身的悲剧意识并大而化之,对仇恨的压抑下是对卧薪尝胆式翻盘的期盼,导致其阶层的言论和行动往往缺乏必要包容。在种族之外,有关意识形态的交锋仍然未能戒除泛文学化的弊病,太多需要被理性思考的问题变成了左右互博中消费愤怒的素材。
最典型的例证是,当部分中国“公知”欢呼昂山素季恢复自由的同时,他们的反对者纷纷激烈指出昂山素季的父亲是与日本合作的“缅奸”……这种现象无疑是今日中国许多社会讨论不能完成的根本——参与者们往往极易冲动并且没有一个公认的知识话语平台,更缺乏一如曼德拉式的建构者。
不仅如此,某些基于不同立场的评价甚至逐渐模糊了边界,6月20日某国内网站题为《曼德拉27年铁窗生涯:曾研究毛泽东武装斗争思想》的回顾文章将一小段内容作为他们对曼德拉政治生涯的全部解读——“在《红星照耀中国》中,我看到了毛泽东的决心和他非传统的思想方法使他取得了胜利。”而这种有意无意的以偏概全恰恰遮蔽了曼德拉思想以及行动的可贵。
事实上,中国与南非、缅甸的社会变革根本不足以在样式及进程的层面上互为镜像。曼德拉和昂山素季在他们不自由的国度里所居住的“牢笼”已被幻化为浴火重生的浪漫场所,并演变为成就所谓伟大却又缺失核心意义的符号,其间对于今日中国人最具意义的镜鉴反倒是对“暴力革命”思维的根本否定,否则,无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最终结果是“虽败犹荣的安慰”,还是“平民奇迹的惊喜”,都不能平复中国在历史三峡中所遇的坎坷。而这,恰恰是曼德拉一生为这个星球的所有公民提出并付诸尝试的伟大命题。
“假如有寻求和平对策的意志和承诺,那么南非会一直是处于冲突中的国家可以效仿的例子。”曼德拉如是说。转载请注明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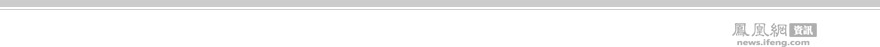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凤凰网保持中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