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倍魄 媒体评论员/凤凰评论特约评论员
核心提示:3月29日,方舟子接受媒体微访谈聊性自由话题,热辣言语频出引起社会关注。访谈中,方舟子认为中国的性自由仍比西方保守,但在包二奶和嫖娼方面比西方“开放”,这源于在性保守的情况下金钱的刺激,“如果有性自由,包二奶和嫖娼反而会减少。”方舟子定义性自由“是两个成年人自愿做的不危害别人的一种自由”。他认为, 人有性自由的权利,但是它的边界是“成年人、自愿、不危及第三方”。否则危害到了别人,就称为泛滥;而如果只给自己性自由而不给予伴侣,则是不道德。 而方舟子更早之前发表的《男人爱貌,女人爱财》一文也成了近来的争议文章,有人以该文证明现今人类社会的男女性别秩序有着天然的进化生物学的“科学依据”。该如何看待方舟子关于性的观点?
广外大学副教授何光顺在微博上发表言论,认为女生应当不必上第一节课,而把时间专门用于化妆,从而让“男生因为美的感动和鼓励,就会赢得奋斗的动力了”。何老师的言论引来了女权主义者的批评,认为他利用教师在课堂上的话语权散布性别歧视的观点十分错误。我是支持女权主义的观点的,并且注意到了一位持不同观点的网友,在争论中引用了方舟子2007年写给《第一财经日报》的文章《男人爱貌,女人爱财》,以此证明现今人类社会的男女性别秩序有着天然的进化生物学的“科学依据”。
方舟子的这篇《男人爱貌,女人爱财》提到了进化生物学的“‘相似-吸引’假说”和“‘潜能-吸引’假说”并直接结论说人类男女的择偶心理符合这两个进化生物学假说。这样,在人类心理活动与进化生物学假说之间的因果链条和科学证明的依据就完全在文章中被避而不谈了。方舟子在文章的结尾称,“我们人类其实也和大多数哺乳动物一样遵循着这条择偶原则,即使我们没有意识到、乃至有意否认这一点,但是已写入基因的本能仍然在悄悄地影响着我们的选择。”
科学主义的傲慢态度在中文互联网上表现为“理工男”动不动就给社会议题的讨论者送上“文傻”的标签,似乎一旦将对方摁倒在“文傻”的座椅上,自己就自动站上了科学的圣坛,掌握了“科学霸权”。
方舟子的论断并不严谨
《进化生物学》的内容里有没有方舟子所说的“‘相似-吸引’假说”和“‘潜能-吸引’假说”,方舟子并没有给出其出处,而且它们是否适用于人类择偶心理也可暂且存疑。但直接研究人类择偶心理的显然是心理学的内容。在林林总总的心理学理论当中,有一门新学科叫“进化心理学”,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初创至今不到30年的历史,是进化论生物学和认知心理学结合体。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心理学系教授戴维•M•巴斯是进化心理学的领军人物,他所著的《进化心理学》第四章“女性的长期择偶策略”里的相关论述,我们应当可以认定它们比方舟子的科普短文《男人爱貌,女人爱财》更严密、更权威。让我们看看巴斯教授的论据和结论。
巴斯教授在论述女性的择偶策略时完全没有提到进化生物学的“‘相似-吸引’假说”和“‘潜能-吸引’假说”,如果这两个假说是存在的和重要的,并且极大程度地影响人类女性的择偶策略,巴斯教授不可能对这两个假说只字不提。通观整个章节,巴斯也没有像方舟子那样肯定女性择偶策略“写入了基因”。在全章最后的小结中,巴斯的结论严谨得多,他说:“现代女性继承了她们成功的祖先择偶时的明智和谨慎。较之于善于择偶的女性,那些不加区分就选择配偶的女性可能会更少成功地生育后代。”请注意,巴斯教授这里使用的是“继承”而不是“基因遗传”,而在所有哺乳动物中,人类是在子女抚育和教育方面投入最多的种群,所以这种“择偶的明智和谨慎”的“继承”就可能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父母的教育和社会文化的影响。也就是说这种“继承”可能是基因的继承,也可能是文化的继承或者是观念的灌输。
巴斯教授并没有那么吹嘘“基因决定论”,像方舟子那样肯定地说那些人类择偶行为是“写入基因的本能”在悄悄地影响着我们的选择。在整个章节中,巴斯也只例举了两个生物学的实例,并且都是鸟类,一个是非洲织巢鸟的雌鸟偏爱能织出更坚固窝巢的雄鸟,另一个是居住在以色列的伯劳鸟的雌鸟会偏爱拥有更多羽毛和布料之类物品的雄鸟。这些当然是雌性动物“爱财”的很好例证,可惜,巴斯论述中这样的例子只有两个,并且,在生物进化的链条上离人类太远。如果有大量哺乳动物和灵长类动物的实例成为证据链条,那么人类择偶原则来自于生物进化的基因遗传的“科学性”会大大增强。在所有生物种群中,只有人类堪称“文化动物”,如果雌性动物择偶原则并非在大量的不同种群中具有普遍的相似性,那么,人类的择偶原则来自于“基因遗传”的假设就很难站住脚。
事实上,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能给出足够多的反例和足够多的复杂性来消弥这些简单化的“基因遗传”假设。著名的人类学家拉尔夫•林顿定义了人类的“社会遗传”概念,即由价值、信念和世界观构成的社会文化不是靠生物学遗传的,而是由生活在社会文化环境中的人一代一代地向上学习并向下传递的。这种文化的世代相传的“社会遗传”过程,也被称为濡化(enculturation)。大量的研究表明,灵长目的幼子如果被剥夺了母亲的关怀,即使存活下来也不能正常地成长和发展。这表明“社会遗传”发挥着“基因遗传”所不能起到的作用,对于灵长目这样的高级生物种群的生存和进化而言,意义同样重大。而在印度西南部的纳亚尔族人,未成年子女在与母亲和舅舅组成的家庭里成长,尽管生父可能享有短期而又持续的对母亲的性特权,但这个男子没有义务在经济方面支持他的性伴侣,她的家也不被视为他的家(William•A•哈维兰《文化人类学》第八章“性与婚姻”)。于是,假如女性“爱财”的心理模块始终存在并发挥作用,纳亚尔族人的家庭模式又是如何形成的呢?纳亚尔族妇女完全无视配偶的经济帮助,这样的情况又如何可能发生呢?
在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中,强调对混淆变量(confounding variable)剔除,否则就无法确定数据结果究竟是来自于研究者期待的变量,还是其他的混淆变量。显然,对进化心理学家来说,人类的“文化遗传”就是混淆变量,而“生物遗传”才是他们希望确定的变量。但在巴斯的《进化心理学》第四章中,极少给出生物学的实例,绝大多数调查数据都来自于人类社会,因此,根本无法剔除“文化遗传”这个混淆变量。所以,进化心理学的理论是推测性、类比性和解释性的,被批评为“不成熟的科学”和“貌似科学的研究取向”。
进化心理学的“革命性”在于它与主流心理学的“文化心理观”针锋相对。它的核心“突破性观念”是心理结构的“模块性假设”。但进化心理学家能为这些心理模块(如达尔文模块)提供的“证据”是非常贫乏薄弱的,并且很难进行重复实验。我们知道,对脑损伤病人的研究可以进行很多重复实验,令我们能够确认脑组织与人类语言功能的对应关系,但进化心理学所假设的“心理模块”却完全找不到与人类的生物组织或基因的对应关系,所以,到目前为止,进化心理学只是一种心理解释框架而不是一门科学。
我们都知道方舟子是坚决反对中医的,中医里的很多概念提供的正是一套关于人体生命运行机理的解释框架,而这些概念很多都无法用西方科学标准下的实验方法进行可重复的验证,这让包括方舟子在内的中医反对者将中医斥为“伪科学”。那么,同样只是一种心理学的解释框架,同样是无法进行重复性的实验验证的“进化心理学”,方舟子却用一篇《男人爱貌,女人爱财》将其内容当成科学定论向公众“科普”,这不能不说是方舟子这位科普作家对来自于东方的古老理论和出身“西方现代”的理论采用了双重标准。
科学可能成为“高级迷信”
这就涉及到更深一步的问题:什么是科学和科学方法?由谁来代表科学的权威性?又由谁来批判和监督“科学主义”成为僵化的教条?如何防止科学成为“高级迷信”而将人性“物化”?
理查德•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堪称科学主义的代表之作。强调人类自私的天性来自于生物基因,这本身在学术上不成问题,但将科学主义上升为价值观,否定人文学科在人类社会的重要价值,把人类文明缩减为冰冷的自然存在和逻辑存在,是科学主义的严重局限。
科学主义的傲慢态度在中文互联网上表现为“理工男”动不动就给社会议题的讨论者送上“文傻”的标签,似乎一旦将对方摁倒在“文傻”的座椅上,自己就自动站上了科学的圣坛,掌握了“科学霸权”。
提到“科学”与“人文”的争论,就不得不提到1996年发生在美国、影响波及全球的“索卡尔事件”。这场旷日持久的“科学”与“反科学”的大论战能为中国社会的理性秩序提供思想参照。
《社会文本》是美国著名的左派文化批评先锋刊物,代表后结构主义、文化多元论和女权主义等对科学所持的批评态度。纽约大学理论物理学家艾伦•索卡尔(Anlan Sokal)1996年5月在《社会文本》杂志发表了文章《超越边界:迈向量子引力的变革性诠释学》,而这是一篇诈文。文章发表之后,不明就里的人文学者乐道:你看,连科学家都来质疑科学主义了;而科学家们一眼看出这篇诈文连基本的科学常识都不懂。几天之后,索卡尔又在另一本杂志上发表了文章《曝光:一个物理学家的文化研究实验》,表示前一篇文章不过是模仿嘲弄后现代科学批评的游戏之作,是堆砌了既无逻辑前提又无经验根据或概念论证的一派胡言。
索卡尔的恶作剧给了人文学者以难堪,是对西方长期以来在“进步圈子”的政治辩论中弥漫的尖刻文风和话语霸权的反拨。但人文学者并没有坐以待毙。他们继续反对“科学主义”的迷信,批判工具主义、技术至上和无节制的经济扩张。
有趣的是,方舟子的《男人爱貌,女人爱财》这篇短文恰恰在网上关于女权主义的辩论中被人引用,来证明男权社会的性别秩序是有“科学依据”的。而事实上,在美国的心理学研究中也有过关于研究结果与种族歧视关系的争议。1994年出版的《钟形曲线:智商与美国人生活的阶层结构》一书指出,黑人的平均智商低于白人,而智商又是决定人生发展的重要因素。这本书掀起的巨大争议使得美国心理学会不得不介入重新调查,得出的结论是:种族间的智商差异确实存在,但这可能是文化和种族隔离制度造成的结果,而没有证据表明智商与基因之间存在任何联系。——这一事件表明,在反种族歧视和反性别歧视成为社会常识的美国,一方面尊重科学数据的权威性,但同时坚持数据解释的逻辑严谨,另一方面,科学家的研究结论也不得不承受“科学批评”的社会风险,“政治正确”是普通人的常识,更是科学家的常识。
可以说,方舟子的科学主义倾向让他对“女人爱财”的客观现象做出了非文化的“基因解释”,这既不逻辑严谨,也不政治正确,必然招致女权主义的批评--虽然在中国,女权主义远不如科学主义势力强壮。
在学术左派对科学主义的批评中,女权主义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视角。后现代主义批评家认定,处于商业社会中的科学研究不可避免会被政治和商业利益污染,他们对克隆技术和基因技术等现代科技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保持着戒备之心。
在中国最能代表“科学”与“人文”冲突的,就是关于“转基因”和“中医”的争论。“科学主义者”都信赖转基因食品的安全,而信奉“中医”和传统文化的人则对“转基因”心怀疑虑,甚至有人相信“转基因”是一种商业乃至政治阴谋。
面对这些争论和困惑,我们何去何从?良序、合作的社会需要有一个让公众信赖的知识分子阶层,当遇到社会关切时,能为公众提供专业而权威的见解,成为社会理性与价值观的守望者。
但“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争论将长期持续下去,因为人类既是理性的存在也是情感的存在,失去任何一种存在方式都将使人成为单向度的人。而在目前的中国社会,“科学”与“人文”之争其实还不是主要问题,更大的问题是反智主义和犬儒主义的泛滥。因为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都是建立在理性主义之上的,而反智主义和犬儒主义完全否定了社会理性的宝贵价值。
因此可以说,目前的中国社会更需要的是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在相互批评、相互校正中齐头并进。
凤凰网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来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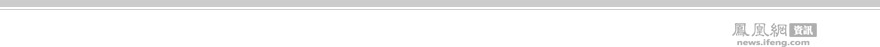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凤凰网保持中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