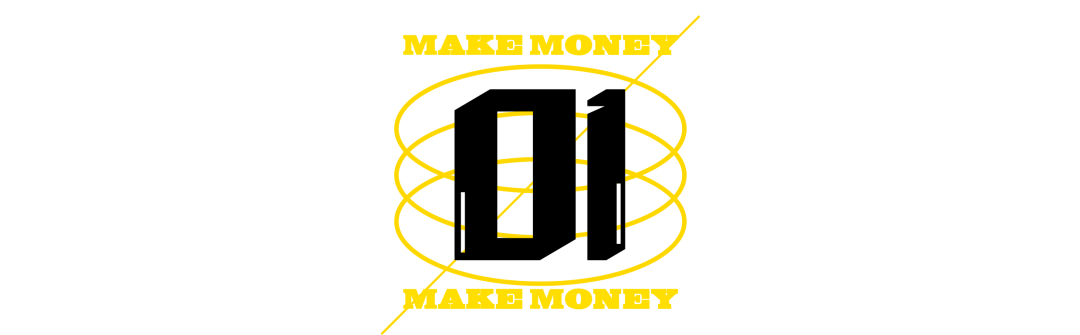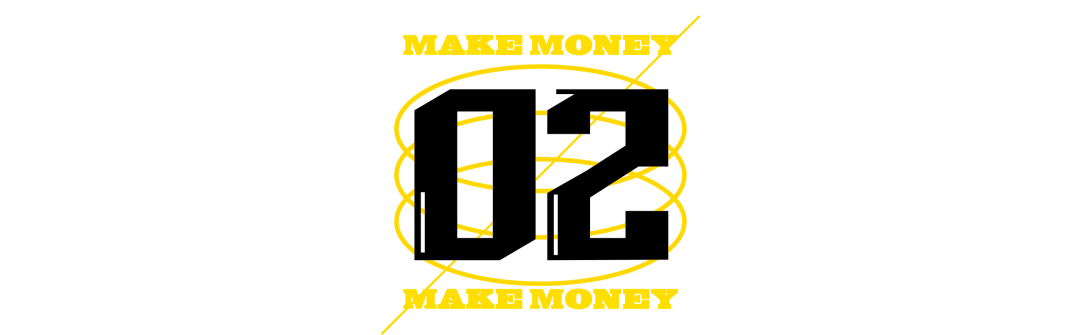我为中老年劳动女性哭泣


独家抢先看
在看这篇文章之前我们先萃取一些共识:
上班是为了赚钱;
上班的底线是劳有所得;
保障劳动者权益是合法合理的诉求;
最起码,把人当人,把女人当人。
被圈养的女人们
女人是不值钱的;
失去性价值的女人更是。
当我刷到"采茶女"的相关信息时,大多只剩截图了,原帖像过去很多事情那样,悄无声息,销声匿迹。
可这些模糊的拥挤的乱糟的截图,成了突破我固有常识的一把砍刀,劈开了一个切片——采茶女工的世界。
一间铁皮屋子,挤着几十个中年女人;
木板搭建成简易的上下铺,被褥、生活用品、人,混合在一起;
渴望被晒干的衣物,悬挂在铁皮墙前方,不知下次穿在身上会不会依旧潮湿。
长长的桌子上堆积着每个人的水杯或碗筷,没有其他一点犒劳自己的东西。
有床板睡已经算是"豪华房",和水泥地只隔着一层红色防水薄布;
她们就这样躺了上去。
一大锅清水挂面,成为她们的主要体力来源;
鲜少有几片青菜叶子,便已算是雇主的恩赐;
需要长时间从事大量体力劳动的女人们,吃的是不如唐志军的生命体征维持餐。
"如果去晚了可能面条也没有了"的朴素恐慌,让她们被形容成像"猪"一样抢食。
面对面排排坐吃白面条,足以让她们在和姐妹谈笑风生时忘却自己的待遇。
在茶山的半山腰啃着干馍馍,也已经不算稀奇。
有前语文课代表看到这些画面,想起了学过的课文《包身工》;
同样鸽笼般的住宿、高强度的工作、像猪一样的吃食。"旧社会才吃人呢"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幽默。
有电视剧爱好者想起了《还珠格格》的翰轩棋社;
可惜籍籍无名的采茶女工们书写不了被救的爽文。
有人说想起了自己的妈妈、奶奶、姥姥;
还有人的妈妈就在采茶女的队伍中。
甚至有自家亲属因这份短暂的零工意外丧命。
100多个阿姨,住几十人上下铺;
《北京折叠》的设定在采茶女身上变成了一种物理折叠。
即使十几天没有洗澡的地方,采茶女工们大多选择的是将就一下、忍耐一下。
是的,歌颂朴实劳动人民优秀品质时,我们总是喜欢用吃苦耐劳、乐观精神等词形容。
她们也的确乐观。
在下工后姐姐妹妹们聚在一起,铁皮房亮起了几处手机手电筒。
阿姨们打开手机摄像头记录美好生活,留出一处空地当作舞台,你方唱罢我登场;
唱山歌,唱戏,一种真实粗粝的《钢的琴》,用久违的原始温馨,消解着劳累的工作和逼仄的生存环境。
看到这个视频时,我承认自己感动于阿姨们的乐观坚韧。
甚至开始警惕自己是否有些"高高在上的怜悯"。
但我们又是否要因为这份乐观,而对她们经历的苦难、不公闭口不谈?
在我们纠结或远处或近处的哭声时,她们却因为自己总是能"忍一下"的"品质",而被几句假大空的歌颂掩埋。
图源:《阜阳600里》
"忍一下"不该是品质,而是"知不可忽骤得,托遗响于歌声"的无奈,是日子还得继续过的妥协,她们没时间内耗,没精力计较。
年纪轻轻结婚,忍着生孩子,忍着一边干活一边带孩子,忍着给孩子攒钱,忍着孙子出生带孙子,忍到老,忍到死。
不能因为她们习惯了忍,就总要她们忍,一个健康社会应有的尺度不该如此。
人海无名的中老年
劳动妇女
采茶女工所映照的是从农村乡镇而来的中老年劳动妇女群体。
主流叙事总是属于年轻人的,即使有一个角落,也属于那些像年轻人一样的"老年人"。
在新世界的前进中,这些劳动妇女成了失语的泡影。
那泡影究竟散落何处了呢?
她们是歌词里总在熬粥的妻子。
是夜间的绿皮硬座车上席地而睡,前往乌鲁木齐采棉的女工。
是凌晨四点守候在街头,寻找日结工作的身影。
是在厕所隔间里吃饭、睡觉的保洁阿姨。
是一句很快被遗忘的新闻。
是几个轻飘飘的数字。
我在城市生活里也时常接触这些中老年劳动妇女;
3小时150块的上门保洁,工具自备,平台分成要抽走大头;
洗浴中心的搓澡阿姨,操持着安徽、河南、东北等地的口音;
她们身上总是融合着两种情绪。既有出来闯荡的洒脱,又有对劳动的小心翼翼。
我感恩于这些我能接触到的阿姨,在很多时刻她们给了我最为真诚朴素的温馨。
本山子曾经说过:劳动者是最美滴。
可这些实打实用双手托举生活的中老年劳动妇女,却因丧失了可利用的性价值,被当作猪啰、当作不止不休的机器、当作不需要体面和尊严的人。
前段时间,互联网上涌动着#为保洁阿姨建休息室的呼吁。
在商场、学校、光鲜亮丽的高楼大厦里,她们却只能蜷缩在厕所或楼梯间。
保安和保洁,一字之差,环境待遇却差之千里。
导演戚小光曾拍摄过一部名为《女子宿舍》的纪录片,吉林一间只接待女性的女子宿舍,每晚收费2元,十平米不到的杂物间,挤着20多个女人。
发霉的床褥、肉眼可见的蟑螂、用砖头垫起即将散架的床铺。
住在这里的女人大多无家可归,只能从事打零工的苦力活。
有人因为是女孩,13岁就被卖给了村里的光棍,可常年的认命与隐忍换不来安稳的生活。在经历丈夫的家暴出轨后,还要为两个吸血鬼儿子奔波。
有人在马路边连站两个月找活,却没寻到一个雇主,尽管她特意画了眉、擦了捡来的雪花膏,还是被人嫌弃“她太老了”。
在这里,“生病”也成了秘密,不只是因为看不起病,而是消息传出去,她害怕再也找不到工作了。
这群女人总是在等待被挑选,没办法,“不管咋的,咱得活下去”。
这部记录中老年劳动妇女的纪录片,还没上映就已经消失了;
不被看见的纪录片,和这群不被看见的女人捆绑成相同的命运。
采茶女、采棉工、保洁阿姨、女子宿舍的零工女人……
她们的生活不是被臆想出的苦难,不需要被高歌的乐观,不需要怜悯和同情;
她们需要的是还给她们应有的保障和待遇,是被当成人的体面和尊严,是最基本的人权。
腰乐队在《我们究竟应该面对谁去歌唱》的简介里写到:“我们为农民和工人写歌,但农民和工人不听我们的歌,只有先锋才听,一些大学生、小青年、知识分子、狂热的音乐爱好者才听。
这让我时常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究竟应该面对谁去歌唱?” 。
是的,看到今天这篇文章的人又是谁呢?
那些习惯了不被看见的劳动妇女们,也许看不到。她们总是缄默不语,默认着在最底线的生存里没有话语权。
有活干,有钱赚,在她们朴素的认知里,就已经足够。
看到采茶女,看到这篇文章的是我们,即使我们也有自己的困境,我们也存在于被卡住的人生。
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悲观的现实即:
人是最不值钱的。
996的办公室牛马们自嘲为极品廉价劳动力;
吃清水面条干噎馒头的是打零工的采茶女;
一份月薪几千的工作可以让许多985大学生挤破脑袋;
时代最自卑时,一代人几十年的工龄和生存经验可以被几万块买断。
但相比之下,我们懂得发声。
在前段时间的网友呼吁下,很多场所已经给保洁阿姨建立了休息室/工位。
这次,中老年劳动妇女的权益,不要被短暂地被略过了,不要成为未解决的议题,不要像一滴水消失在水中。
我们想要的,不过是劳有所得,是有尊严、体面、人权,是每一份耕耘都有收获。
是我们可以“奋勇啊,然后休息啊,完成你我她平凡的人生”。
“特别声明:以上作品内容(包括在内的视频、图片或音频)为凤凰网旗下自媒体平台“大风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videos, pictures and audi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the user of Dafeng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mere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pace serv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