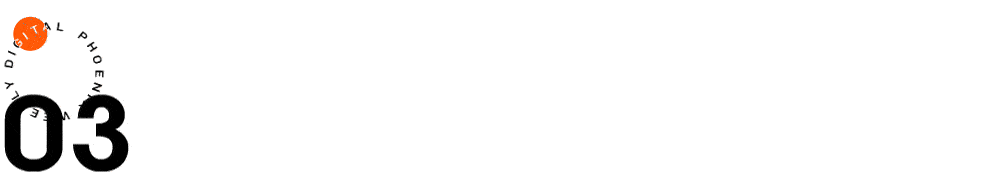80后这代人,吃了多少“时代红利”?


独家抢先看
记者丨卢伊 编辑丨段文
新媒体编辑|闫如意
80后的中年危机,来得格外的迅猛。
青山资本在年度消费报告《35岁,中国式中年》中指出,尽管全球范围内的中年危机往往在四五十岁才逐渐显现。
但在中国,随着产业结构、劳动者教育水平的高速变化,35岁以上的劳动力正在被市场出清。
无数政策优惠、就业求职、婚育观念等,也将35岁作为一道门槛,过之即弃。
“好像35岁有一道无形的门,走进去了便‘隐入尘烟’。”
在这份报告推出的2024年,35岁有了更为具体的指代——他们出生于1989年,是80后中的最后一批。
尽管他们距离通常意义上的“中年”仍有一定距离,但当35岁成为迈入中年的新标准,这意味着:
整个80后群体已集体步入中年,提前直面来自职场、家庭和社会的中年危机。
80后,这是一个拥有2.2亿人口的庞大群体,他们是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也是教育改革的试验品、东西方思想碰撞的产物。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沈杰曾指出,这代人出生在改革开放开启的80年代,成长在全面建设市场经济体制的90年代,成熟在中国加入WTO的21世纪初期。
因此,在80后身上,新的价值观念、人格特征和行动方式开始生长,也因而更能够表征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
他们的一生,都在顺应时代变化,也在变化着这个时代。
〓 1993年7月,广东深圳,家长们带着孩子在麦当劳吃汉堡。
独生子女、义务教育、高校扩招、住房商品化改革……从出生到成年再到中年,80后都处于经济和社会变革发展的变动时期,是社会经济转型下的一代人,也几乎见证了中国40年来几乎所有的重大改革。
因此,他们既是被时代寄予了无限厚望的佼佼者和探索者。
同时也不得不承受着不确定性带给他们的重重压力与困惑。
睁开窥见世界的眼睛
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曾经这样报道80后——“另类的新激进分子”。
2004年2月,北京少女作家春树带着她的《北京娃娃》登上了这期杂志的封面,和她一同成为报道主角的还有作家韩寒、黑客满舟和摇滚乐手李扬。
他们性格叛逆,不走寻常路,常常引发巨大的轰动与争议,因而被视为中国80后的典型代表,被与美国“垮掉的一代”相提并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春玲曾研究过美国1960年代的反叛青年。2008年,当她将研究对象转向生于中国的80后时,她发现二者的成长背景中,都面临着相似的社会经济高速发展。
在首批80后诞生的1980年,中国相继发生了几件大事:
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正式挂牌成立;中国开始发展集体经济,基层开始冲破旧体制,推行包干到户、包产到户;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获批设置经济特区,成为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明确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作为被计划生育政策影响最深的一代人,大多数80后是作为独生子女出生的。
他们的父母普遍都是双职工,经历过历史动荡,文化程度不高,但工作稳定,他们只能用简洁的单字,将对子女成长和国家发展的乐观期望写进新一代的名字里——男孩就盼“伟”“勇”“超”,女孩则要“艳”“敏”“丽”。
那是一个蒸蒸日上、日新月异的年代,也是一个充斥着阵痛和代价的转型期。
公开数据显示,1998年-2000年,国有企业下岗职工达2137万,人们第一次真正认识到,没有铁饭碗,工作是可以被开掉的,劳动力是需要竞争的。
在父辈的中年危机中,80后们提前懂得了现实的残酷,因而具有格外强烈的危机感和使命感,这或许为他们日后的中年危机埋下一道伏笔。
当然,有下岗潮也有下海潮,改革开放的洪流,为市场经济和人民生活注入了新的能量和风尚,80后很快体验到了物质和信息如何从不丰富走向过剩。
随着改革开放刮起的春风,港台及欧美的影视剧、动画、音乐逐渐引入内地,并由此催生的录像厅文化、磁带文化等,构成了一代人的记忆,也为80后打开了窥探世界的一扇新窗。
〓 1996年,广东广州,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带领听众大喊:“我一定能讲漂亮的英语!”
当孩子们不再满足于电视播放的《加里森敢死队》《西游记》《大侠霍元甲》,而又无法接触更为神秘的“内部电影”,录像厅里的《射雕英雄传》《上海滩》和《古惑仔》刚好能带来强烈的视听刺激和不同江湖的侠义情仇。
走出厂办院落和学校操场的80后,也有了更多新的玩法。
1985年,中国第一台电子游戏机“汉龙”在广西柳州汉龙电子计算机分厂诞生。五年后,同样诞生于80年代的任天堂红白机正式引进中国,紧接着,能够兼容各种游戏卡带的小霸王学习机也于1993年横空出世。
从恐龙快打、合金弹头、拳皇,到魂斗罗、坦克大战、超级玛丽,这些经典共同构成了一代中国人的童年记忆。
彼时,街头巷尾多的是脚踩喇叭裤、头戴蛤蟆镜的“嬉皮士”,他们围着“三洋牌”收音机,里面传出邓丽君的“靡靡之音”《甜蜜蜜》《何日君再来》。
耳濡目染中成长起来的80后随后将他们变成了更为时髦的王菲、张国荣、小虎队、“四大天王”,以及动作夸张的霹雳舞。
曾被抵制的可口可乐在中国实现本土化生产,位于深圳罗湖的东门商业步行街也开设了内地第一家麦当劳餐厅。
全球化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80后的日常。
教育改革的践行者
九年义务教育在中国开始于1986年7月1日,刚好是初代80后刚刚升入小学的时候。
公开资料显示,我国用14年时间基本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
1990年代中期,完成小学教育后的初中升学率几近100%,而完成初中教育后的高中升学率则从1980年代的30%增至2005年的60%。
自1998年开始,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接受大学教育的比率也从40%攀升到80%。
这些数字的变迁,刚好也覆盖了整个80后群体的教育足迹。
1999年,中国首次宣布将大幅度扩大该年度的高等教育招生规模。这一年,最早一批80后刚好进入高考考场,高校招生人数多达160万人,增幅高达47%。
在这场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扩招规模最大的高校大扩招中,出生于第三次婴儿潮的80后们陆续赶上了扩招的余温,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激烈竞争态势多少得以缓解。
这次高校扩招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使大众教育代替了精英教育,数百万人享受到了高等教育的机会,促进了教育机会的均等。
人力资源开发水平和国民素质的提升,更有助于缓解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下,每年300多万高中毕业生形成的新的就业压力。
但大学生数量的快速增加,也直接或间接地催生了高校人才培养质量下降和大学生就业困难问题,其中后者恰好始于2002年,即首届扩招大学生毕业的年份——是的,又是80后。
到2008年,在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国实体经济也逐渐受累。官方数据显示,当年第三季度以来,中国出口大幅下滑,经济增幅放缓,就业压力加大。这让许多80后大学生担负的就业压力更为沉重。
李春玲的研究发现,80后一代的教育机会不平等程度并未明显下降,且城乡教育差距还在进一步扩大,多数最终突破层层关卡的农村子弟进入的是二、三流大学。即使获得大学文凭,就业问题更难突破。
《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曾这样描述“蚁族”:
平均年龄集中在22-29岁,九成属于80”一代;他们拥有较高学历,有的毕业于名牌高校,更多来自地方院校和民办高校;他们多从事保险推销、广告营销、电子器材销售等工作,平均收入低于2000元,有的完全处于失业状态;他们人数众多,主要聚集于城乡结合部或近郊农村,生活条件差,缺乏社会保障,挫折感、焦虑感等心理问题严重。
作者廉思曾经为“蚁族”的未来深感担忧,认为“他们揭示了一代人的痛苦、无奈和彷徨”。
经济发展降速时期,一部分80后开始转向保守和稳定。
2008年1-4月,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曾对应届大学生就业倾向进行调查。
相比去国企或政府部门工作,当时的主流选择为外企,占比高达42.4%。但同年11月下旬,金融危机蔓延后,该中心再次发起调查时发现,想去国企和政府部门工作的大学生比例增至41.1%,而外企则仅占18%。
这一现象在十余年后的今天再度重演。
也有部分80后决定推迟就业,继续深造提高竞争力,以博得更好的工作机会,考研热由此兴起。
1980年代初期,中国才正式建立了自己的学位制度,恢复招收新一轮硕士、博士学位研究生,并在22所重点高校试办研究生院。彼时,国内研究生总数仅有1万余人,招生数更是仅有3616人,但同年代出生的80后步入象牙塔后,全国在学和毕业研究生总数已破24.5万,并快速增长。
据教育部统计公报数据,到2011年(注:此为传统意义上最后一批80后首次考研的年份),全国已有研究生培养单位755个,在学和毕业研究生共207.58万人。同年,全国考研人数达151.1万人,而教育部仅计划招收49.5万人,淘汰率已近2/3。
这一热潮直至去年才有所“降温”。
与此同时,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陆续派出赴美访问学者和公费留学生,并于1981年起允许自费出国留学,并于同年首次举办托福考试。俞敏洪的新东方就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创立的。
对80后来说,他们也出生于同样的时代,伴随着中国接入国际互联网、全民英语热、成功入世申奥成功,他们越来越多地在社会发展和现实生活中感受和参与到全球化事务中,也越来越普遍地成为留子和“海归”。
不过,随着留学人群基数增大,海归群体从精英逐步走向大众。
2017年,中国各类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48万余人,创历史新高,2012年这一数字仅为27万人。
从住房、生育到养老,直面民生问题
曾有媒体写道,从“剩女”“直男”“丧偶式育儿”等标签,到要不要二胎、如何教育孩子、如何给父母养老等,这个时代大多数的流行议题几乎都围绕着80后的生活轨迹,无不透露着一代人富足生活背后也会被选择困惑和现实焦虑所包裹。
2017年,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复旦大学社会科学数据研究中心最新发布的“80后的世界——复旦大学长三角社会变迁调查”,以1980-1989年出生的80后为跟踪主体,研究的内容包括这一代人的家庭、婚姻、就业、迁移、住房、生育、子女教育、父母养老等各个方面。
研究显示,尽管上海80后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4.7年,且连续三次调查中的总体收入涨幅均高于同期上海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和上海CPI增幅,但他们仍坦言面临着住房、子女教育和经济三大压力。
中国这代80后出生于中国房地产元年,房子自此被赋予商品的定义,也有了随市场和供需而变化的价格。
一位80后受访者回忆,那时自己还是不懂房子有多重要的年纪,长大后才发觉,错过了60后的国家分房和70后的低房价优惠,等来的已是炒房团四处横扫下的楼市狂欢、房价高企,“如果时间能够倒流,我一定马上回去买房。”
麦田房产曾经专门为“80后”们算了一笔账:假设一对“80后”情侣,月收入共为8000元,如果要在北京望京某社区购买一套60平米左右的一居室二手房,总价约在165万,首付则需要40万左右,如果按照贷款30年来计算,月供将达到4500元。
首付40万,对于那时的绝大多数“80后”而言不啻于天文数字,即便有家人的资助,对于许多家庭来说也基本要花掉两代人的所有积蓄。而在那个民法典尚未大修、婚前协议还不是那么广受认可的年代,由谁出资、结婚时房本写谁的名字,分分钟会引发口水大战。
尽管这一情形对于当下年轻人而言并不陌生,但“80后”作为第一批直面房贷压力的群体,其挑战可想而知。“蜗居”“房奴”“啃老”等曾经的热词就是一个写照。
按照社会时钟的发展,安家落户的下一步就是婚恋和生育。
2010年,有媒体发起的调查显示,结婚生子的确也是80后打工人最常提到的愿望之一,只是,他们的婚育观更加多元复杂,裸婚、剩男剩女等都发端于这代人。
生育环境、成本和政策的变化,也直接影响着生育意愿。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80后和00后的人口分别是2.19亿和1.47亿,出生人口萎缩了33%。
而前述复旦研究显示,随着中国的生育政策逐步放松,上海80后的理想子女数由2012年的1.58上升至2016年的1.7,但二胎生育意愿依然薄弱,仅有13.1%的被访者愿意生二孩,不愿意生二胎的前三个理由是养孩子太贵、房子不够大和时间不够。
与此同时,有资料显示,80后是中国社会养老压力最大的群体。
随着老龄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作为一代独生子女的80后开始成为家庭的夹心层,一对夫妻,上有四老,下有两三小,无论是父母的养老医疗花费,还是子女的教育成长投资,承担家庭责任的经济和精力压力早已无需多言。
“最坏的时代,最好的时代”
家庭的重担仅构成了80后中年危机的一个部分,更大的危机来自职场。
作为国内较早开展80后群像量化研究的学者,李春玲2013年就曾在研究中指出,80后步入社会时,金融、互联网科技等行业发展迅速,这些新兴行业的中年人很少,给80后精英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可以说这一代人非常幸运,他们得以很快地向上流动。”
如今10年过去,金融、互联网行业依然红火,一些80后精英已然跃升行业中坚。
据不完全统计,2021年以来,国内至少14位80后担任高校校领导;2023年“两院”院士候选人名单中,有8人出生于1980年代,系院士增选首次出现“80后”的身影;2024年4月25日发射的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上,三名飞行乘组成员叶光富、李聪、李广苏都是80后;商业领域,越来越多的80后创业者跻身消费市场,比如滴滴程维、美团王兴,还有被称为“接管了全球钱包”的电商出海四杰——TikTok张一鸣、Temu黄峥、SHEIN许仰天、阿里蒋凡等。
但更多80后是陷入瓶颈的。
全国总工会2022年一项全国性调查显示,35-39岁年龄组职工中有54.1%担心失业,70.7%担心技能过时,94.8%感觉有压力,均是各年龄组中比例最高的。
照年龄推算,这些受访职工多在1983-1987年出生,他们是80后一代的中坚力量,可以说正值“当打之年”,甚至都不能算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年”,但他们依然为年龄焦虑,这被视为一场“中国式的中年危机”。
35岁年龄门槛的出现,更将整个80后代际集体推入这场危机。
受体力、精力、外貌等因素影响,军人、主播、运动员等职业对年龄门槛更为敏感。
〓 2024年4月25日,甘肃酒泉,三名80后航天员出现在神州十八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上
以2024年国庆期间在北京首钢园举办的 WTT中国大满贯赛为例,杀入男单决赛的马龙生于1988年,即将迎来36岁生日,这已经踩在了运动员职业生涯的末端,而最终将他击败的决赛对手林诗栋却是05后,两人有着近18岁的年龄差。
而35岁作为明确的职业年龄上限,最早可追溯至1994年和2007年出台的公务员录用有关规定。彼时,相比进外企、大厂或自主创业,考公考编并不是80后时兴的出路,因而这一年龄限制并不凸显。
但或因公务员招聘标准具有较大社会示范效应,同在体制序列的事业单位考编、高校教师招聘等陆续出现了35岁上限的要求,接着,诸多央企国企乃至部分民营企业也逐渐将35岁以下作为录用标准。
到2017年,网传“华为清退34岁以上老员工”的消息激起强烈震荡,尽管此后华为高管回应称传言并不准确,但自此,35岁年龄门槛开始频繁出现在以互联网科技为代表的多个行业,并成为了约定俗成的一道“红线”。
四川大学曾发布一份长达十年时间、调查了30万个招聘广告的研究,结果显示上海八成以上、成都七成以上的社会职位都要求应聘者年龄在35岁以下。
互联网大厂是“35岁年龄门槛”的重灾区。据《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35岁以下从业人员占64.6%,其中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占比70.4%。
这一情况在同年脉脉数据研究院发布的《互联网人才流动报告2020》中,有了更为具化的表征:19家互联网头部企业人才的平均年龄为29.6岁,其中,阿里巴巴和华为员工的平均年龄为31岁,而字节跳动和拼多多员工只有27岁。
年龄无法优化,人却可以。当年轻越来越多地成为招聘标尺,甚至让位于学历、业绩、经验、能力时,多少未能实现向上流动的80后在此折戟沉沙,却美其名曰“优化”和“毕业”。
〓 2016年4月,员工在北京一区块链公司内午休。调查显示,互联网、金融行业是“35岁门槛”重灾区。
这甚至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有数据显示,在硅谷工作的员工平均年龄为29岁-35岁之间,远低于美国职场人平均年龄42岁。为了避免踩中“35岁就业门槛”,一些硅谷码农不惜花重金做美容、注射肉毒杆菌,以期在外貌上“显得比实际年龄年轻”。
一些被优化的80后就业时发现,当他们“退而求其次”,寻求一些“没有太多技术含量”的工作时,年龄门槛依然存在。比如,二三线城市的景区售票员也得“大专以上、35岁以下”,一些连锁服装品牌的门店销售则要求年龄不超过28,甚至25周岁。甚至有人想要入住青旅,也会因为超过35岁被拒绝入住,理由是:“年龄大的上下床不安全,容易出事”。
“80后实际上是一个市场竞争压力非常大的群体,我们在访谈中感觉他们就是在市场压力下不停往前冲。”李春玲的访谈始于10年前,那时绝大多数80后即将奔三。如今,当他们集体提前步入中年,依然在压力下寻找机会,负重前行。
有关这场“中年危机”的讨论仍在持续,就在今年全国两会上,也有不少代表委员提出,政府应对35岁年龄限制情况的改变作出表率,逐步放开公务员录用的“35岁门槛”,从北上广等大城市开始。
现实中,多地也已将部分公务员岗位的年龄限制扩宽至40周岁以下。这些变化,或许能为受限于年龄门槛的80后们松松绑。
采访中,一位80后姑娘告诉我,她曾经很喜欢电影《小时代》里的一句台词,“我们依然在大大的绝望里小小地努力着。这种不想放弃的心情,它们变成无边黑暗的小小星辰。我们都是小小的星辰。”
在这部主创团队多为“80后”的商业烂作中,这样一句现在看来颇有“鸡汤味儿”的台词,却仿佛宣告着这一代人所处的时代,和一群在物质生活中奢靡、困惑、挣扎的年轻人。
但现在,早已默认步入中年的她,反而咀嚼起了狄更斯在《双城记》中的第一句话: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
一代人固然有一代人的宿命,但她坚信,“变”只是一种中间态,就像潮水,时起时落。
“机会总会有的。”她说。
“特别声明:以上作品内容(包括在内的视频、图片或音频)为凤凰网旗下自媒体平台“大风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videos, pictures and audi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the user of Dafeng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mere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pace serv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