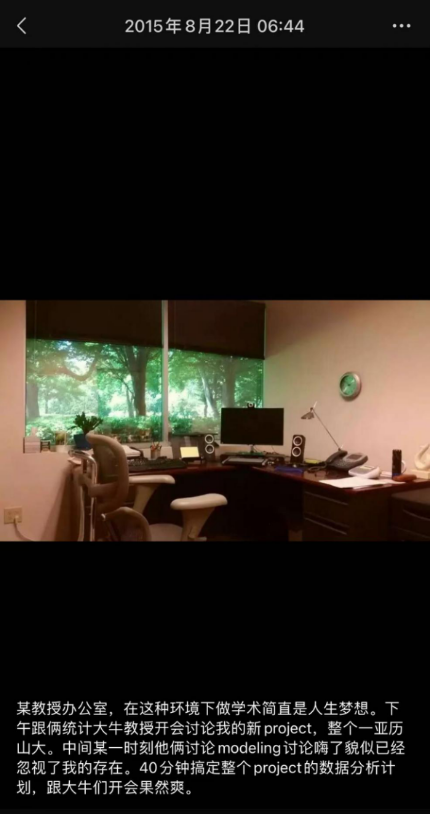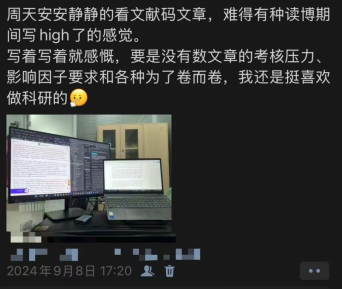海归博士入职985高校,优秀“做题家”也卷不动了
文|《中国科学报》记者 孙滔
“博士后的痛苦太多了!”
当被问及读博和做博士后哪个更艰难时,刘龄毫不犹豫给出了上述答案。她在进入博士后工作站后不到一年就想退站。她看不到工作的意义,甚至自问当初为什么放弃了全职临床咨询工作而坚持要做学术。
那种纠结,远胜于读博时内心的无数次交锋——是继续读下去,还是退学。
她高中毕业就去了美国一所以心理学著称的公立高校,就读心理学专业。从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她在这所大学待了11年。回国后,出于快速了解国内学术圈的考虑,她选择去做博士后,毕竟自己在这个圈子谁都不认识。
新加入的课题组实力很强,与自己的研究方向很契合,大导师也是刘龄很钦佩的教授,所以刚回国的她抱着雄心壮志想脚踏实地做科研。没料到的是,在实验室小导师手下开展工作的时候,她被迫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实验室建设和行政事务上。加之工作上常常被打压,一直独立自主的刘龄感到无所适从。
她没有其他选择,只能苦熬着出站。
挑战总是层出不穷。2023年9月,她入职某985高校担任助理研究员,“非升即走”的学术阶梯又竖在面前。她看到,周围的“青椒们”每天要计算到账了多少钱的项目、发了多少篇文章、影响因子是多少,以及被引量是多少。这些算计一度让她感到生理不适,究竟怎样才能不受外界干扰、回到最初做科研的本心呢?
义无反顾的选择
刘龄清晰地记得,2009年6月21日,她跟爸妈挥别。过了安检后,她一个人拖着两个23公斤的大箱子,踏上了美国的土地,这一去便是11年。
她自小是个又乖又倔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鲜少跟父母发生冲突或叛逆。但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她却义无反顾,“八头牛也拦不住”。
她顶着全家的反对,选择了心理学专业。父母都是医生,他们知道医学道路有多苦,所以不让女儿学医。但一直在四线城市的父母也并不了解心理学是什么,只是隐约觉得就业前景不好。
为什么如此坚持?刘龄说,最初始的动力就是想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从小到大,她极度羡慕那些如鱼得水的“社牛”同学,自己却是独来独往、形单影只。初中时,她常常皱着眉想,“我为什么会是我?怎么样才能不讨厌自己?”
她是“社恐”。她喜欢自己呆着,玩一些积木、拼图或折纸之类的东西,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她喜欢安静,在家放音乐她都会嫌吵。“在尘世的喧嚣中寻找心灵的一片宁静”,是她自从用微信以来没有变过的个性签名。
他们对抗了大约一个月,父母终于妥协了。
尽管高考英语超过130分,但刘龄在大学第一个学期就遭遇打击。《心理学导论》这门课一直听得云里雾里。来自德国的老师口音很重,让她读一页书就得查10分钟的专业词汇,无奈之下只好退了这门课。
她不愿意认输。之后的日子她就把图书馆当成家,一个通宵一个通宵地熬,不懂就反复刷,直到能听懂为止。最终她的平均学分绩点保持了高分,一直到毕业。
到了第二个学期,她发现身边的同学并没有像自己一样一直熬夜苦读,而是在积极参与社区或社团活动。她也试着参与这些活动,发现这些活动其实对于自己的学习和生活都很有帮助。她去了特教中心做志愿者,开始接触自闭症儿童。这也是她后来踏入发展与临床心理学领域的第一个契机。
自小只会刷题的刘龄,并没有做好面对打击的心理准备。她自以为绩点很好,却落选了一个奋力争取的荣誉项目。
还有一次社会学的课拿了一个B+,她也无法接受。出成绩的那天晚上,这个女孩开始跟自己较劲。她研究了一晚上魔方,最后在20秒之内搞定了它。
她向家人诉过苦。但是家人在电话那头只是告诉她,“再坚持坚持”,这样的情绪支持远远不够。
但最终她坚持下来了,并且用3年时间完成了4年的课程,拿到了优秀毕业生的称号。可惜的是,第一次申博的时候,所申请的8所高校全部未果。后来她反思,只是有绩点高是不够的,自己申请经验不足,再加上临床心理学方向博士生申请的竞争太激烈了。
对于所有这些,现在的她可以风轻云淡地说“那都不是事儿”,但是对当年的她来说却好像“天塌了一般”。
于是她去读了一个硕士,两年后再度申博,成功斩获了录取率仅有3%的临床心理学博士生offer。
渡劫
申博成功只是开始,而刘龄不会料到她要渡的“劫”有多少。
第一个“劫”,就是科研成果出不来。
第一次写文章,期待过高却写不出来。这个时期她在科研和教课的同时还要去临床实习。她总觉得导师指导不够,找导师的时候却寻不见人,发给导师的文章拖着迟迟没有反馈,自然也就无法投稿。导师甚至在完全不知会她的情况下,把她的项目给了别人。所有这些让刘龄百思不解,在好几个时刻,她都想要放弃了。
看到陆陆续续有多个博士生和硕士生离开实验室换导师,刘龄也无法坚持下去了。她也不甘心退学,毕竟这个读博机会是自己经过奋力拼搏才争取来的。
2016年夏天,为了换实验室,她与导师和院系开始了长达半年的拉锯。就在这个难熬的时期,国内亲人病逝,而她无法及时赶回。
这个时期她太紧绷了。她几乎每天都在完全不同的思维状态中转换:刚刚还是学新知识的学生,下一刻就要坐在咨询师的椅子上帮来访者梳理思路,接下来可能要跟实验对象互动收集数据。每件事都需要全力调动思维,极其消耗脑力。这一年,她开始进入辩证行为疗法(DBT)的实习阶段,接手的都是有过严重创伤史的来访者。对于一个新手咨询师来说,这些负面情绪后劲太大,每次咨询后她都要缓冲很久才能走出来。
2017年年中,和她朝夕相处3年多的宠物兔在一个早上毫无征兆地离开了。最后的那根稻草落下,她崩溃了。她再次吃上了抗抑郁药,并找了新的心理咨询师。上次吃药还是她本科课业压力大的时候。2017年最后一天的晚上,她站在圣地亚哥的海边,用尽全身力气说服自己要活着。
2018年3月,她休学回国,休养了整整3个月。接下来,她得到了一个上海私立心理咨询及测评相关的工作机会。在近一年的时间内,她和多专业团队合作,深入特教学校工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她在纠结是不是回美国把博士读完。
对于循证实践的追求,对于学术的不甘心,最终让她读完了博士。
更大的“劫”
虽然疲累,但做博士后之前的刘龄还是拥有纯粹的学术世界。她看文献的时候会忘记时间,会沉浸在某一个数据统计方法里不能自拔。换了实验室之后,在新导师这里她又找回了最初的热情。毕业时导师评价说,从来没有见过谁写博士论文可以投入到如此程度。
图源:刘龄的微信朋友圈
周围的很多人是纯粹的。她的一个博士生同学是专业芭蕾舞演员出身,却一心要攻读临床心理学博士。刘龄看到,不像自己周末还泡在实验室,这位同学每天朝九晚五,绝不加班,“是过了5点坚决不回邮件的那种”。但是她的效率极高,不久就发了多篇论文,在毕业之际还形成了关于创伤的一套理论。后来,这位同学去了一所很好的大学担任教职。
刘龄也很佩服自己的第二任导师。这位导师之前玩摇滚,家里收藏了各种黑胶碟片和音响设备,后来又成了擅长数字化治疗的临床心理学家。刘龄说,他的学术能力、临床能力,以及人品“都让我随时随地准备献上膝盖”。他知道尊重学生,能够激发学生的能力,也擅长管理和推进项目。所有这些,刘龄如今都在传承给她的学生。
然而,博士后的日子完全改变了刘龄的认知。
之所以选择回国,一方面是父母年纪越来越大了,她越来越觉得家庭重要;另一方面,回国后得到了更多的社交和文化认同感。
她考虑到,自己高中毕业就出去了,整个心理学的专业体系构建都属于西方的体系,而在国内写文章和申请基金都要从头开始摸索。不仅如此,因为自己是科研加实践背景,与同期纯科研的同仁们相比,毕业时候的论文成果并不“抗打”,因此不如以做博士后作为过渡。
回国之初,刘龄有过“高光时刻”。毕竟科研加实践的背景亦是她的优势。在一个国家级计划启动会上,某教授介绍她是“打着灯笼引进的人才”。
接下来,就遇到了她博士后第一年就想退站的情况。实验室建设或行政工作占用了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电脑文件夹里是各种“月度报告”“季度总结”“建设方案”,自己想要做的一些课题工作却难以开展,自己的工作成果最后也都成了小组领导的功劳。最让她难受的是,博士后出站的时候,她被质疑“你这两年到底都做了些什么”,而她没办法拿这些“琐事”当成自己的成绩。
她特别需要有自我发挥的空间。她盼望着自己带组,去推进自己想做的课题。她想知道儿童情绪调节的能力是如何发展出来的,以及最初家庭环境互动对孩子早期情绪调节的影响。还好,博士后期间有几次让她印象深刻、脑力激荡的课题讨论,使她觉得自己还在做科研工作,还能继续坚持下去。
她认清了现实。开始重新思考国内的体系适不适合自己,以及在这种环境中自己能否存活下来。
虽然不顺心,但博士后期间,她深入接触了国内学术圈,也积累了一些成果。只是有些论文是为了发表而发表,这让她怀疑那些工作对自己真正想研究的方向是否有推进作用。
她怀念一心一意做研究的日子。那些研究成果对于儿童的成长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那种帮助是有实质性意义的。
怎么办?
不甘心,再一次拯救了她的学术生涯。读了这么多年书,怎么能因为外界环境的压力而放弃呢?
不甘心
与《中国科学报》记者近3个小时的对话中,“不甘心”成了刘龄口中多次出现的字眼。
她给自己设了一条底线——再试几年,如果聘期后副高评不上去,她会说服自己,不是能力的问题,而是自己无法适应这种评价体系。她说:“我以前挺卷的,回国这几年反而有点卷不动。”
刚入职时,她就被问到发表文章的影响因子。后来,她还发现大多数情况下只认文章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作者挂多个单位也只认第一单位。当她跟美国导师说起这种情况,“他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她看到,在学术圈“存活”下来的学者们,有让她真心实意敬佩的,也有让她“刷新认知”的。
很长一段时间,辞职的念头总会冒出来。“要不然就再试一次,好像还没有做到100%努力”,这种信念让刘龄坚持了下来。
直到最近几个月,她才想明白一些事情。她慢慢找到了自己的节奏:既然不能改变这个系统,又不愿意违背本心改变自己,那就不如跟着自己的本性去做,该发生的自然会发生。即使将来不能晋升,至少也不会后悔这些年的努力。
她想要回归做学术的初心,去解决现实中的心理学问题,而不是本末倒置地把评职称作为追求目标。虽然回国以来确实有很多不如意,但是也让她结识了一些志同道合、一样愿意坚守本心的年轻学者。每个人都会诉说各自的“劫”和焦虑。但是他们都相信,不过分追求职称,认真做自己的工作,终究是会有收获的。
有了这个底线之后,她跟现实就和解了,也化解了很多压力。她知道自己过往的发展心理学研究过于“传统”,缺少认知神经的基础和对“热点”的追逐,让她在申请项目上吃力了些。没关系,她需要去找一种平衡。
同时,她也不再因为某个“95后”评上优青的新闻而焦虑,增加无谓的烦恼。
她一直热心临床实践工作,目前依然有每周半天的咨询工作。看到自己帮助到一个个家庭,那种即时的成就感能够抵抗学术高压。
在静下心的时候,她也会感慨自己还是能回到当年看文献看嗨的日子。最近她读到《中国科学报》的报道《7年两次考核未过,高校副教授亲历“非升即走”》,主人公马梅正是她的同行。她感同身受:“不发表即毁灭的圈子,让科研工作者不得不思考当初为什么要做科研。”
图源:刘龄的微信朋友圈
她最近的状态好多了。10月12日,她发了一条朋友圈:
“节后复工第一天列了个16条的to-do,然后就一条一条去做。虽然一周过去了,划掉了5个又加了4个,但是这种有计划感和掌控感的忙碌确实是很久都没有过的,甚至让我在午后走回办公室的路上有一种强烈的平和感。我愿称之为‘为自己打工的满足感’。
近几个月一直在给自己磨合工作—身心平衡,无论是通过撸铁重新建立自己与身体的链接,还是把关注点聚焦在自身情绪状态上(取悦自己最重要),都能够帮我排除外界的各种干扰和不确定性。”
(文中刘龄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