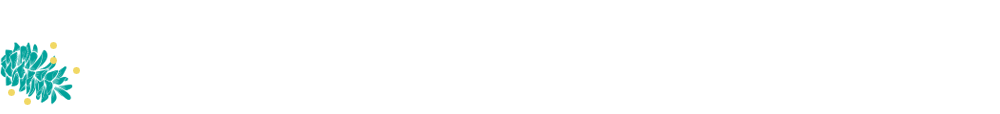“00后”代孕女孩,和她经历的一次流产
文图丨李禾
编辑丨雪梨王
下腹部的剧痛是在11月6日天刚擦亮时袭来的。张婧从睡梦中惊醒,她感觉有人在死命拉扯、搅动自己的肠子,像是要把这具身体的某一部分撕裂。她使劲抱着枕头,用牙齿咬住被子一角,试图用这种方式,让痛感尽快消失。
疼痛不断加剧。张婧意识到,是肚子里刚满5个月大的胎儿出了状况。
那是她接到的第一笔订单。作为代孕母亲,张婧很清楚,成功生下这个孩子,意味着她可以拿到24万元——中介开出的价格,是她平日靠打工难以企及的数字。作为辅助生殖行业中的最受争议的部分,自1988年中国大陆第一例试管婴儿成功降生以来,代孕这个交织着繁衍、欲望和财富的地下市场日渐庞大。而它的底层逻辑,就是用金钱交易一个孩子。
一定得保住孩子,张婧强忍着疼痛,想要喊醒其他人。但在这个三室两厅的“宿舍”里,代妈们都住着单间,她低声喊了几声,没人听到。又挺了近两个小时后,早上八点多,她终于摸到床头柜上的手机,拨通了中介机构的电话。在暗自运转的代孕市场中,中介通常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微信名为“懒懒猪”的中介赶来了,她平时负责对接张婧。
张婧煞白的脸色吓坏了她。原本她只想把张婧送进一直合作的小私立医院,考虑片刻后,决定把她送到一家公立医院。去医院途中,张婧腹部有种强烈的下坠感。没一会儿,羊水破了,大量液体流到汽车后座上。
孩子保不住了,医生说。他们做了相关检查后,次日给张婧做了引产手术,从她的腹中取出死胎及胎盘。对这个死胎,张婧没有任何感情,甚至根本没有看一眼。即便流产前,她已经能感受到那个生命的活动——Ta时不时会踢一脚她的肚子。
如果把代孕比喻成一次赌博,张婧知道,自己赌输了。孩子没了,意味着她只拿到了之前的3万元。
“我还会有什么赔偿吗?”她问中介老板刘雷,“我还会有第五个月的工资吗?”
答案都是否定的。“我们也亏死了。”对方说,并配上了一个哭的表情。
植入
从被塞上那辆七座黑色商务车开始,张婧就不知道自己将要被带向何方。
车上只有她、司机和一个叫殷丽的中介。坐稳后,殷丽让张婧交出手机。张婧知道,对方怕她录音或录像,于是顺从地交了。她想要看看窗外,但车窗玻璃是黑色的,挡风玻璃则被司机和坐在副驾的殷丽死死遮住,丝毫看不到。
有段时间,她感觉到车子上下颠簸,由此判断“可能走了段山路”。就这样大约行驶了一个多小时,车子停进了车库。张婧走下车,一个持黑色安检仪的人将她从头到脚扫描了几遍,确定没有发出“嘀嘀”声,她终于被带入房间。
张婧知道,这里就是地下代孕实验室了。
中介告诉张婧,作为代孕妈妈,她需要在实验室移植胚胎;移植成功后,再连续注射一个多月的黄体酮,后期还得吃一些口服药,接下来就是正常产检,等待生产。
代孕中介对代孕的介绍
张婧环顾了下四周,大概判断出这是栋别墅。一楼的几个房间内,放着各种医疗仪器,穿白大褂、戴口罩的“医生”来回穿梭,“医生有男有女,年龄都挺大”。
很快,她被要求换上一套浅色“住院服”,躺在“货架”上。从她的描述看,所谓“货架”,其实是一张妇科检查床。医生让她张开两腿,抬起来搭在床边类似扶手的地方。张婧原本以为该打麻药了,但“医生”说胚胎植入不疼,不用打。
又有几个穿白大褂的人走进来,在她两腿之间操作。
中介说,他们的业务,不在医院开展
采访过程中,一位三甲医院生殖中心医生向我解释,“胚胎植入简单来说,就是用导管通过子宫颈,把胚胎放入宫腔内。”医生通常会先用胚胎移植管,在B超引导下,把导管放到子宫里,注入胚胎。
“胚胎移植管长度一般在18厘米左右,直径0.23厘米。”这位医生透露。
张婧对这些一无所知,她只记得,整个过程大约5分钟就结束了。
移植完成,意味着张婧体内有了一个与她无关的胚胎。她记得殷丽提过一嘴,说“客户是一对男同性恋”。张婧不信,“怎么可能呢?后期办出生证的时候,母亲一栏,总不能写个男的吧?”但中介说这不是她该考虑的,只管养胎就好。
接着,张婧被抬到另一张床上平躺了几个小时,再返回车库,被那辆黑色商务车拉回宿舍。在宿舍待了不到一天后,又被运到了200多公里外的南方小城。
张婧住过的其中一个代孕宿舍
在那里,她和其他代妈一起,住进了那个三室两厅的宿舍。等待在8个月后,制造出一个健康的婴儿。之所以是8个月,张婧解释,是因为胚胎植入前,已经在外面养了一个月。
成为“卵妹”
我是在9月底得知张婧代孕的。当时她怀孕三个多月。仅凭外表,很难把她和产妇联系在一起——她清瘦,稚嫩,高中生的模样。这是代孕中介眼中最抢手的那款,年轻、没生过孩子、没有伴侣。根据身份证上的信息,张靖今年22岁,但她说,当年办身份证的时候,父亲给她多报了两岁,“是想让我早点儿退休”;她也憧憬着几个月后能到手的24万,说要拿这笔钱去学日语,到国外打工,好离父亲远一点儿,再远一点儿。
父亲是她人生中最不愿意触及的部分。
母亲生完她几个月就因病去世了。不久,父亲又找了老婆,继母带来了两个孩子,张婧被要求喊他们“弟弟”“妹妹”。
张婧是被奶奶带大的,很多年里,她对父亲并没有什么认知。直到有一天,她无意中碰到父亲带着弟弟,在屋子里看色情影片。张婧说,父亲的形象在那一刻全面坍塌了。
长大后,她逐渐发现,父亲瞒着继母在外面不断找女人,前后带过几十个女人回家,“我爸是个很穷的男人,但他离不开女人。”张婧说,他宁可不要家人,也不能离开女人。她甚至透露说父亲“有性病”,他的微信签名写着,“人生,要看跟谁睡,睡对了才幸福”。
“我爸这一生都在谈恋爱。”张婧称,而继母大多数时候都在隐忍。
父亲的纵欲摧毁了张婧对婚姻的全部想象,她很早就断了谈恋爱和结婚生子的念头。
2022年6月高中毕业后,她去了一家咖啡店做服务员,每月工资2000元。
咖啡店离家不远,每天下班,她总会发现父亲带了不同的女人回家。这个沉迷女人的男人对女儿不管不问,也不会在她身上花什么钱——事实上,他原本也没什么钱,很多时候连自己都要靠80多岁的老母亲接济。
在这个南方小城,2000多元的工资仅够维持基本生存,张婧几乎存不下什么钱。
一次刷短视频,她无意中刷到了“招募试药志愿者”的内容。简单来说,就是药物上市前,需要做人体临床试验,正规的临床试验中心通常会招募一些志愿者去服用未上市的药,并从试药者身上采血,用于检验药物性能及稳定性等。
正规试药由临床试验中心直招。但有时正规招募应付不过来,这个业务便被很多中介承揽。一般情况下,临床试验中心会请相熟的中介负责招募。由中介招募的试药周期在一两周左右,根据药物品类不同,试药者能拿到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的补助。
张婧想要挣这种快钱。她联系到了中介,简单接触后,中介把她拉入了一个几百人的试药群。之后张婧发现,这个群里充斥着从事试药、代孕、卖卵、卖精生意的人。
做完常规检查,医生发现,张婧贫血,这意味着她无法成为那类药物的试药者。于是她回到老家,继续在咖啡店工作的同时,不时盯着那个试药群,想看看有没有适合自己的药物。
2022年11月前后,她在群里看到有人“高薪招募12-17天项目”。张婧以为是试药,加上对方微信一问,说是“捐卵”,做“卵妹”。彼时,张婧实际年龄不满18岁。
这位中介进一步解释说,他们的捐卵分为“盲捐”和“面捐”。所谓“盲捐”,就是客户只能得到女孩的卵子和资料,没法看到真人。“面捐”的话,可安排客户和“卵妹”见面。
“卵妹”中介
担心暴露隐私,张婧选择了“盲捐”。在这里,女孩子们是待价而沽的,学历、身高、年龄、外貌都决定着她们卵子的价格。中介以张婧只有高中学历为由,最终商议价格是2.5万元——张婧从未见过这么多钱。中介还告诉她,“这个很简单,躺那睡一觉就完事了。反正你每个月都要排卵,不利用一下,就白白浪费了。”
张婧心动了,她辞掉了咖啡店的工作,在中介安排下,到了一座南方城市。
从入住宾馆的第一天开始,就有一位自称护士的人,每天上门给她打促排针,一连打了近20天。被连续注射促排针后,张婧觉得腹部很胀,明显感觉肚子大了。“护士”说,是正常情况。
在宾馆住了20多天,她被带上一辆商务车,车窗也是黑色的,看不到外面。
目的地同样是一个地下实验室。在这里,张婧经历了麻醉。“医生”在B超引导下,用半个手臂长的取卵针(约35厘米)将卵泡液及卵子吸出。整个过程不到10分钟。
张婧隐约听说,自己大约被取了20颗左右的卵子。取完后,实验室的人私下加了她微信,说以后有捐卵或代孕需求可以直接联系,不用再通过中介。
卖卵的2.5万元很快到账。
张婧原本以为这件事就这样结束了。但不久,她觉得腹部不舒服,肚子依然很大。去医院一检查,医生说是腹腔有积水,给办了住院。在医院自费住了7天后,张婧告诉了中介。中介让她赶紧出院,说是他们有“售后”服务,可以安排人免费给她抽腹水。
接下来的几天,一个自称“医生”的人每天带着设备,到宾馆房间给她抽腹水。身体完全恢复后,张婧回了老家,找了家奶茶店打工。卖卵的2.5万元,刨去自费住院的6000元,她从剩余的1.9万元中,拿出4000多元买了部手机。
这是她第一次用这么好的手机。她把剩下的一万多元存起来,开心地在小城生活起来。这笔灰色收入让她认为,自己身上的东西是有着明码标价的,比如卵子,以及子宫。
机器而已
关于代孕的伦理讨论,互联网上论战不断。《人民日报》此前的报道中,有专家表示,“应适当放开代孕准入”“伦理不应该成为代孕技术的负担,而应成为促进技术有序发展的工具”。报道引发了2017年前后,新浪微博上一场有300万人参与的“代孕是否应该合法化”的讨论。彼时有声音认为,代孕或将解禁,但随后这个声音不了了之。
近年来,与代孕相关的话题更多聚焦在女权、压迫上。相当一部分女性主义者认为,代孕的本质是“母职交易”,是对女性的压迫——毕竟,这一工种甚至不受法律保护。东京大学教授上野千鹤子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社会》一书中认为,代孕这类“租借”子宫而获取金钱的买卖交易当中,买方总是男性,卖方总是女性。代孕妈妈不仅受到阶级和父权的压迫,也会受到市场经济的压迫。
张婧听不懂女权、压迫这些大词,她只知道,自己身体上的这些零部件是可以换钱的东西。之前在咖啡店打工时她从网上看到,说在国外打工很赚钱。她打听了下,说是去日本只需要3万元中介费。
张婧从卖卵剩下的一万多元中取出一点儿,报了日语培训班。准备攒够3万元后,去日本打工。可一段时间后,手头积蓄所剩无几,出国愈发遥不可及。2024年初,张婧想到了卖卵挣的那笔快钱,于是从手机上翻出之前在实验室添加的那个微信号。
对方就是殷丽。她告诉张婧,他们的主业是做代孕。
负责张婧代孕的中介之一
最初,殷丽想让张婧帮忙找个代妈,给她分提成,“要么帮我找代妈,要么帮我生一个。”得知张婧不认识这方面的人,她直接开价24万,“租下”张婧的子宫。
具体的付款方式,首先是每月发2000元工资;胚胎移植满30天且测到胎心后,付5000元;移植第3个月付18000元,移植第5个月付18000元,移植第7个月付36000,移植第8个月支付36000元。孩子生下来,鉴定DNA无误后付清尾款。其中的每一步也都有明码标价——如果是初次剖宫产的话,奖励20000元;有剖宫史剖二次宫产补偿10000元;假如生个双胞胎,额外奖励30000元。
而一旦移植后胚胎停止发育需要清宫或者药流,则再无其他任何“工资”和补偿。
见张婧有些犹豫,殷丽反复告诉她,“每个女人都是这么过来的,每个女人都要经历生孩子这件事,就看你自己能不能接受。”想到自己的父亲和去日本打工的理想,张婧同意了。
5月,她见到了对接她的殷丽。6月15日,在她当月例假结束后的第15天,顺利完成了胚胎移植,入住了“宿舍”。在那里,她又认识了中介里的另一个人——刘雷。事后张婧得知,这个刘雷,可能是中介老板。
这是张婧第一次怀孕。她排斥“怀孕”两个字,“你可以说她怀孕,但不要说我怀孕,因为我心理上不觉得自己是怀孕“;她也感觉不到肚子里那个胚胎的存在,只有在做B超时,才能模糊看到一个影像。平日里,她点着10元钱上下的外卖,绝大多数时间里在房间里待着,很少和其他代妈们交流。
妊娠反应很快出现了,她感到乏力、嗜睡、恶心、呕吐,情绪波动也大,中介不敢让她去大医院,把她带到了一个门诊部,这家门诊的主业是口腔。门诊出具的彩超检查报告单显示,“经阴道部探查示:子宫前位,增大,内见一大小约17×24×11mm的孕囊样回声,内见卵黄囊,见胚芽及心管搏动,胚芽长约2mm。”这份报告的送检医生姓樊。近日,该门诊人员告诉我,他们不知道代孕一事,“樊大夫已经离职了。”
当天,中介给她转了5000元奖金以及2000元工资。
代孕中介老板给张婧奖励的证据
那之后,她的产检又挪去了一家私立医院。刚开始的一段时间,张婧会拿着自己的身份证去检查。中介告诉她,后期生产的话,得拿客户身份证办住院,这样才能保证出生医学证明能办到客户名下。
身体上的变化是显著的,“比如说洗漱,原先简单几分钟就洗完了。可怀孕后,感觉好麻烦。”张婧说,洗漱前她得先考虑下,怎么从床上坐起来,如何弯身,怎样走到洗漱台把水龙头打开,如何拿着毛巾去接水。这种平时根本注意不到的细节,现在都会被放大。
偶尔,她也会闹情绪,比如去一次产检,闻到别人身上有狐臭味,觉得“好臭”,就此拒绝再去医院。刘雷说她太年轻,不懂事。一次,他给殷丽发微信说,“她欠骂,早上去做检查,又哭又叫的”“医院医生都不愿给她查了,说我们是不是强迫她来代的”。殷丽随后发微信开导张婧,“已经都这样了,就别矫情了”。
肚子里的胎儿在变大。9月15日的彩超检查报告单显示,“宫内见一胎儿回声”,胎儿体重170g±25g,双顶径38mm,头围131mm,腹围109mm,股骨长22mm,肱骨长21mm。胎盘附着子宫前壁,厚度约23mm,下缘抵达宫颈内口,成熟度0级,羊水最大深度52mm——这份报告的申请医师为该院妇产科的一位副主任医师,而在我们事后向院方问询此事时,对方先进行否认,随后马上挂断电话。
张婧在私立医院做的检查
这张A4的报告单没能唤起张婧任何母性,“我就是个机器而已,没有什么感情,这个行业就是如此”。
产业
提到代孕行业,包括张婧在内的很多代妈都会提到一个叫吕进峰的人。
2004年,27岁的吕进峰创办了一家代孕网,被不少人认为是国内首家地下代孕机构。后期,他在其官网自称“中国代孕之父”,他称自己本着“强烈的责任感”,从事着“助人为乐的爱心慈善事业”。
吕进峰当年的“创业”很简单——妻子怀孕后,他开始关注准妈妈论坛,捕捉到代孕商机后,买来几台电脑,注册一批QQ号,疯狂群发广告。客户、代妈、医生随之找上门来,吕进峰将几方环节打通,做起了代孕中介。
一个代孕宿舍里的代妈
早些时候,他只负责向客户介绍医生和代妈,从中收取两三万块钱的介绍费。2006年后,他全盘接手代妈事宜,将一条龙服务“打包”出售,这一模式被后来不少人复制并沿用至今。2020年4月27日,广州一家代孕机构被曝“自2015年底开始,已为超过400位男同性恋家庭提供代孕服务”。财新周刊2024年8月的报道中则提及,一位从业者透露,仅他所在的城市便有大大小小提供代孕服务的公司100多家,上规模的则近10家。据此估算,全国提供代孕服务的企业可能“有1000家的样子”。
根据中介给我们提供的数字,业内目前的市场套餐价是,70万左右不包性别,100万左右可以选性别,这其中,代妈能分到三分之一左右的费用。如果客户要供卵,除了套餐费外,还需另付3万至20万元不等卵费。
随着价格的水涨船高,想要出租子宫的人趋之若鹜,尤其是那些相对贫穷的女孩。
这次采访中,除了张婧,我还找到了28岁的周瑾。周瑾的老家在安徽山区,22岁那年,她和村里一个男人结婚,次年生下个男孩。
周瑾原本觉得,自己这辈子就这么过了。但丈夫总是出去赌博,输了钱,就拿她撒气。忍了几年后,周瑾决定离婚。男方留下了孩子,公婆给了她10万元算作补偿。拿着这笔钱,周瑾去县里开了家服装店,一年到头都在赔钱,积蓄慢慢耗尽。
2022年,一则曝光非法代孕的新闻,反而让周瑾看到了商机。
她在网上找到几家中介机构咨询,报价在20万元到30万元不等。周瑾起初有些犹豫,把子宫当作商品出售,让她觉得羞耻。但她很快说服了自己,“这个来钱快,更何况我都生过一个了,有经验”。
一个代孕中介提供的详细费用
戴上眼罩,周瑾被带进了一家地下实验室,完成了胚胎移植。
对于怀孕流程,周瑾很熟悉。中介告诉她,客户是对50多岁的失独夫妇,精子来自那个丈夫,卵子则来自一个大学生。那段时间,她总能收到客户隔三差五寄来的营养品——本着客户和代妈不能直接联系的潜规则,这些都由中介转交。而随着胎儿月份增长,周瑾如期收到了中介打来的钱。
2023年3月,周瑾的生产时间到了。客户提前赶来,中介用对方身份,帮周瑾办了入院手续,顺利生下了一个男婴。客户觉得周瑾人不错,当场给她包了两万元红包,相当于她最终拿到了27万的“工资”。
“打工”回到家乡,父母发现,女儿精神不错,还胖了一些;朋友们也都满脸艳羡地问她找的什么工作。“在有钱人家里做保姆。”周瑾说。
她原本打算拿这笔钱做点儿投资,考察一番后断了这个念头。2024年3月,周瑾再次联系中介,问可否再次代孕。中介爽快地表示,“当然可以,休息3个月就可以了。”
于是今年5月,周瑾再一次怀上了陌生人的孩子。
“我想好了,我也没啥本事,只要能生,就一直生。啥时候不能生了,还做这一行,自己做老板。”周瑾告诉我,她正在跟现在的老板学习,希望摸清整个产业链条。
有人说,做代妈这行,只要吃到了一次甜头,诱惑就一直都在。也因此,总有代妈选择不断接单。一位河南郑州的代妈告诉我,她做代妈,是自己老公推荐的,目前已经帮别人生过两个了。而她的老公,还专门在代孕宿舍周边租了房子,陪她遛弯、晒太阳、做产检。
那两个代孕的孩子,给这对夫妻换来了50多万元的收入。拿着这笔钱,他们把自己正上小学的儿子,送进了老家最好的私立学校。
流产之后
引产手术后的张婧,这些天就躺在医院十几平方米的房间里,翻看着手机。
早先那个卖卵的中介,依然每天发布多条信息,“招募捐卵志愿者,18岁至28岁,形象好、气质佳的大学生优先,补助10万+”。代孕中介也没闲着,经常在朋友圈发布类似“恭喜江西50岁王女士,成功验到胎心胎压”、“欢迎台州L先生夫妻来公司考察签约”、“感谢山东美女小姐姐寄来的冬枣,很脆很甜”、“恭喜河南31岁小美女移植”之类的广告。
这个市场太大了,张婧感叹着,“那么多生不了孩子的人、失独的人,都需要啊”。
那笔打了水漂的钱,也让她越想越不甘心。也是在流产后,医生才说,她宫颈短,容易早产,说是以后怀孕也得小心。她找殷丽打听客户的情况,问对方现在打算怎么办。“赔出去二十几万。因为妹子(卵妹)费用,还有三代手术费,还有给你的几万,加起来二十来万”,殷丽告诉她,客户目前只能重新找个代妈继续做。
张婧的出院记录
聊天过程中,殷丽还用另一个代妈的例子给她洗脑,“小李是经历三次才成,婷婷19岁经历的更多,你这个身体怎么就脆弱了?我告诉你,我身边认识的女孩,哪一个没有人流过几次”“为了赚钱肯定是要有牺牲,因为赚钱是最辛苦的”“但是人家有一颗坚定的心,不达目的决不放弃。”最后,她告诉张婧,“等你休息一下好好做事”。
不甘心的张婧通过微博私信,找到了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帮忙维权——不久前,上官正义通过卧底形式,举报了国内多家非法代孕的事件,也因此在代妈圈里小有名气。
11月12日张婧出院当天,上官正义带她去有关部门举报。对方说会安置好,并说要安排她再住几天医院恢复身体。他们同时建议张婧报警,后者听从了这一建议。
“你说我还能怎样,没读过大学,没有专业技能,做代妈还流产了。”她越想越觉得自己可悲,这些年她挣的钱,主要来自卖卵和代孕,一切都围绕着自己的身体。
她又提到婚姻,说以后如果必须成家,也得找个愿意丁克的男人。她心里清楚,很少人能接受她做过代妈,“这对男方来说不公平,所以我不找对象,也是一种善良。”
她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该去哪里,如同当年不知道那辆商务车将会把自己带去何方。医院要求两周后复查,中介表示不再负责;院方给她开出的一种药品,也被中介退掉了。
中介接张婧出院
“我出院后还能住宿舍吗?”她问刘雷。
后者立马拒绝,“宿舍也没有空地方的,那边房子过几天就要到期了。”但他也表现出了一个中介所能表现的最大“善意”,他让“懒懒猪”接她出院,并帮她在地铁站附近订了两天酒店,94元一天,“我个人补你一千块钱,给你当回家路费吧”。
还有家可回吗?张婧不知道,她不想面对父亲和他的女人们。
(文中所涉代孕母亲和中介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