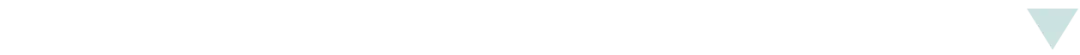富士康重回郑州,但情况变了
近一个月,三条“富士康”相关的消息接连引爆舆论:
一则是7月下旬,台湾媒体中时新闻网称,由于在印度生产线制造的苹果手机良品率仅50%,且测出大肠杆菌超标,富士康正将部分产能重新迁回中国,全力生产iPhone 16。
与此同时,河南日报载,7月22日,富士康与河南省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在郑州打造新事业总部大楼。河南省长王凯直言,“希望富士康坚定投资河南信心”。两天后,富士康母公司鸿海科技集团发出公告,称新事业总部项目一期投资达10亿。
然后是8月初,内地的社交媒体上,郑州富士康突击“高薪招工”、“两周进场新员工至少5万人”的消息开始刷屏。视频中,火红的招聘易拉宝立在富士康厂区门口,大字写着:“加入我们,梦想在这里起航。”
后疫情时代,富士康曾加速将产能撤离中国,转移至印度、东南亚等地,一度引发国人焦虑: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江湖地位,可能就此不保?
如今一连串“回暖”的信号,实在耐人寻味。网友惊叹,“富士康太牛了,一下子解决5万人就业。”观望中的香港媒体也评论道,“富士康‘回归’中国内地。”
所以,富士康真的回来了吗?
上个月底,在已经严重磨损的手机屏上,许宝坤看到一条让他振奋的招工信息:富士康把产能从印度迁回中国,正在郑州大量招工。
他是91年生,初中学历,老家在河南驻马店农村。这条招工信息无疑给赋闲一个多月的他打了一剂强心针,他当天就出发前往省会郑州,打算赶紧在郑州富士康超级工厂找点事做。
这个超级工厂位于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是富士康在郑州三个厂区中最大的一个(以下简称港区富士康),也是全球最大的苹果手机生产基地。工厂距机场仅6.3公里,每天至少有3趟航班为它运来高端零部件,也有五六趟航班将其产品出口到全球一百多个国家。这里占地560万平方米,相当于784个足球场,沿着宽阔笔直的雍州路两侧,分成从A到K的多个子厂区。
G南区旁就是港区富士康的招募中心。8月12日早晨,距8点正式开门还有十几分钟,等着面试的新工人已零散排出十几米,有人拉着行李箱,也有人在马路牙子上或蹲或坐。电子喇叭反复播报着一个男低音的防骗通知:“未穿蓝色马甲的不是工作人员,不要理会,避免被骗、丢失财物或无法入职。”
距招募中心稍远的路边,站着三三两两的小中介。一旦出现新面孔,中介们就涌过去追问“进厂吗”,试图努力把对方拉进自己的招工咨询群。群里的富士康招工广告写着,招工的年龄区间从18到48岁,“不查学籍,不查流水,今天返费8000,小时工26,免费被子3件套+50元车补”。
“现在每天一千多人面试肯定是有的。”一个中介向凤凰网表示。
这个8月,富士康大门敞开,工人哗哗涌入——每年7-9月是这里的招工旺季,招的主要是临时工,又细分为小时工和派遣工。“富士康的临时工收入比正式工高。”另一个中介表示。
其中,小时工按照工作时长计价,进厂后先和富士康正式工同工同酬,差价会在每月28日发放;派遣工也先和正式工同工同酬,但在工作一定期限,比如3个月后,可以领取一笔额外的奖金,即“返费”。
在港区富士康附近的招工中介报了名,经过简单的面试、培训,许宝坤丝滑入职港区富士康,成为一名临时工。他被分去了流水线组装iPhone 16,这是苹果公司计划在2024年9月10日全球发布的新品。
紧锣密鼓的苹果筹备季里,富士康成了一个巨大的就业蓄水池,那些颠沛流离的低学历农民工、找不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大龄”的职场失意人,通通都被收留。
得知富士康派遣工的返费涨到8000元后,22岁的谢俊也从郑州家中来到了港区富士康。
他是2024应届本科毕业生,学的是土木工程。房地产行业曾贡献了中国近25%的GDP,被称为“中国最大的就业蓄水池”,但如今,在被外界调侃为“烂尾楼之都”的郑州,谢俊没能找到合适的工作。
富士康成为他短期过渡的首选。富士康的员工级别分员级和师级,他被定级员一,富士康最低的普工级别,和初中学历的许宝坤一样,底薪2100元。
从2024年这个季度看来,就业指标是蓬勃向上的,比如招聘人数的增加、临时工工资的上涨、面试通过率的提高。金可诚是郑州一家大型人力资源公司的负责人,多年来一直为富士康招工。他表示,今年5月到8月,富士康派遣工的返费从4500元一路涨到了最高8000元,小时工的价格也从22元每小时涨到了最高26元,现在进富士康工作3个半月,可以拿到将近2万元,“这在郑州属于比较高的收入”。
招工旺季的巨大涟漪,迅速扩散到了毗邻港区富士康的沃金商业广场周边:一位60岁的电三轮司机对凤凰网表示,以前一天拉不到100块,现在一天能拉200多;一家服装店的店长也说,营业额在半个月内上涨了50%。
“人回来了,生意就回来了。”服装店里,这位40多岁的个体户女老板扬起眉毛说。
说“回来”,是相对“离开”而言的。
前两年,“富士康重仓越南印度”“富士康加速撤离中国大陆”的新闻传遍了财经媒体——对郑州经济而言,这无疑是个沉重的消息,毕竟富士康在2018年曾以一己之力占去郑州超过80%的出口额——接着,多米诺骨牌接连倒下:2024年一季度,河南手机出口量断崖式暴跌61%,导致一季度河南出口额大跌23%。
在因富士康而兴的郑州港区,人们密切关注着和中国制造相关的国际大事,哪怕一个车间工人也会在茶余饭后不时谈起“印度制造”,以及自己在某种意义上的竞争对手:印度工人。
“印度劳动力比中国更廉价。”严枫华是一位在郑州富士康工作了12年的老员工,在她看来,富士康在人口更多、更年轻且人力成本更低的印度建厂,不啻为一个理性选择——去年,印度超越中国,成为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印度全社会平均年龄只有29岁,而中国是39岁。另外,印度工人的工资不到中国工人的三分之一。
苹果的全球战略部署证实了工人们的推论。iPhone是苹果最赚钱的产品,2023年底,印度生产的iPhone占到了14%,如果不出意外,几年后这个数字会达到25%——而在2022年之前,超过96%的全球iPhone都是在中国大陆组装的。
谈及印度这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时,郑州富士康的工人多数抱有善意的理解。“中国也曾是一个农业大国,也是这么一步步走过来的。”严枫华说。“东南亚要发展,印度也要发展,就像中国改革开放时吸引外资一样,你不可能阻止人家。”在富士康工作了14年的李林说。
但意外终究发生了:在素有“外资坟场”之称的印度,富士康的发展一路坎坷。2024年7月23,一则来自台湾中时新闻网的消息称,“印度厂iPhone代工的良率(仅5成左右)”且“卫生管理(大肠杆菌超标)仍存在问题”。尽管这则消息并无确证,另一些现实却确凿无疑:
2023年7月,富士康母公司鸿海对外宣布,退出与印度金属石油集团韦丹塔合作的195亿美元芯片制造计划。当时路透社、彭博社等报道,原因与该工厂建设缓慢、补贴迟迟不发放等有关。在2024年的夏季高温中,富士康的印度工厂还被政府要求减少30%的用电量,断电成了家常便饭。诸多“不测”,让印度富士康的产能远不抵预期。
富士康在印度建厂后,严枫华的一些同事曾被派去支援。回到中国后,他们的感慨之一是,用同样的机器,在中国可以生产出来的产品,在印度生产不出来,“我们对品质的管控标准,他们理解不了”。感慨之二是,在印度,富士康的政策很难执行下去,哪怕这些政策合法——一度,印度卡纳塔克邦为了配合富士康的生产,将政策改为允许12小时倒班、女性上夜班,但愤怒的工人们烧毁了法案副本,当地装配线工人帕德米尼告诉媒体他无法容忍高强度的生产线:“我必须活着才能工作。”
比起印度,中国富士康堪称效率的王者。严枫华记得,一次,郑州富士康要向员工宣导品质政策,决定大约在当晚8点出台,到第二天,这项品质新政的打印版本已经贴满了车间,并在每个厂房门口的电视屏和LED屏上滚动播放,早晨8点开会前,员工们每人都领到了一张,由厂长带领大家现场背诵:
“全面品管,贯彻制度,以提供客户需求的品质。全员参与,及时处理,以达成零缺点的目标。不接收不良品,不制造不良品,不流出不良品。”时至今日,这段“箴言”仍不时浮现在严枫华脑海里。
但对富士康来说,将低端产能向印度等地转移,或许已是长期趋势。近日,财富中文网分析指出,此次富士康产能回迁是为了保障iPhone 16系列的平稳出货,这充分肯定了中国代工厂的能力和价值,另一方面,这也是给印度方面更多的时间做准备,以便在将来承接更多的产能。
8月17日,富士康董事长刘扬伟宣布,2025年将加大对印度的投资。
许宝坤没有关注这些经济新闻,他更关注的是印度的国民性。通过那台799块买来的小米手机,他刷到过包括种姓制度在内的科普知识,他得出结论:“印度人比较慵懒,会享受,不会为了钱太拼命,不太好管理。”
“中国人对名利看得更重,用这个就可以管理好。”他做了一个数钱的动作。
挣钱一直是许宝坤生活重大的母题。18岁那年,他离开驻马店老家去北漂谋生,因为他被《士兵突击》中的许三多打动,想成为下一个王宝强,“他长相也普通,家境和我一样,对不?”
在后奥运时代蒸蒸日上的北京,许宝坤努力挣钱:他在八一影视基地做过群演,演一个国民党反派,日薪90元;他去工地打过杂,也通宵装卸过快递;打过最久的一份工是当小区保安,月薪4000元,不累,但那份工作时常让他自卑——开好车的业主有时会凶他,“他们看不起我们,脾气很大”。
而在富士康,按照招工时25元一小时的承诺,即便不加班,每天只工作8小时,许宝坤也能拿到200元的日薪。一进厂,他的工牌里就被充上了400元饭费,这是富士康提前预支给工人的,发工资时再扣,“对没钱的人很方便”。宿舍是6人间,150元一个月,水电免费,“很干净”,还有两个厕所,远胜日结房和桥洞。如果表现良好,他还有机会转成正式工,领到五险一金——他以前的工作从未有过五险一金。
许宝坤感到自己被赋予了尊严。“你感觉自己就是个正常的工人,没有那种痛苦、自卑的感觉。你是来挣钱的,我也是来挣钱的,大家都是平等的。”
当被问及富士康最好的地方,几乎所有工人第一时间都下意识脱口而出——“富士康从不拖欠工资。”每个月的7号,富士康一定会准时发工资。“不管行情好不好,富士康不拖欠,不克扣。哪怕你只上一天班,也能拿到这一天的钱。”严枫华说。
在这里,如果正式工被裁员,会有N+1赔偿——这在劳工阶层并不多见,前富士康员工王雄飞的两个朋友最近被一家私人门窗厂开除,没有领到一分钱赔偿。进厂初期,他经历过一次2小时的停电。那2小时,富士康也算进了工作时间。
况且,对都是河南人的他们来说,这还是一份在家门口的工作,再不用背井离乡北上南下打工了。
尽管2010年从深圳内迁到郑州、成都等地主要是出于降低人力成本的考量,但无意之间,富士康引领了中国制造业的一大风潮:离土不离乡。
“在家门口就能得到和走出去一样的工作——待遇一样,环境一样——这点很有吸引力,尤其是对有孩子的人。”一直参与富士康招工的金可诚说。
当时郑州富士康已经能辐射到开封、许昌、焦作、新乡、洛阳等地,吸引全河南的劳动力。河南的一些县甚至开通了定制车,从县城直接开到港区富士康,天天发车。根据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数据,2011年,河南省内务工人数首次超过了省外。
散落在全国各地的不少河南打工人因此返乡,进入富士康。他们往往来自农村,家境不佳,学历不高,“一般就是初高中”。
李林在2010年加入郑州富士康,并被送到深圳富士康短暂培训。那一年,深圳富士康以“十几连跳”扬名世界,还因此背上“血汗工厂”之名,但对了解过煤矿工作的李林而言,这已经是自己当时最好的选择,“富士康的收入比不上煤矿,但没那么辛苦和危险,工作环境也更好”。
“富士康是很好的厂,就算跑到广东、江苏,这样的厂也是数一数二的。”许宝坤感慨。
十年间,在港区富士康周边,一个庞大的“富士康城”逐渐成型。村民在拆迁后搬进了高层安置房,酒店、酒吧一条街、大型超市、KTV和服装、餐饮店逐一出现。
金可诚表示,制造业用工人数和周边服务业人数比一般是1:1.2。也就是说,1个富士康的工人,会吸引来1.2个人为他提供衣食住行服务。这相当于最高峰时,郑州富士康养活了70多万人。
对河南人来说,这是托底的安全网、最起码的念想——再不济,还可以去富士康。
作为郑州富士康的第一批员工,王雄飞和李林一路见证了公司这些年的起落兴衰。
“河南是人口大省,当时制造业不发达,就业条件很差。”他们记得,2011年3月港区富士康正式投产时,周边很荒凉,厂房周围的田野里后来还在种玉米、小麦和花生。这里位于郑州市所辖中牟县,土质是沙土地,风一刮,身上都是土。当时一些厂区还没有食堂,周边摊贩甚至可以进去卖小吃。
也是在2011年,他们开始生产苹果的iPhone 4S,做的是焊接工作。iPhone 4S很快成为苹果的经典和爆款机型之一。到2014年左右,港区富士康的员工数达到了30多万。进富士康前,王雄飞在郑州的一个食品厂短暂待过,一天工作12个小时,到手1000元左右,但富士康让他的工资瞬间涨到3000多元。“富士康来了,周围的工厂工资都涨了。”他说。
但这几年,老员工李林发现自己的收入并没有随着GDP和物价同步上涨。2017年,他的底薪是2100元。2024年,他底薪是2400元。他给凤凰网展示自己手机上的纳税记录。作为一个郑州富士康14年的正式工,今年上半年,他的月平均工资为4500多元。
最高的一个月是3月,近7000元,其中包括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年终奖。最低的一个月是2月,因为无班可加,只拿到2400元底薪。
2023年也是如此。这年春节后直到5月,郑州富士康的业务惨淡,员工想加班几乎都没有机会,很多正式工每月只能拿2000多元的底薪。尽管每天围着iPhone系列转,直到现在,李林还没有用过一部苹果手机。
“今年不比去年强多少。”他表示,5月前,自己单月加班时长只有3-4个小时,到了临近旺季的6月,加班才多了一些。
不知道什么时候起,李林发现,富士康的工人越来越少了。iPhone的尺寸、色差监测和螺丝装拆等工序,以前靠人工,现在靠机器。“前端只需要几个人放物料,传动带把它们送到机台,机械臂抓取后自动加工。”
“这几年机器多了,人少了。”严枫华也说。
疫情,是郑州富士康的一个转折点。尽管此前苹果已经在将生产线转往印度、越南等地,但疫情之后,因为地缘政治压力、争夺新兴市场等因素,苹果加速了产业链的转移。很多富士康的工人就此离开。他们去往附近的其他电子厂,去送外卖,做装修,或者再次去往南方打工。
当富士康随苹果加大在印度和东南亚的布局后,国内网上出现了各种极端论调:“河南不缺一个富士康”“富士康走了就走了”“富士康滚出中国”……
每次看到这样的言论,王雄飞都很气愤——“他们不知道富士康给河南带来了多少东西。”
如今,港区富士康的工人已经从30多万降到了10来万。尽管2024年8月难得迎来了一个用工高潮,但金可诚知道,这样的盛况只会持续3个月,仅如昙花一现。过去那种招工忙到晚上12点、人们为了进富士康当工人给中介塞钱的日子,一去不返了。
对于此前富士康“两周进了至少5万人”的报道,金可诚表示,“是计划招5万人,但目前还没招满”。他的观察是,和前两年相比,富士康今年的招人指标在下降,他的公司“利润比前几年还少”。
即使目前富士康大门敞开,招的也大都是临时工。他们与人力资源管理公司签署合同,属于第三方派遣,干完旺季就走。这有利于富士康在短时间内(尤其是突击iPhone新品发布的时刻)迅速扩张产能。但生产旺季一过,临时工们就会像候鸟一样离开。
2012年苹果还一骑绝尘时,中国青年报指出,如果要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在整个世界产业链中,苹果是美国的代表,富士康就是中国的代表。
作为劳动力密集、利润微薄的代工企业,富士康的危机其实早已浮现。
毛利润率整体在降。根据鸿海8月14日公布的2024第二季度财报,其毛利率为6.42%。而在15年前,其季度毛利率最高曾超过10%。
在中国市场,富士康最重要的客户苹果也大不如前。2024年第一季度,在全球智能手机销量榜上,三星排第一,苹果排第二,排名对换。彭博社引述一位专业人士分析称,排名变化的重要原因是“中国市场竞争加剧”。
第一次看到iPhone 4S时,王雄飞曾倍感惊艳。那时他用的是一部1000多元的国产安卓手机,反应迟钝,时常卡顿。而iPhone 4S的屏幕非常灵敏,“点哪个就是哪个”,一点不卡顿。
但现在,国产手机的性能已经跟上来了。2024年第二季度,苹果手机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掉到了第六,排在vivo、OPPO、荣耀、华为和小米之后,四年来第一次跌出前五。
富士康也有了新的代工竞争者,比如比亚迪和立讯精密。如今,它们都加入了iPhone 16供应链。
长期以来,大幅减员增效、临时工取代正式工、无人化,都成为富士康控制成本的发力方向,势不可挡。
这引来了人们的忧心忡忡。“河南有9000多万人口,无人化以后,这些人怎么找工作,特别是学历不高的?”王雄飞问。
如今,“富士康城”也盛况不复了。正值招工旺季,多家店铺却已歇业,门口贴着“旺铺转让”,剩下的店铺也在下调租金。一家女装店负责人向凤凰网表示,这里曾经请了七八个员工,现在只请了一个。另一家女装店最贵的商品从139元降到了69元,店员称,“临时工干几个月就走,不舍得消费”。2016年iPhone 7 Plus刚上市时,一个生意兴隆的服装店老板花6000多元买过一部,现在生意不好做,她用的是一部2000元的vivo。
张庄距港区富士康5公里,是附近最大的城中村,也是很多富士康工人的廉价租房宝地。如今这里正在拆迁,一位有100多套房的村民和政府没谈拢。进村的路因拆迁被挖得乱七八糟,加上工人锐减,他的房间出租率从当年的100%降到如今的不到30%。
他发现,张庄开始拆迁后,一些富士康的工人就离职了——没了城中村,他们的生活成本直线上涨。
这位村民说,张庄办事处之前组织他们开拆迁动员会,提到“你们房租也收够了”。
他心想:“那是时代给我们的红利。”
对刚进港区富士康三天的打工人许宝坤来说,公司的战略转型还过于遥远。眼下,他感觉自己已经被机器人打败了。
他说自己记性不好,做iPhone 16模具整合的流程,怎么也学不会。他又被安排去捡机器人焊接后的手机,因为手速不够快,一直堆积。身边的同事不停帮忙,这让他心理压力巨大,权衡再三,他选择了主动离职。
在“富士康城”一个商场的长凳上睡了几晚,他还是没能找到合适的工作。刚从驻马店老家来郑州的他,现在又得回老家了。但家里的地早就包给了别人,他回去也无地可种。
带着全新的被褥脸盆,坐在“富士康城”最繁华的十字路口一角台阶,他几次打开一盒已拆封的红旗渠香烟,却始终没有点燃一根。33岁,初中学历,身无长技,他不知道应该去往何方。
感觉到危机的富士康,也正在努力寻找新方向。2023年,富士康新事业总部在郑州揭牌。当时富士康董事长刘扬伟表示,要在河南省再造一个“新的富士康”,专注于加速电动车整车、储能电池、数字健康和机器人产业落地。
2024年8月中旬,凤凰网实地探访了未来的富士康新事业总部所在地。这里距港区富士康42公里,和郑州市郑东新区中原科技城创新孵化基地大楼仅一条马路之隔,目前还是被围挡拦起来的一片空地,上面覆盖着绿色防护网,停着一台挖掘机、一台推土机。
旁边一个小卖部的老板表示,富士康和河南省政府的战略合作签约仪式是在7月22日签署,四天后,这片土地开始平整,“没几天就平好了”。
在旁边的中原科技城创新孵化基地,一栋大楼上写有“富士康新事业总部”字样。大楼的其中两层,就是富士康新事业总部的临时办公地。其中一层正对门的办公室门口写着“EV(电动车)制造发展中心”。
李林说,富士康一直想造新能源车,过去也有一些动作,但这次,“看来是动真格的了”。也有同事犯嘀咕:这个领域已经是一片红海,现在入局会不会太迟?有人听说比亚迪也在招工,而且工资更高,开始四处打探机会——他们想去更能挣钱的地方。
无论如何,李林选择在富士康留下来。
十多年里,iPhone从4出到了16,李林感觉自己的生活毫无变化。到点上班,到点下班,缺乏社交,人变得麻木。他已经习惯了钟摆一般的生活,离不开了。
而有些时刻,王雄飞也在想象“回归”富士康。在富士康工作四年多后,他选择了离开,去看看不一样的世界。后来他做过很多工作,比如手机分期、游戏搬砖,还有一次,他失业了好几个月,直到在郑州开起了网约车——探索世界的结果是,他慢慢意识到,很多工作“比在富士康上班还累”。
“我想进富士康。”王雄飞的另一位网约车同行也这样告诉凤凰网。这位司机曾任职于一家知名电商零售企业的物流部门,2022年,35岁的他在被裁和转岗中选择了被裁。他想进几家有物流业务的互联网大厂,但HR的回复如出一辙:“超过35岁不要。”
当上网约车司机后,他每天早晨6点半出车,工作超过12小时,自己交社保,不安全感时刻萦绕。他也发现,这份工作并不自由——“几点出车,几点收车,赚多少钱,都被平台的大数据控制得很死,每天基本不会有浮动。”
于是,曾被诟病“沉闷”“不自由”的富士康有了某种强烈的吸引力:它稳定,招工年龄上限宽容到了48岁,正式工有五险一金,离职还能拿N+1。
他们开始惦念和向往富士康,仿佛那在机器运作声中高速运转的流水线,奏出了打工史上一曲美妙的乐章。
应受访者要求,许宝坤、谢俊、严枫华
王雄飞、李林、金可诚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