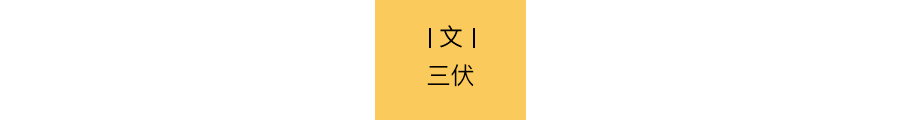高中辍学打黑工,她成了“顶流作家”


独家抢先看
谁也不曾想到,2024年评分最高的国产剧,是一部只有8集的《我的阿勒泰》。
像是躲进了现实的乌托邦,网友评价看完这部剧的感受:我好像潮湿的腐木,晒到了阳光。
在剧集的渲染下,阿勒泰成为新的旅游圣地,“人在工位,心在阿勒泰”的心情散落在网络各处。
而剧中女主李文秀,正是李娟的化身。
在李娟的笔下,有关阿勒泰的一切如河水般流淌出来,她的母亲、外婆、人生的一切都随着水流摇摇晃晃。
她从《九篇雪》写到《遥远的向日葵地》,从春牧场写到冬牧场,从一个辍学打黑工的少女,写到人民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的获奖人。
她将人们遗忘的记忆捡起,她一路走,一路写,成为如今的李娟。
阿勒泰的冬天,是一望无际的、浩大的白。
一场雪叠在另一场雪身上,下得凶时,能垒到几米高。李文秀从厚厚的雪堆中出现,奋力挖着雪道。
半天时间过去,雪道的长度停留在十米,“于是在冬天最冷的漫长日子里,没有一行脚印通向我的家”。
伴随着原著旁白,阿勒泰的故事由此开始。
《我的阿勒泰》剧照
李文秀高中辍学,在乌鲁木齐一家饭店打工,梦想成为作家,却遭到周围人的耻笑。
被迫回到彩虹布拉克后,她跟随着母亲在草原上开小卖部一起生活。她在夏牧场交到朋友,陷入恋爱,狠狠受伤。
她用柔软的眼睛抚摸着阿勒泰的森林、草地和河流,用文字记录着生活的一切,写出直击人心的文章。
《我的阿勒泰》剧照
这是李文秀的眼睛,也是李娟的眼睛。
2020年,导演滕丛丛决心要将李娟的散文集《我的阿勒泰》影视化,她对原著进行了大刀阔斧地改编,只保留了故事原本的筋骨。滕丛丛在采访中讲起:“李娟有自己看待这个世界的独特视角和价值观,她对生活的感知是极具天才质感的。”
打开李娟的生命,她所看到的阿勒泰,比雪更宽厚与自由。
初读李娟的书,她的文风诙谐,视角温暖,阿勒泰的万物在她笔下活得丰盛。
阿勒泰的猫是潇洒的。李娟与母亲收留了许多只流浪猫,其中一只猫仅在快生仔时才在路口黏住李娟母亲,到家后和家里的原住鸡原住狗点头哈腰,生完孩子就扬长而去。李娟母亲常常一边破口大骂,一边又兢兢业业照顾这只江湖女侠留下的子嗣。
阿勒泰的牛是狡黠的。小卖部的帐篷仿佛有种魔力,每到夜晚都有源源不断的牛来帐篷后蹭痒,把篷布弄得哗哗响。李娟每天忙着赶晚上聚会的牛,外婆负责清理帐篷前的牛粪。外婆跟不上牛的脚步,牛就故意等在前面,等外婆到跟前了,再送她一堆。
阿勒泰的猫和牛 李娟摄
阿勒泰的人行走在浩荡的天地间,活得无比艰苦却又无比豁达。印象深刻的有一位名叫比加玛丽的哈萨克族母亲,她的一个孩子在两岁的时候被她失手烫死,另一个孩子在不满周岁时在被窝中捂死了。李娟去她家做客时,她把孩子的照片给李娟看,得意地说:“怎么样?漂亮得很吧。”语气中毫无悲伤。
死亡在草原上是一件平常的事情,活着的人才要将颠簸的生活闪亮地过。
没事的时候,李娟躺在草地上睡觉。一朵云带来一片雨,她被雨叫醒,来不及醒神,迷迷糊糊往前走几步,到没雨的地方接着睡。
她如此写阿勒泰:“北疆之北是阿勒泰,她是狂野的梦,她是山野的风,奔跑在凉夏,沉静在寒冬。”
《我的阿勒泰》剧照
很多人评价李娟是天生的作家,是中国近现代文坛的精灵。作家苏北曾说:“我要是能和上帝通上话,我就请他一定要永远将李娟留在人间,专门让她写文章给人看,给人们带来美和快乐。”
事实上,李娟的眼睛充满感伤。她说:“快乐是我的情商决定的,悲观是我的智商决定的。”
阿勒泰的春天温暖干燥,初生的羊羔一朵朵点缀在草地上。
草地远看是葱葱的绿,近看还露着地表的颜色。雪就要挥手作别,但风气势汹汹地来了。
2007年春,李娟跟随牧民扎克拜妈妈一家生活在春牧场上。狂风卷席着沙土,呼啸着吹过李娟头顶的帐篷,也吹过她漂泊无定的人生。
阿勒泰的风 李娟摄
李娟出生在新疆,但她心中的故乡不在这里。
她与新疆的缘分要追溯到更早一代人,许多年前,李娟的外公外婆在四川谋生艰难,来新疆投奔亲戚,在这里生下李娟母亲。
父亲的角色在李娟的生命中始终缺席。李娟仅在新疆生活了很短一段时间,两三岁时,她被送到四川,和80多岁的外婆一起生活。
李娟在书中记录过自己的童年,是一段被暴力围绕的日子。
在四川上小学时还存在体罚,李娟的班主任想出一招:每次成绩排名出来后,让班里的学生互相打,第一名打倒数第一名,第二名打倒数第二名……
放学后,还会有男同学守在必经路上,不是青梅竹马的青涩往事,而是等着要踹她胸口、抽她耳光、烧她头发。
某一年,她回新疆插班上小学,因为身后人叫了一声,李娟回头看了眼,被老师抓到,让她自抽耳光,抽了整整一节课。中途声音小了,老师还要她抽得再响亮些。
下课后,老师径自走了,李娟依旧不敢把手放下来,直到同学们三三两两离开教室,她才逐渐减轻力度,最后捂着肿得高高的脸哭出来。
很长的一段时间,李娟被黏在挨打的恐慌与痛苦中,无法抽身。她在无数个日夜里将这些事翻捡出来,反思是否被伤害都源自自身的问题,是否是自己太惹人讨厌了。
可“她小时候除了邋遢和虚荣,实在没啥大毛病。她胆小怕事,老实巴交,并且热爱文学”。李娟百思不得其解,唯一的答案大概是,她的母亲远在新疆,身边只有年迈的外婆,是一个承接校园暴力的完美容器。
“被人欺负这种事,最大的恐惧并非源于伤害本身,而源于从伤口中渐渐滋生的宿命感。”许多年后,她如此写道。
李娟
在那段无助的日子里,文字成为李娟与生命对话的介质。
小学一年级时,李娟捡到一张旧报纸,挨个读出认识的所有的字,这件事给了她巨大的震动。“好像写出文字的那个人无限凑近我,只对我一个人耳语。这种交流是之前在家长老师及同学们那里从不曾体会过的。”
她开始自己动手写。最开始给远在新疆的母亲写信,一周写一封,文字夹杂着拼音。那时她还是结巴,话说得磕磕绊绊,但笔下的文字却可以像流水般流淌出来。
小学二年级,她的作文写得洋洋洒洒,是同学中字数写得最多的。语文老师笑着说:你这么能写,以后可以当作家。
当作家。风似乎在李娟的耳畔吹过。
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她给报纸投稿,可惜只听过骗子的回声。中学时期,李娟回到新疆,和母亲一起生活。她的学生时代结束在高三的一节英语课上,那天要考试,她找不到自己的小抄,干脆跑回宿舍,收拾好行李,直接退学了。
后来她解释:“我也不是很适合校园生活,因为开始住校了,不太适合集体生活,学习也不是很好,也不讨老师喜欢。所以,想想还是当作家吧,不要浪费时间在学习上了。”此外,还有经济方面的掣肘——某次班里要收90块钱,母亲让她告诉老师,缓一缓再交。
李娟旧照
只是,成为作家不是一件容易事。
离开校园后,十八、九岁的李娟去到乌鲁木齐打工。她做过地下服装厂的流水线工人,做过车工,入不敷出,根本攒不下钱。
她在文章里写下那个年轻的李娟:“乌鲁木齐总是那么大,有着那么多的人。走在街上,无数种生活的可能性纷至沓来。走在街上,简直想要展开双臂走。晚上却只能紧缩成一团睡。”
但她依旧不想离开。她在等一场穿过身体的大风。
风来自阿勒泰草原。
1999年,20岁的李娟的文章首次刊登在《中国西部文学》上。有人质疑她是抄袭,新疆作家刘亮程为她正名:“不可能是抄的,她找谁去抄?中国文学没有这样一个范本让她去抄,这只能是野生的。”
野生的李娟跟随母亲的杂货店来到牧场。那是2000年,她一边生活,一边创作,文字如河流般源源不绝。
夏天的草原上鲜花遍野,密集的雨水带来河流的汛期。
牧民逐水草而居,河流是草原的母亲。河水暴涨时,水流浑浊,交通受阻。河水平静时,自在流淌,滋养万物。千百年来,河流怀抱着无数的生命,“才开始它们如吸吮乳汁般吸吮河流,到后来如吸吮鲜血般吸吮河流”。
无数个漫长而晴朗的黄昏中,李娟与母亲顺着河一直走。河流之于草原,就是母亲之于李娟。
《我的阿勒泰》剧照
《我的阿勒泰》中,李文秀的母亲张凤侠人如其名,是个风风火火的汉族女人。她独自一人去到很远的地方买羊,骑着骆驼走在古老的仙女湾小道,英姿飒爽。
剧中的张凤侠有着李娟母亲的灵魂,但多了些对爱情的执着,少了些人类本身的复杂。
现实中,李娟与母亲的关系并不融洽。她在书中如此描述两人的关系:“我觉得,只要付出努力,我就能洞悉世上的一切秘密,但除了我妈的心和她的记忆。她所记得的永远和我记得的不一样。她的心永远在我的追逐和猜测之外。她是这个世上我最无能无力的人。”
母亲曾带过她内心最深的痛苦。
那是李娟从四川回到新疆的第二年,收到了来自四川好友的信。彼时她有个同学,品学兼优,是家长眼中的香饽饽。
同学想看李娟的信,李娟不给看,两人开始争执,母亲从她身后抢过了信,当着所有人的面大声朗读信里的内容,一边念,一边鄙夷地点评。
这些话曾深深扎在李娟心里,把她身体割出一个大洞。
但河流有时不管不顾的凶猛,有时也带来峰回路转的救赎。
远处的李娟母亲 李娟摄
2003年,李娟发表了第一本散文集《九篇雪》。同年,她在朋友介绍下,进入当地宣传部工作。
她来到阿勒泰,一边上班,一边照料难以自理的外婆。那时,母亲总是冒雪赶到市区,给她带来无数东西。
某次,她带着两根三米长的竹竿以及三到五个人的行李,独自坐班车进城。
第一天,母亲在省道旁等了半天,才知道班车坏了。第二天,她不死心,继续等,终于顶着风雪给李娟带来了两根竹竿,只是为了让她晒衣服更加方便。
但这样的母女情感篇幅不多,更多的时候,李娟在记录母亲本身的力量。
李娟母亲早期是兵团职工,做过教师,因为和家长干仗怒而辞职。也做过农业技术员,养的猪逾千斤,打破连队猪场历史纪录。青春的记忆堪称辉煌。
后来,她在牧场上开了个裁缝店,继而又开了杂货铺。她和周围人的语言并不共通,却总能凭借自己的理解与表达,自洽地活着,甚至影响着周围的人。
道路的尽头是母亲的小卖部 李娟摄
2007年,李娟母亲在荒野里种了一百亩向日葵。她每天骑摩托车往返向日葵地和村里的小卖部,目标是每天赚到80块钱——才能雇得起工人收割向日葵。
独自一人守着向日葵地时,太阳强烈,母亲赤身裸体地走在干裂的大地中,汗水反射着圣洁的光,手里的铁锨像是女王的权杖。
“她双手粗糙,裂痕遍布,上面的陈年污迹怎么洗也洗不干净。她放弃了肉身的美好,不顾一切榨压最原始的力量……她是我见过的最沉重也最庞大的生命。”
这也是李娟眼中的母亲,人生宽广得像一条波澜壮阔的河。
阿勒泰的秋天是金色的,漫山遍野的向日葵仰着脖子,路过的树也染上颜色。
2008年的秋天对李娟来说,是离别的季节。
种下向日葵的那年,阿勒泰恰逢大旱,种植户赔得血本无归。河下游有个承包了三千亩地的老板因此自杀。
李娟回家看母亲和外婆,问起自家的收成。母亲气势磅礴地回:“幸亏咱家穷,种得少也赔得少。最后打下来的那点葵花好歹留够了种子,明年老子接着种!老子就不信,哪能年年都这么倒霉?”
再问到外婆,外婆只高兴地说:“花开的时候真好看!金光光,亮堂堂。”
正在吃饭的外婆与一直忙碌的母亲 李娟摄
与电视剧《我的阿勒泰》中的奶奶不同,陪伴在李娟身边的祖辈,只有外婆一人。外婆像一棵树,古老,沉默,又孤独。
在四川的那些日子,祖孙俩相依为命,靠外婆捡垃圾维持生计。后来李娟回到新疆,85岁的祖母独自在乡下种地。直到2000年,外婆被母亲接到新疆。
李娟在阿勒泰的城市里工作时,将外婆接在身边照顾。
李娟每天下班时,总会看到外婆趴在阳台上,眼巴巴地看向小区大门。当视野里出现外孙女时,她就高高地挥着自己的手。
周末,她和李娟出去散步,看到人行道上的花就笑:“长得极好,老子今晚要来偷。”看到算命摊,就在背地里大声地说:“这是骗钱的。”
那时外婆已经90多岁,糊涂的时间大过清醒的时间。
更多的时候,她在收拾行李,喊着要坐火车回家,还趁李娟上班时,偷偷拿着行李试图离开。出于无奈,李娟只好将她锁在家里,骗她说明天就带她出去。
李娟在纸上绝望地写:“我就是一个骗子,一个欲望大于能力的骗子。而被欺骗的外婆,拄着拐棍站在楼梯口等待。她脆弱不堪,她的愿望也脆弱不堪……其实我早就隐隐意识到了,唯有死亡才能令她展翅高飞。”
李娟的外婆(左一)
2008年,李娟的外婆去世了,享年96岁。葬礼上,人人都说这是喜丧。外婆的墓碑上也没有名字,他们遵照传统,只刻了五个字:李秦式之墓。
李娟提笔,自己为外婆写了篇悼文:
“秦玉珍,流浪儿,仆佣的养女,嗜赌者的妻子,十个孩子的母亲。大半生寡居。先后经历八个孩子的离世。一生没有户籍,辗转于新疆四川两地。七十多岁时被召回故乡,照顾百岁高龄的烈属养母。拾垃圾为生,并独自抚养外孙女。养母过世后,六平米廉租房被收回,她于八十五岁高龄独自回到乡间耕种生活。八十八岁跟随最小的女儿再次回到新疆。从此再也没能回到故乡。”
一棵树沉默地倒下,余下的人还要背着思念,继续往前走。
草原上从不缺少云。
云跟随着风的形状,塑造了雪的底色,影子投射在河流与树木身上,白得柔软。
去年的一场直播中,俞敏洪说,从李娟的文字中可以感觉到她面对困难的乐观。李娟却说:“我可能是一个很快乐的人,但我从来不觉得我是个乐观的人。从乐观来说,我远远不如我外婆和我妈。”
但回头看,在两代女性的影响下,又在粗砺的旷野里滚过几遭,她早已拥有现代社会中少有的豁达。
2007年,28岁的李娟回到牧场,和牧民扎克拜妈妈一家生活。次年,她从单位离职,带着全部的5000块钱南下,到江南打工、恋爱、生活。
没过多久,她回到新疆,在朋友提供的一间几平米的土坯房中,完成了《羊道》三部曲的大部分创作,记录下她在春牧场与夏牧场的全部记忆。
阿勒泰的夏牧场 李娟摄
2010年,她又一头扎进冬牧场,随着牧民一起,在地窝子里住了三个月。在《冬牧场》中,她记录下自己看到的自然的粗砺,那些缓慢流淌的生命的强韧与脆弱。
很多读者从这本书认识了李娟,评价她:“把沉重写得轻松并且显得毫不费力令人向往。”这也正是李娟的有意为之。
李娟是书中世界的创世神。她没有记录下独自在陌生环境中的无助与忐忑,也没有记录下遇到的卑劣的苦难。“现实中的丑陋很多,但那些东西不值一提。”
《冬牧场》时期的李娟
文字就是李娟所有情绪的出口。
李娟最喜欢的作品是2017年出版的《遥远的向日葵地》。这部散文集用了大面积的篇幅描写母亲,实际上,在写这本书时,李娟和母亲的关系极差。
书中看不见两人的分裂,只看到一个苍茫又勇敢的母亲,李娟说:“与其说我是在向外人展示这样的母亲,不如说我是想说服我自己,我想改变我自己,我想缓和与她的关系。”
近些年来,母亲独自待在牧区。她有一头牛,本来是别人用来抵账的,被母亲养得精贵,渐渐成了宠物。牛离不开乡下,李娟母亲就陪牛待在那里。
除此之外,母亲的生活依旧热烈。2022年,她独自开车自驾游,从阿勒泰开到海南,途中生了病,就在服务区里硬生生挨了过去。
而李娟和她的两只猫生活在乌鲁木齐。她在社交账号里间断地更新着日常,在简介里调侃自己:拖稿李天王;平时不说话一说刹不住综合症患者;直播几乎是唯一社交。
2023年,她做了一个手术。她在随笔里写,有一些朋友因为联系不到她很着急,忿而将她拉黑,于是她决定每年都失联一段时间,每年都失去一些朋友。
再之后,有网友催她写书,她假装看不见。有网友劝她保持纯真,她一笑置之,刻意保持的纯真才不是纯真。
还有人问她:如何排解一个人独处时的孤独。
李娟疑惑地回复:“为什么要排解它呢?孤独是一件很正常的东西,而且是人生中必不可少的东西,如果你不能享受它,那就忍受它吧。”
李娟近照
今年,李娟45岁了。无数人问过她的情感生活,和俞敏洪对谈时,俞敏洪也祝她找一位伴侣,李娟只哈哈一笑。
她在书中的角落里写过两次心动,一次是乡村舞会上遇见麦西拉,另一次是搭车时认识了司机林林。
她把爱情写得透彻:“我出于年轻而爱上了麦西拉,可那又能怎么样呢?我在高而辽阔的河岸上慢慢地走着,河深深地陷在河谷里……在这样美丽着的世界里,一个人的话总是令人难过的。所以我就有所渴望了,所以麦西拉就出现了。”
就像是电视剧《我的阿勒泰》中,少年巴太问李文秀:“如果我不能陪你过你喜欢的生活,你还会喜欢我吗?”李文秀坚定地回答:“我喜欢这儿,不仅是因为你,也是为我自己。”
李娟近照
哈萨克语中,人与人之间产生的感情都来自于被看见,所以“我喜欢你”的意思,就是“我清楚地看见你”。
剧中的李文秀对巴太说:“我才20岁,我都不知道,我真正喜欢的生活是什么样。”现实生活中的李娟说:“40岁以后,(我)就很明智地选择了现在的生活。”
今年5月份,李娟再次回到熟悉的草原直播。镜头里,她有着少女的灵动,岁月的痕迹在她身上几乎不见,尽管她总是自称“娟姨”,要正常地面对衰老。
直播过程中谈起她如此年轻的原因,李娟笑着回:“因为我不上班,这就是最大的和成年人的区别。”
“我是一个特例。书卖得挺好的,就不用想太多了。而且我没有太大的欲望,我没有孩子,所以我不用为家人考虑得太多。同时我也不是一个社交型人才,我也不用去维持那么大的交际网。”
云懒懒散散地飘着,李娟随意地生活着,过必要的日子,赚必要的稿费。
李娟知道,她清楚地看见了当下的自己。
部分参考资料:
1、李娟散文集《我的阿勒泰》《阿勒泰的角落》《九篇雪》《冬牧场》等
2、凤凰网对话李娟
3、《南方周末》对话李娟
4、俞敏洪对话李娟
“特别声明:以上作品内容(包括在内的视频、图片或音频)为凤凰网旗下自媒体平台“大风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videos, pictures and audi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the user of Dafeng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mere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pace serv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