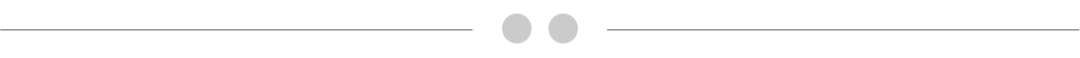“为什么一定要生男孩?”一个女导演决定把妈妈拍成电影


独家抢先看
《妈妈和七天的时间》
导演李冬梅决定将妈妈作为自己第一部电影的主角。《妈妈和七天的时间》里,李冬梅安放了对妈妈多年来的想念,几乎毫不掩饰地呈现了一位安静的母亲可能拥有怎样的一生。
这部电影成绩斐然,曾获得第四届平遥国际电影展费穆荣誉最佳影片,入围过第七十七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威尼斯日单元。李冬梅本人也因此片成为首位获得哥德堡电影节英格玛·伯格曼最佳国际影片出道作奖的中国导演。
《妈妈和七天的时间》气质独特,有人会被其间大量的留白打动,体会到掩藏在日常中汹涌的情感和无可挽回的宿命;也有人难以忍受沉默无声带来的煎熬,不知道为什么要看一家人的一日三餐,盯着一个女孩走完上学的路。
但对李冬梅来说,这些呈现是一种必须。电影里,出生和死亡交替出现,现实中,这是李冬梅的亲身经历。李冬梅是家里最大的孩子,1992年,妈妈李行玉在生第五个女儿的时候去世,时年36岁。
从此,李冬梅的人生被分成两部分,12岁之后的日子好像停滞了,她没有从迷茫和动荡走出来过。
拍电影是她为自己找到的一条与自我相处的出路,写完有关妈妈的故事,把它拍出来,李冬梅才觉得自己开始从那个断掉的点慢慢地成长、痊愈,对妈妈的思念没有停止,反而变得更深,但她能够接住了。
今年五月初,《妈妈和七天的时间》在院线上映,排片和票房并不理想。这是李冬梅预料到的事。她正在各地路演,进行映后分享。
我们跟李冬梅的对话发生在一个午后,她说拍这部电影是想要有人记住像她妈妈和外婆一样的女性,她们曾在这个世界存在过,这部电影承受了她个人生命的重量,可能飞不起来,但下一部应该可以,“我希望它飞一点”。
所有电影都有自己的命运,《妈妈和七天的时间》也是,但看过的人会记得一位普通女性如何在七天里度过一生。
以下是李冬梅的讲述。她正学着以一个最舒展的姿态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01.
如果只能拍一部电影
很长时间以来,我没有意识到12岁之后,自己的成长可能是停滞了的。我31岁才去电影学院上学,毕业的时候已经35岁了,我写了好多长篇的剧本,一直没有找到资金,也没有特别强烈的要把这些故事拍出来的愿望。
但是,突然有一天,我回看自己所有写好的、有自传性质的剧本,发现里面什么都写到了,唯独抹去了母亲去世前后的经历。这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警醒,是什么原因让我没有写这一段?追问的答案也非常明显,这是我人生里很难去面对的事。
当时我想,如果只能拍一部电影的话,我就要拍这个电影,相当于做出了一个面对妈妈的决定。开始写剧本后,我心里的第一个场景就是和妈妈在一起吃的最后一顿饭,通过那顿饭,往前推、往后推,就成了很准确的七天的结构。
我尽了最大的可能忠于自己的记忆,人物所处的境遇,包括日常生活的状态,都是非常真实的。也在影像表达上做了一些抽象化的处理,我把整个村庄作为舞台,人物是舞台上的演员,镜头拉远之后,我跟妈妈之间的关系成为更广阔图景中的一部分,这个图景包括了女性的处境,也包括90年代的乡村生活。
《妈妈和七天的时间》
我们当时大概花了三四个月的时间,全部集中精力在选角的工作上。片子里的奶奶、外婆、妈妈、小女孩都是我家乡那边的人,她们住的跟我儿时长大的村子很近,说的话也是一样的。
她们没有任何表演经验,身上却有我没办法用文字描述的特质。有一天我们骑着摩托车在路上走,看到一个老太太背着一个大背篓,里面东西特别多,她个子很矮,走路飞快,我一下子觉得那是我外婆年轻一点的样子。
包括演妈妈的演员,她本身性格是非常活泼的,很开朗,有一种天真。我自己的妈妈也有这种天真,虽然她生活在重负下。在片场,她们可能做的最大的事情就是做自己,不用演,她们已经完全和人物契合。
哪怕只讲述这七天的故事,在关于母亲的回忆上,我也有很多取舍。我妈妈是一个思虑很重的人,像电影中那样,她很少会笑,很少大声说话,大部分时候挺沉默的,但是我知道妈妈很爱我们。她对自己的女儿没有多余的表达爱意的动作,女儿穿反了衣服,会给她重新系好扣子。
我妈妈的文化程度不高,有一次我在堂屋里写作业,妈妈要给在东莞打工的爸爸写一封信,她不知道“莞”怎么写,我帮她查了这个字。我想,这个情节应该出现在这七天里,就把它放在了妹妹跟妈妈相处的时候。
《妈妈和七天的时间》不是纪录片,虽然以真实事件为原型,真实事件发生在1992年,但它真的只有在1992年才能发生吗?50年前会发生吗?过了50年呢?所以我在跟美术讨论的时候,做了一个比较坚决的决定,我们要把年代模糊掉。
这个决定意味着我们的一个态度,女性为了生儿子而失去生命不是固有时间上的特殊事件,它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在不同的时间都有可能发生。甚至这个故事不一定只是发生在农村,像我母亲一样,几代女性的沉默和隐忍,是没有时间限制的。这件事情值得被讨论,它仍然存在。
《妈妈和七天的时间》
在这部电影里,时间和人物一样重要。只有在时间的河流当中,才能体会到人世的无常。无常必须得在看似煎熬的重复和平淡的日常中才能凸显出来。其实电影减去30分钟,或者更多,照样成立,但影片中所有静水流深的铺垫,都是为了最后无常的猛烈一击。
这也是我想在电影中跟观众呈现的,用肉身来体会无常和日常的一线之隔。这七天,也是一个人一生的时光。
02.
记住
我外婆和妈妈这两代女性,她们在这个世界上,来和去都很沉默。我作为她们的后代,又学习了电影,从各方面来看,都有拍这部电影的充分理由,但我总觉得,它更像是一个自我救赎的行为。
拍摄的时候,经费不足、每天借钱不是最难的,最难的事情是,你不能再对自己撒谎了。你不能假装自己不忧伤,假装自己没有经历过这些伤痛,所以,每时每刻你都会被提醒,自己曾经在那里很无助,很惶恐。要理清几十年前的记忆,是很难的。
拍摄的过程里,我大部分时候没有哭,因为没有时间,哭也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但有一场戏是,妈妈难产后被从家里抬去医院,她在架子上露出了一双脚。看到那双脚,我哭得很厉害。
影片里很多细节都是真实的,它们刻在我的记忆里。包括外婆对女儿的情感,没有一句我爱你,但她会默默陪着女儿,给女儿弄洗脚水,在她生产前照顾她。
我外婆是一个很坚韧、很聪明的老太太,她把很多事情搞得很清楚。小时候去外婆家,如果外婆不在家,我就觉得一分钟也待不下去。但如果外公不在家,好像无所谓。
外婆个子矮,去地里收红薯藤的时候,背得多了会站不起来。她有时候会跟我们讲,邻居也会说,你外婆要跪在地上才能爬起来。外婆背红薯藤,是帮我们喂猪的。电影里省略了喂猪的情节,背红薯藤是真实的。
《妈妈和七天的时间》
妈妈去世后,我们没有聊过为什么一定要生男孩这件事。那个时候,外婆觉得这是命运,我们也会觉得这是一种宿命,反而不会去责怪重男轻女的思想。
很多年里,外婆跟着我们一起去我妈的坟上,每次都撕心裂肺地哭。然后有一天,外婆跟我说,我不想去你妈的坟上了,因为我哭累了。
这么多年来,我对妈妈的思念没有停止过,但外婆对女儿的思念是更如影随形的深刻,可能她想起妈妈的痛,远超过我。
从外婆、妈妈,到小咸(影片中的大女儿),她们中间隔了大半个世纪,命运又有很多的延续。这个故事离我太近了,我没有办法去设计她们,完全只能凭着一种本能的情感,将她们天然地呈现出来,她们天然就是那个样子,情感是很朴实的。我希望电影里的她们能活得更开阔。
小时候,我知道妈妈离开得那么早,在那么年轻的时候去世,又生了那么多孩子,是让人非常悲伤的。一直到电影拍完,这种忧伤也没有怎么缓解。我本来以为电影上映会是我跟妈妈之间某一种思念的断点,我可以按下暂停键了。
直到前几天,我发现这可能是更深思念的开始。因为你从很多人的眼里看到了妈妈,那么多人告诉你,妈妈在忍辱负重。虽然我原来也知道,但是这一次通过那么多人的眼睛,跟他们一起分享,余生我都不会忘记了。
03.
舒展地活
电影里,小咸失去妈妈后,爸爸终于从打工的地方赶回来,她说了一句话,“以后我会像儿子一样孝顺你的”。
一个12岁的小女孩,可能她从生下来没几岁就听到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还有外公外婆经常讨论,你妈妈又怀孕了,想要一个儿子。所以,她很大的一个困惑是,为什么自己不能是个儿子?如果自己是儿子,妈妈就不会受这么多苦了。
小孩子对父母的爱,会让她们想满足父母的期待。小咸用那句话安慰爸爸,也是出于内心的愧疚感,说出了一句近乎于呐喊的话,因为她没办法是一个男孩。
我跟小咸有几乎90%的重叠,很难把我们拆开来。小时候我就是这样说的,是这么想的,而且不止小时候,好多年,我都在践行对爸爸说的那句话。
前几个月,我突然发现,自己很多的不开心都源于和爸爸的关系。之前家庭强加的东西,内化到了我自己身上。后来,爸爸可能什么都没做,他没有继续强化它,而我已经开始不断地加深那种内疚感,想要满足他的期待。
后面这二三十年的时间里,这件事变成了我的功课。我得让当初的那种想法停下。
直到拍完这部电影,我才觉得自己又开始从12岁那个断掉的点慢慢成长、痊愈。我其实有很多的愤怒,很多的抱怨,很多的不甘心和很多的追问,但更多时候,都在通过自我伤害、独自承担的方式,让表面的和谐进行下去。
《妈妈和七天的时间》
爸爸对我的愤怒一无所知。前几天他还在说,你这个电影就是骗人家去看啊,你骗一次也行,反正中国有16亿人,也能骗一些人进去看了。后来他可能发现这句话挺不妥的,给我发信息说,你不要相信我说的那些话,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我曾经对他发过很大的脾气,但是,我没有办法去跟他讲刚刚跟你讲的这些话,而且他可能听了后,也不一定明白我在说什么。
我的家庭里没有纯粹的坏人,虽然想要个儿子,但爸爸没有对我们特别苛刻,爷爷奶奶也都把我们看的挺宝贝的。可能就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你的恨都不完整,没有办法彻底地去恨。
我刚刚突然想到一件很恐怖的事,哪怕有一天爸爸去世了,我可能都没有办法完完全全地从让他为我骄傲,满足他对我的期待,或者是证明我不会比一个儿子差的习惯中走出来,它实在太根深蒂固了。
所以你可以想象我们这次讲述多么重要。失去母亲的创痛能够被看见、被讲出来,而且大部分人都能理解、共情。但是作为一个女性,跟父亲的关系,以及自我身份认同这件事,是一条更漫长的路,需要我们勇敢地正视它。
如果有一些小孩子,她也是一个女儿,也有这样的困惑,如果她们在某一个时刻看到这部电影,我希望她能告诉自己:不是你的错,你不用去满足任何人的期待。我们不需要跟男性比较,比较本身就是一种自我否定。我们得非常坦然地,以一个最舒展的姿态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04.
我就是她们
我正在学着活成我本来想要成为的样子。
学电影是一件有点阴差阳错的事。小时候我的愿望是当老师,先读了师范中专,又去重庆读大学,学了四年英美文学,再之后,我回来镇上教书,第一个愿望实现了。
后来,我辞了职,跟学学前教育的二妹一起到深圳创业,开幼儿园。渐渐地有了一些收入,2009年,我挣到了人生的第一个一百万。
但我内心的动荡没有停止过,我对自己的人生非常茫然,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不知道该做什么,只是想要不停地尝试不同的事情,写作、摄影都做了一些,做生意也算一种尝试。在特别不安的情况下,我想要找到出路。
我带着全部积蓄去了澳洲学电影,从电影学院毕业后,存款所剩无几。如果人生可以重来,我觉得应该多挣一些钱,再去学电影。
《妈妈和七天的时间》
学生时期,我的电影跟现在不太一样,完全没有写实的风格,悬疑、惊悚、爱情,各种东西都拍,学校也非常支持。但是《妈妈和七天的时间》没有办法写成超现实的东西,现在这样的表达方式更加接近于我内心的感受。
拍摄《妈妈和七天的时间》也出现过波折。就像很多观众不是很理解这部电影的一些坚持,剧组的人也不太能理解,哪怕他们是电影从业者,拍过主流的电影,也拍过文艺片。文艺片是有类型的,情节性还是比较强,但这部电影几乎已经不在文艺片的范畴内了,从电影美学的认知角度,它对我的剧组成员是个挑战。
首先,我还没有作品来证明自己,学过电影也不意味着就知道怎么拍电影。他们又觉得我的剧本写的很好,总是被感动到,但这么拍,没有办法投入感情。
我平时说话做事比较温和,大部分时候可能会给人一种印象,以为我不会太坚持。事实上他们会了解到,我不是呈现出来的那样,我对艺术创作的坚持远远超过他们的想象。
在这部电影里,不需要一种表面的、精致的美,虽然每一个镜头都有它的用意,但会尽可能摒弃掉对观众的操控,交给观众足够的距离,情感上的满足和真挚的情感本身是最重要的。
第一个摄影师,他受不了我的拍摄方式,最后我们没有在这个电影里合作。后面来的摄影师在跟我沟通的时候,我也没有改变,依然在尽力解释。
总的来说,我们得信任对方。我作为导演应该要相信他们,不过在作者性很强的创作里,我们也要非常信任和支持作者性的表达,因为只有导演才真正看到了整个电影的全貌。
我不介意工作人员挑战我作为导演在片场的权威,这个挑战应该是建设性的,不是因为我是个女性,不是因为你觉得你的经验更丰富,比我懂得更多。如果以一种建设性的、合作的方式提出建议,我非常欢迎。
导演李冬梅在片场
最近,我在各地做路演和映后分享,有一场观众全部是女孩子。在那一场里,我简直呼吸都是顺畅的,全场非常和谐,不用言语,不用解释,就知道对方是支持你的,理解你的。我有一种回家了的感觉,心里很踏实。那是我路演八九天以来,印象最深的交流。
《妈妈和七天的时间》只是一个开始,过去这么多年,我才把一直困扰着自己的身份认同困境拍了出来,接下来,我会继续用自己的方式看待女性在世界上的位置和存在价值。我觉得我有这样一个义务。
以前,我的使命感和性别意识没这么强。但现在,我最大的一个接纳是,我是女性导演,电影里面可能90%是大女主,我更能够对她们的命运感同身受。因为我就是她们,我和所有的女性是在一起的。
当然我不会去限定自己,我希望自己能对得起电影这门艺术,如果有一天要做主流电影叙事的话,也要对得起花钱来买电影票的观众。更高的目标是,自己内心能够更宁静一些,变成一个开阔而包容的人。
我的新片已经差不多完成了,正在最后的后期阶段,希望明年能够上映。第三部长篇也在筹备中。后面的电影可能没有我自己的重量,应该能飞得起来。我希望它飞一点。
前不久我去剪了头发,被发型师剪得很短,本来我觉得太短了,但意外地很像我妈妈。很可惜,我没有一张妈妈的照片了,小时候照相比较少,只有一张全家福,不知道是被我爸藏起来了,还是扔掉了。那张照片是我妈妈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身份证之外唯一的留念。
现在,我的长相和发型,非常像妈妈。我正在喜欢自己的短发。
采写:汁儿
策划:看理想新媒体部
配图:受访者提供
“特别声明:以上作品内容(包括在内的视频、图片或音频)为凤凰网旗下自媒体平台“大风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videos, pictures and audi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the user of Dafeng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mere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pace serv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