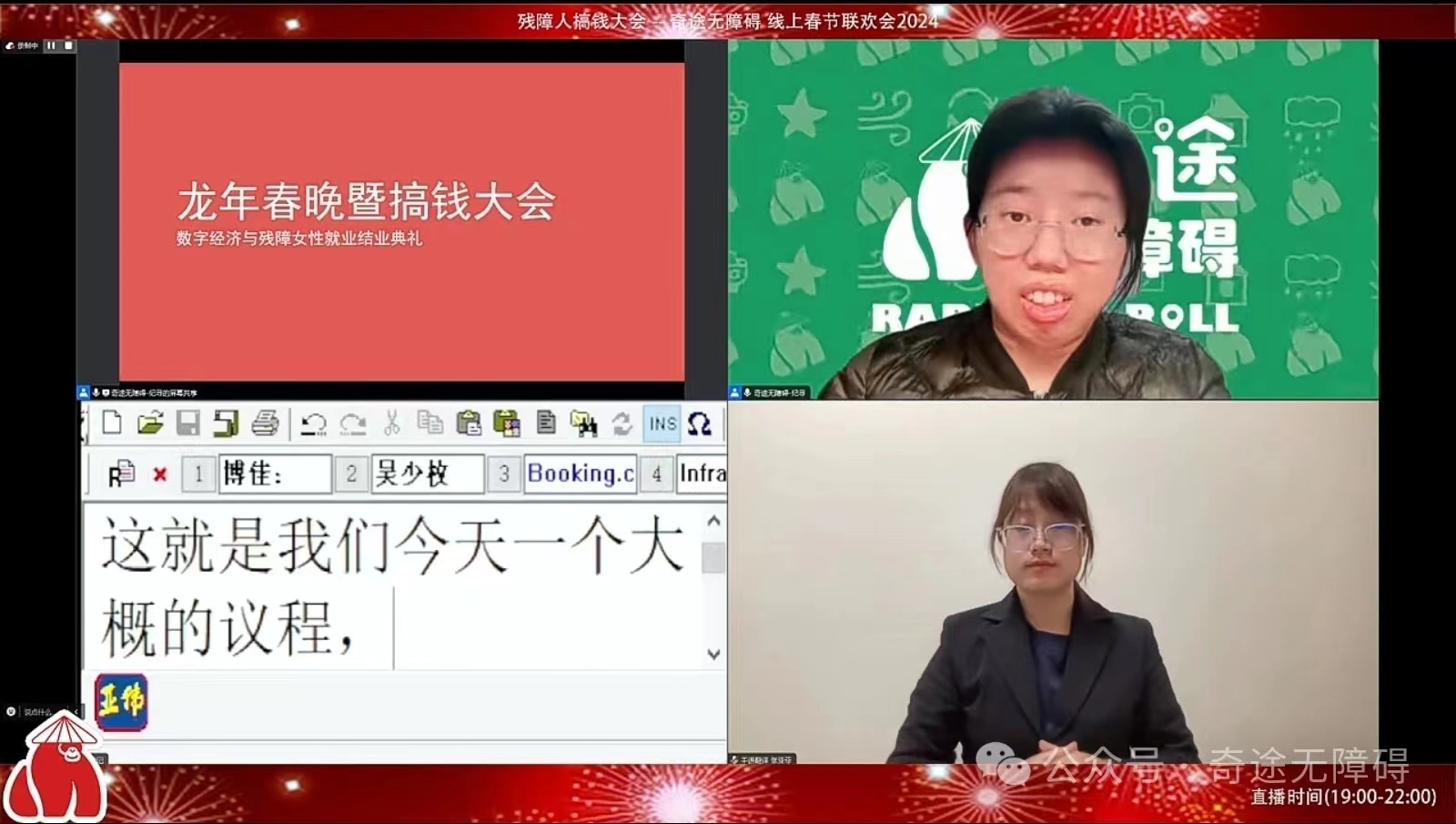“奇途无障碍”创始人纪寻:推进无障碍建设,不能只讲一个故事|全国助残日特别策划


独家抢先看
今天是全国第三十四个全国助残日,此前一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博物馆作为公益性的公共文化机构不仅承担着教育科普的功能,也反映出一个社会的包容度,帮助人们在有限的空间内探索世界、彼此相逢。
社会创新机构“奇途无障碍”的创始人纪寻是一名轮椅使用者,2023年开始,她和团队伙伴围绕“无障碍博物馆”开启了一系列测评和访谈。过程中,博物馆作为一个需要跨越重重障碍抵达的终点,带给了纪寻许多复杂的感受,也让她看到,对于很多残障人而言,在走进博物馆之前,走出家门尚且是一件难事。
“走不进去,走不出来”是纪寻对残障人群生存状态的观察,她形容这是一个恶性循环——走不出去就没办法找到好工作,没有好工作就更难走出去。长此以往,残障人群的社会地位不提升,他们的声音就无法被真正听到。
虽然2023年《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颁布实施,让无障碍议题开始被更多人关注,但纪寻对它能带来的改变目前持观望态度:“如果不切入真实具体的需求,无障碍建设是不可持续的,一阵风后就没了。”
以下是纪寻的讲述:
从世界的角落出发
我叫纪寻,是一名“腓骨肌萎缩症”罕见病患者,目前靠轮椅出行。因为父母是流动单位修大桥的,小时候我都是跟着父母全国各地流浪,去各种各样的建筑工地,七岁的时候搬到了南京,到现在将近30年。
在南京,我做了一家社会创新机构,叫“奇途无障碍”(以下简称“奇途”)。在此之前,我在美国、法国生活了六年时间,那期间在世界各地旅行,去了很多博物馆。
在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国家肖像博物馆,我看到了令我难以忘怀的展。它讲述了从19世纪开始到今天女性地位变化、争取权利的历史。残障群体和女性一样,都需要从被压迫的角色,寻求权利的觉醒。看的过程中我泪流满面。
在这个博物馆,我还看到一张照片。那是肯尼迪家族成员和两个“特奥会”运动员的合影,被打印成巨幅照片挂在展厅里。在那张照片里,我看到一条路:残障群体可以从底端走向顶层,被更多人看到,甚至影响国家的顶层决策。
这次经历对我的工作产生了非常大的动力,我开始想:我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以后要向哪去。
我很喜欢日本画家奈家奈良美智,他的经历教会我一件事——“人的成长是一条曲线,好运是积累的过程”。2014年,我才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毕业一年多,因为想看看世界各地的不同文化,加上正好拿到了去巴黎政治学院的奖学金,我开启了欧洲之旅,从那时起萌生了对无障碍旅游的兴趣。
纪寻与妈妈在撒哈拉沙漠里
每一次出门,我都要做很多研究:当地的无障碍怎么样?有哪些政策、哪些服务?交通出行是否方便?虽然国外有很多网站分享这类信息,但是国内在这块是很缺乏的。我当时就想做这样的事,分享旅行信息给中国的残障人。
经过一年半不间断的旅游、前后三年的项目准备,2018 年,我成为Booking.com(缤客网站)遴选出来的可持续旅游的创建者。他们在全球选了五个人,我是唯一的中国人。
也是那一年,我回国创业,通过“一席”那次演讲很多人了解到了无障碍旅游这件事。如果你在互联网上搜索无障碍旅游,很多词条搜索出来都是“奇途”做过的事,这让我们很自豪。
为什么是“无障碍博物馆”?
2023年初,我们发起了“无障碍博物馆残障社区连接计划”,希望以残障社群的视角带领大家做博物馆及所在城市的无障碍测评。我们想干的事很多,最后落脚在了“无障碍博物馆测评指南”。
这个项目入选了知乎的“灯塔计划”,我们是唯一一个以残障创作者为主的创作团队。截至目前,我们走访全国三十多家博物馆,采访了十五位和无障碍相关的专业人士。
说到让我印象深刻的博物馆,国家博物馆(下文简称“国博”)首当其冲。它汇集了各省最优秀的文博展品,你可以在这里看到上下五千年。但必须要说,如果残障伙伴乘坐公共交通前往国博,也是真的很不方便。
我们当时选择的是地铁。高德地图上显示只要三十分钟车程、总共五站路,但因为我使用轮椅得坐“爬升梯”上下,一趟就要10-30分钟,加上好多换乘,需要不停等待。后来我们忍无可忍找地铁工作人员“作弊”,直接把轮椅架到扶梯上。即便这样,我们还是花了两个小时才抵达国博。好不容易抢到票,半天已经过去了。
还有一次是在陕西历史博物馆(以下简称“陕历博”)。刚去的时候我们很沮丧,因为它实在太火根本预约不上。但我们已经定了要去拍这个博物馆,看着眼前的人山人海,我很害怕任务完成不了,就去窗口问:有没有给残障人的绿色通道?结果对方告诉我,残障人士本来就不用预约,陪同人员也不需要。只是这个信息要去线下窗口才能得到。
当时我像中了五百万彩票,感觉自己成了“VIP”。但进去以后发现,里面就像沙丁鱼罐头,参观的人走出了泰山行军的感觉,真是一步步往前挪。
我心里“咯噔”一下,虽然我进来了,但因为坐在轮椅上视野受限,几乎啥也看不到。我需要在后面喊“能不能让我看一下”?但那会大夏天人很多也很吵,根本没人注意。但后来也有好几次有人看到我们,主动把位置让了出来,那一刻还是很感动的。
我们一直在说,博物馆的无障碍并不仅局限于博物馆内部,而是从出发到到达都构成了无障碍体验的一环。
像广州、深圳的无障碍设施就蛮不错的,无论是地铁、还是无障碍出租车。可能是因为运营成本比较高,无障碍出租车在中国的普及率一直不高,但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它的存在非常重要。广州给每单无障碍出租车五十元的补贴,而在北京,你打一个无障碍出租车起步价就是98块钱,这对很多人,尤其是收入较低的残障群体来说,简直是天价。好像因为残障,你还受到了经济惩罚。
每个城市都有做的好和不足的地方。这里面还包含“无障碍衔接”的问题,对于残障群体而言,无障碍建设就像一个网格,一个点一个点衔接上了你才能最终抵达目的地。
我们做“无障碍博物馆”的项目后,会收集反馈,发现大家真正的问题更多在于:我如何能从我的家走出去。
在这背后,一个是有的伙伴独立能力没那么好,还有的缺少家庭和社会支持,心理上有坎,包括还有的居住在没电梯的老旧小区,这就直接让很多人门都出不去。
再比如说,我们社群里有人告诉我们,他们家没有电梯,出去需要雇人把轮椅搬上搬下。这种一般按次付费,一次二十块钱,体重更重的可能要五十。他就会觉得,我出门一趟还啥都没干,就要花五十,加上各种交通问题,如果附近没地铁站,公交车也不好坐,打车成本更高,还要找人陪同……出个门一套下来,要花那么多钱?他就会说,那我不出去了。我记得当时向知乎提交第一版的作品,他们看完之后反馈说:不是出去玩吗,为什么你们看起来这么沮丧?其实就是那天坐地铁的路上耗的时间太长太长了。
纪寻(前排左二)和她的伙伴们
后来我也在想,“无障碍博物馆”作为一个媒体项目,一方面要面向公众展示实际遇到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承担了责任,让残障伙伴建立出行的信心。告诉他们,即便你会遇到很多挑战,你也是可以出行的。如果去国家博物馆是你的梦想,我就用我的经历告诉你,它可以实现。
所以后来我们做这件事的价值导向变成:我会提前向你预告,你的路上会有哪些难点,但你可以把它当作闯关的过程,最终去到你想去的地方。
当时我给国博写的推荐语就是,“这是每个中国人都要来的地方。看看我们国家最伟大的文物吧,即便前路有再多困难,它都值得。”
如果要总结,我们为什么选择了博物馆,有这样几个原因吧:一是因为博物馆有文化传承的意义,二是它是带有社交属性的场所,链接的人的素质和包容度相对较高;另外就是,博物馆承担了公共教育的职能。
陕历博的地上有一个巨大的无障碍通道的标识,它给人一种特别“直面”的感受,每个人都会注意到。当时我们在“一张图故事”里写道:当这样一个标识出现在博物馆,被小朋友们看见的时候,他们可能从小就会意识到:一个场馆里有残障人和无障碍设施,是再稀松平常不过的事。
“走不出去,走不进来”
“奇途”是做无障碍旅游的,但是受新冠疫情影响,有三年我非常迷茫,不知道自己要干嘛。但因为那会我们已经把社群建立起来了,他们会一直推着你前进,让你要做些什么。
闲着也是闲着,我们就做了很多线上活动,开始以社交娱乐为主,慢慢地也发掘了残障群体更多的真实需求。
我一直说,就业才是真正让残障人走进社会,为自己赋能的方式。现在互联网带给了所有人包括残障群体前所未有的机遇,但大家也会疑惑,我天天对着电脑工作,我算融入社会吗?因为这个社会里除了我没有别人。这里就有一个怪圈:你走不出去,你就走不进来。你得先找到你生存所需要的资源才能获得机会、获得收入、才能去更远的地方。但现在是一个恶性循环,因为你走不出去,就没有收入,越走不出去就越走不进来。
在社群里,我们有一个叫“拍拍乐”的活动,让残障伙伴面向社群讲述他的故事。现在“storytelling”有点负面的含义,大家会联想到“忽悠投资人”。但在残障伙伴这里,讲故事首先是让他面对相对安全的环境,开始勇敢地表达。
虽然都是一些普通的残障人的故事,没有那么多值得歌颂的点,但残障人的生活本来就是一种成就。而且当一个故事被讲述、记录,也会有演讲的机会找到当事人,帮助他链接一些社会资源。
更重要的部分是,在平台上做了分享之后,会有残障伙伴真的觉得“自己被看到了”。在我们的小红书上,会有人看到帖子问“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我们就会把作者拉过去回答,一来一往,他们就成了朋友,就延展了那个残障伙伴的生活空间。
奇途无障碍 2024线上春节联欢会
为什么我们的社群粘度高?因为我们在提出具体的问题,大家在这里不停地能量交换,不断成长。观察他们在社群里的讨论,有时候作为运营者我都会对一些问题产生好奇。比如说,“不露脸,能不能赚到钱?”“电动轮椅电池能不能托运?”我们社群里的讨论非常直接,大家不想听虚无缥缈的大道理。有些伙伴羞于启齿的,“奇途”可以帮他们链接回答问题的人。尤其现在我们链接的社群人数在一万两三千人左右,数字很庞大,大家常常会遇到相似的问题,积累一些解决办法,长期下来,我们就有了自己的数据库。去年,《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开始实施,很多人开始围绕“无障碍”讲故事。但整体而言,我对它短期内能带来的改变没有那么乐观。因为“无障碍”距离普通人的真实需求仍然有很大差距,大家没有耐心去研究它:这些人到底需要什么?
我会遇到很多奇怪的事。掌握话语权的专家可能都不认识一个残障人。像是因为国家战略层面要做“无障碍”,于是一群不懂的人在一起商量,把真正的无障碍需求者纳入他们的讨论范畴,但最终又还是以甲方的意见为主导,本末倒置了。如果没办法切入到真实具体的需求,无障碍建设也是不可持续的。可能一阵风后就没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残障群体作为无障碍设施的使用者,也应该树立起这样的意识——这是和我们有关的事务,我们应该更积极地发声,争取应有的权利。
这也对残障伙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曾经面向600 多位有无障碍需求的旅行者做调查,相当一部分的残障伙伴自己都不知道“无障碍”是什么、他有什么无障碍需求。很多人的思维方式甚至是“人定胜天”:只要我足够强大,就能和正常人一样。
在这个意义上,对残障群体的无障碍教育还有很多路要走。这是个很复杂的议题,需要更多元的利益相关方参与,“奇途”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中介。如何让残障群体的社会地位能够真正提高,最终仰赖的还是这个群体本身的壮大。
对于这一点,“奇途”能做的首先是在残障就业这块做更多亲身实践,既然我们已经链接了很多成功的就业经验,那我们能不能孵化一些小的创业项目,和伙伴们一起成长、赚钱。还有就是,我们能否让“无障碍”成为一个抓手,让残障伙伴的视角也成为资源,加入到无障碍建设中,组织大家积极地参与社会活动、真正让他们走出去。
作者|李迅琦 编辑|佘韵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