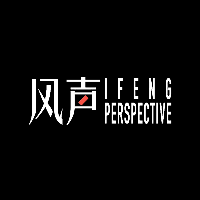风声|全网热议的爽片《周处除三害》:死刑是大开杀戒后的救赎?


独家抢先看
作者|陈碧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如电影海报所言,“干一票大的”,《周处除三害》确实干了票大的。它与众不同的犯罪叙事、拳拳见血的暴力、对肉体痛苦的极致渲染、对精神控制的妖魔刻画,再加上充斥全片的对人性淡漠、失望乃至厌恶的情绪,无一不酝酿着汹涌的暗黑能量,以暴制暴几乎贯穿始终。你可以说它是一部爽片,因为人们喜欢私刑复仇,喜欢“侠客行”,“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人们也喜欢浪子回头,喜欢《世说新语》里的恶人周处最后改邪归正,就像电影里的陈桂林杀死了比他更坏的恶人,他的生命似乎有了价值。
但它绝不止于一部爽片。电影的结尾,罕见地呈现了一场死刑的执行。他对骗他的医生说:“幸好我上了你的当。”刮胡子的时候,他的睫毛在颤抖,眼泪无声地流淌。当他望向镜子的时候,那是一张对生命无限眷恋的脸。开枪之前,他对着镜头,也就是对着打破了第四堵墙的观众们真诚地一笑,然后闭上了眼睛。
也许这才是那“一票大的”。人性的最无奈也最光辉之处,就是永远存在可能,善行之下,也许有败坏;恶念之后,也许有醒悟。即便是犯下死罪,诸如谋杀、强奸的人,他们依然可能拥有譬如勇敢、慷慨、助人的品德。在审判到来之前,他们如何获得救赎?如何在善恶的交锋里审视自我,真正理解自己的行为?
罪与罚,才是这个故事的谜底,也是人类永恒的主题。
死刑故事的两面性
陈桂林的死刑判决书,可能是这样的:
被告人陈桂林,身份证号A125783729,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持手榴弹行凶抢劫并致一人死亡,后又持枪致一人死亡,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负案潜逃期间,绑架幼童,其行为构成绑架罪;后持枪行凶,致“香港仔”等四人死亡,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此后,又至澎湖灵修中心行凶,持枪致灵修尊者“牛头”及无辜信众二十余人死亡,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被告人罪行极其严重、犯罪手段残忍、犯罪后果严重,主观恶性极大,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应当依法判处其死刑,立即执行。
看完这样的判决书,陈桂林可谓血债累累,这样的死刑犯死了就死了,不会有任何价值。但故事还有另一面——一个杀人犯的救赎之路。
他是一个想要扬名立万的黑道少年,因仇杀跑路。潜逃四年,奶奶去世。此时,他得知自己身患“绝症”,又看到自己只排在通缉榜第三位,决定要在临死前“干票大的”,好让所有人记住自己。这是个幼稚的决定,但他格外认真,甚至绑架了救命医生的儿子,以换取两大恶人的行踪消息。结果在除恶路上,他的心态慢慢发生了变化。
他杀掉香港仔,救下了小美,还给了小美自由。在澎湖的灵修中心,他杀掉了邪教尊者并让愿意离开的离开。剩下的人,他认为完全不值得拯救,就抬抬手几乎是用一种冷漠到轻蔑的态度在开枪,信众像动物一般死去。最后,他选择去投案自首,领受死刑。
从开始杀人到最后决定赎罪,他的眼神一直在变化,从一开始的无知中二到潜逃追凶期间的痛苦、惊惶、恐惧、残忍甚至冷漠,再到片尾的温暖、清澈、留恋,他在真诚地赎罪,真诚地在行刑前说那句:“我对不起大家。”
判决书上是看不到这些的,只有在电影故事里,我们能看到人性的觉醒,以及自我裁决的重要。善与恶、对与错,乃至被害人和凶手的身份都并非一成不变,而且往往能够并存。
陈桂林是不是一个恶人?是的,他杀人不眨眼。但他为什么要惩恶扬善?为什么要搭救一朵行将枯萎的小花——程小美呢?又为什么要在灵修中心站出来揭穿真相,告诉那个绝望的妈妈“你快走啊,你带着孩子走啊”?
如果答案仅仅止于“人之将死,其行也善”的话,就没法理解人性本身的复杂和汹涌。总是在这种时候,让你相信那句话:人性向善。在所有人的内心深处,都埋藏着善的种子;甚至在每一个恶人身上,都捆绑着一个想要挣扎出来的好人。
这是一个救赎故事,也是一个死刑犯的故事。在报应思想看来,死刑判决是恰当的。但从犯罪预防上说,被告人产生了赎罪意识,并承诺坚持更为重要。“罚”并非强加而是内在产生,才能真正起到对“罪”的预防效果。换句话说,人性的恶,仅仅依赖于刑法制裁是不够的,更需要灵魂救赎。
如果罪犯只是口头认罪换取从宽,内心不悔罪,他要么觉得自己只是运气不好,要么觉得自己还可以“干票大的”,那么潜在的社会风险没有消除。所以,除了法律意义上的惩罚之外,更应去追求心灵上的救赎。
这种救赎,源于杀人者首先要认识到自己是有罪的,然后才可能去忏悔,并承诺用余生去赎罪。这也正是主张犯罪预防的功利主义者不支持死刑的原因,因为死刑,恰恰剥夺了他人赎罪的权利。 这一点,我们将在后文谈到。
该如何看待私刑与死刑?
影片探讨了私刑与死刑。镜头语言几乎直给了这么个结论:私刑是野蛮的,死刑是文明的。全片大部分暴力镜头都呈现了以暴制暴的行刑式枪决场面,尤其有的暴力还冠以“除恶”的名义。
唯一文明的处决方式出现在片尾——死刑的执行:“请核对身份。”“请问你还有什么遗言吗?”“请问需要麻醉吗?”如果说冲击力的话,死刑执行的冲击力丝毫不逊于除恶过程中人和人之间的斗狠好勇。
当法律在处决陈桂林剥夺他生命的时候,是把他当做人;而最关键之处在于,此刻他也获得了救赎,回归了人性。但是,那些私刑场面,爽的感觉也许来自我们的野蛮一面,人不再是人,而是一个个无足轻重、可以被轻轻抹去的符号。
没有人愿意被当成肉类一样处置,或者只是增添的数字“又杀了一个”——就像电影里灵修堂屠杀所呈现的那样,血淋淋的,轻飘飘的。私刑带来快感,但这快感就像服毒一样,最后侵蚀的是行刑者的灵魂。
换句话说,执行私刑,即便以正义的名义,即便你认为这些人不值得拯救,你就有权处置他人的生命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回答是“你没有”,没有人有权擅自处置他人生命。因此,这就是罪,不论以什么名义剥夺他人生命。在文明的社会里,唯有死刑具有正当性。因此,电影在片尾实现了反转,以文明的方式行刑。
死刑的第一正当性来源于报应思想,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以陈桂林为例,他为什么该受领死刑?因为报应。我们从小就听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劝善教育,在日常生活中却经常落空,不得不用“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来安慰自己。
报应思想的最佳实践场所在哪里呢?在刑法里,尤其是在死刑判决里。这种思想至少可以追溯到同态复仇: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命抵命。所以,死刑本身确实能够体现复仇的快感,也被犯罪学者比喻为现代人集体杀戮欲的体现。
死刑的第二正当性来源于功利主义。
在这种思想下,死刑作为一种不得已的恶,除非能够证明施加这种恶的结果可能会好于不施加的结果,否则就不能被认为是合理的。因此,当我们说“做错事是要付出代价的”,功利主义算账是算未来的账。
具体到某一个人身上,比如陈桂林,在报应论看来,他的死刑恰如其分,因为他过去做的事需要负责;在预防论看来,也许死缓加限制减刑也足以起到预防犯罪的效果,因为他活着也丧失了继续犯罪的可能,同时他服刑本身以及他的真心悔罪也是对潜在犯罪的一种震慑。
换句话说,惩罚不该剥夺人们改过自新的机会,只需要改变犯罪者未来的行为模式就足够了。
那么,执行死刑是正当的吗?我们在实际生活中,面对不同的死刑案件,经常会按照自己的偏好选择报应论或者预防论。实际上,没有一种理论能够完美地解释死刑的正当性,每种解释都有遗憾和缺失。
尤其在行为主义兴起之后,我们一方面强调人有意志自由——“路怎么走,你自己选”,一方面又发现个人的选择可能并不是完全自由的,至少有一些是由家庭和社会的影响决定的,我们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全部的责任。这种矛盾动摇了死刑的正当性,也令法庭无法保持一贯的冷峻。
在这里,我并不是说暴力犯罪或者陈桂林这样的人应当被原谅,而是说,需要在一个人性化的框架内作出死刑的判决。否则,我们杀掉他,跟他杀掉那些弱鸡一样,又有什么区别呢?
回到电影《周处除三害》,我们讨论罪与罚,讨论救赎,其实就是要回答社会应如何对待那些有罪的人?这正是司法伦理的核心内容。
一个社会对自己的公民使用暴力的时候,背后有什么样的道德考虑,这些道德上的考虑是否充分合理,体现了文明的程度。
救赎之路:去爱,去相信
看《周处除三害》的时候,联想到最近被执行死刑的几个死刑犯。有人说如释重负,有人说大快人心,也有人说五味杂陈。因此,电影对于犯罪和死刑的刻画恰逢其时,让我们对于“罪与罚”的话题有了更明确的指向。
在电影里,我们觉得应该对人性的良善抱有期望。但回到手上的凶杀案卷,比如吴谢宇或者劳荣枝,又会隔空冷笑:农夫同情蛇,谁来同情农夫呢?
一个都不能原谅?!亦或是我们没有资格原谅?那么做错事的人或者那些手上沾满鲜血的罪人,他们应当如何获得救赎呢?他们该像谁求得原谅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罪与罚》是从一起杀人行凶开始的,以救赎和复活结束。小说里每个人的内心都有深渊,人人都在艰难抉择,在善恶之间备受煎熬。黑暗中,唯有爱是一切的救赎。
《周处除三害》也有同样的设定,柔弱的程小美就是陈桂林最后的救赎,他杀死香港仔之后,冒险回来救下小美。当他听到小美妈妈的一生就是从一个男人的奴隶变成另一个男人的奴隶之后,把车留给了小美,“你现在自由了”。而他们用刮胡子相识,又用刮胡子告别;这个世界还有爱他的人,他的人性部分就复活了。也只能因为这种心态的变化,他才能真诚悔罪,诚实地面对惩罚。
这种美好和转变可能会因为太单薄而被嘲笑,就像大家也嘲笑美剧《冰血暴》第五季的结尾。多萝西对食罪者说:“他们让我们吞下这些罪恶,好像这是我们的错。但你想知道治疗方法吗?”她说,“你必须吃一些充满喜悦和爱的东西,”她举起一块饼干,“然后被原谅。”它的主题同样是,只有爱能够救赎一切罪恶。
而在我们愤世嫉俗的话语里,这种升华被视为圣母心,爱既虚弱又无力,能够拯救什么?
人性固然软弱,又经不起诱惑,但即便有成千上万次黑暗法则的灵验,只要有一次人性的超越,只要有一次人性的光辉,那就足以发出耀眼的光芒,人就值得被拯救。 所以,罗新老师评点说,人性有超越的一面,因而也就有足够的潜力。所以,我们还是应该去相信啊。
虽然《周处除三害》是一部充斥着暴力、伤害和死亡的电影,但把它们升华为文明和价值的,赋予它们意义的,是故事的另一面。
看电影的时候,也许你发现自己对于死亡是漠视的,对于暴力是天然亲近的,你是在故事里享受着杀戮快感的,确实如此,因为万物都注定趋于混乱的熵增。但是,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具有抵抗自身熵增的能力。去爱,去相信,这就是本片给人希望的地方。
“法治理想国"由中国政法大学教师陈碧、赵宏、李红勃、罗翔共同发起,系凤凰网评论部特约原创栏目。
主编|萧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