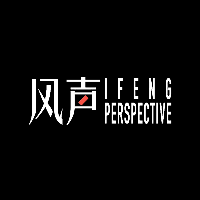风声|中国要在AI赛道追上美国,先要允许企业赚到钱


独家抢先看
作者|罗布
IT行业从业者、观察者
自2022年底ChatGPT横空出世以来,中国展现了十分急切的追赶速度,目前已累计推出了超百款大模型——号称“百模大战”、百舸争流。业内观察者普遍认为,中美大模型的差距在一到两年之间,马斯克稍早前接受采访时也表示,双方差距在12个月左右。也因此,尽管资本市场表现不佳,但AI相关概念股却总体保持飘红。
随着春节期间Sora文本生成视频技术横空出世,越来越多人开始担忧,中美AI技术差距比想象中大,且未来还有被进一步拉大的危险。
讨论AI竞争,显然不能就技术论技术,中美AI技术发展喧闹的背后,实际深受各自经济社会及国际政治环境的影响。
企业要先赚到钱,才能大胆搞研发
近年来,在讨论科技创新时,国家政策愈发强调“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
从当前经济整体面临的压力,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自身发展的挑战困境来看,如何恢复和提振市场信心、如何让企业挣到钱,实际上是前沿数字科技创新的先决条件。否则创新对于业界而言,很可能成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和“劣币驱逐良币”的PPT圈钱浮云。
以评判企业创新投入的重要指标“研发强度”来说——其概念是“研发经费占营收的比重”。
在中国,要申报“高新技术企业”,研发强度需不低于5个点。若以全球市值最高的苹果公司为例,近年其研发强度也并非特别突出,大约也就5个点;风生水起的特斯拉,研发强度甚至连4个点都不到。马斯克还就此嘲笑苹果,说“苹果研发花的钱不值”。
而按照中国标准,特斯拉都戴不上“高新技术企业”的帽子,苹果也只能勉强保住。
“研发强度”概念并不是不对,但我们不能只看“研发强度”这一比例数值,还要看研发金额的绝对数值。
国内顶尖科技企业中,腾讯、阿里的研发强度大约在8个点,华为甚至超过15个点,研发强度比苹果、特斯拉高出数倍。而从“绝对数值”看,作为中国科技创新的领头羊,这三巨头的研发投入金额之和,占到了全国总研发金额(包括所有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等)的7%。
不过,如果把这个研发金额的绝对数值,和美国头部企业一比,就相形见绌了。原因很简单,苹果挣的钱,比中国企业多太多。它那么大的营收和利润基数,拿出一点点比例的钱,都是巨大的财富,可以对科研做出极大的助力。
而如果我们更直观地去看企业利润,会发现中国企业和美国差距明显,中国的科技企业远没有美国的竞争对手们“那么大、那么强”。
2023年《财富》排行榜,最赚钱的20家中国公司中,有8家银行、1家白酒、3家石油、1家电信、1家电力、1家综合物流、1家保险。上述16家企业里,有15.5家是央企,这16家里面没有一家是我们直觉理解意义上的“科技企业”。
20家的榜单中,还有2家在台湾——台积电和长荣海运。只有剩下2家,是大陆的科技民营企业——腾讯和阿里,分别位列利润榜第6和第15名,其利润也分别只有工行的一半和1/5。
而如果看美国最赚钱的20家公司,苹果、微软、谷歌分列前三,脸书第9,此外是4家石油、4家金融、3家医药、2家日化、1家汽车、1家零售,苹果的利润大约是工行2倍。无论是从企业整体类别分布结构讲,还是从数字科技企业的盈利能力讲,美国都更具竞争力。而利润竞争力的背后,所蕴含的就是投资、建设、创新的底气。
OpenAI的创始人兼CEO山姆·奥特曼在回忆公司发展历程时,谈到当时急需资金。于是他最初找到美国政府——在他看来,拥有“曼哈顿计划”(原子弹)和“阿波罗计划”(登月)历史的美国政府是最佳选择。但当他吃了闭门羹后开始相信,“市场才会一直起作用”。最终结果是,微软投了10亿美元。
创新是个风险极大、收益极不明确、回报极不确定的事情。财大气粗才能掷地有声,才有可能砸出来前沿的结果。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从这个角度说,我们需要支持鼓励中国的科技大企业进一步做大做强,而不是过度规制它。企业本身发展好、营收好、利润好、预期好、前景好,才有底气、有信心拿出更充足经费去做科研探索,去在全球市场上参与国际竞争。
科技创新,亟待一场思想解放
近日,湖南省委提出要做“解放思想”的大讨论。对于科技创新,其实也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第一,是要解放人才,为疯狂的人提供生存和发展空间。 这次大放异彩的Sora团队中,两位负责人都是2023年刚刚博士毕业,甚至也有00后的参与者。OpenAI的创始人兼CEO山姆·奥特曼曾说,“你试图让这群稍微格格不入的乌合之众去做一些疯狂的事情。”其实他本人就是传统观念中“格格不入”、“疯狂”的人。
作为创业者,山姆·奥特曼显然受益于美国自由开放环境,他同硅谷其他很多“神话”类似,从顶级名校斯坦福辍学。作为公开的同性恋者,他在去年刚刚与男友完婚。
作为投资者,他豪掷超5亿美元支持从事可控核聚变研究的初创公司Helion,和旨在以血浆再生、细胞编程为路线推动长寿的生物公司Retro Biosciences,这两家公司的不少研究路径,在大多数人看来都是“离经叛道”、“天马行空”。
此外,作为社会关心者,他还创建了“世界币”——一套兼顾加密货币和生物识别系统的玩意儿;还花数千万美元开展持续多年的对美国全民基本收入的社会研究。甚至,作为政治观察者,他因为对特朗普执政感到不满,而一度考虑竞选加州州长。
若在中国的环境下,奥特曼或许会被戴上很多帽子——“辍学”、“异类”、“变态”、“搞虚拟货币”、“资本干预社科研究”……当这些帽子盖在某个天赋异禀的人身上时,很可能就会使他变得平庸。
美国足够包容开放的社会环境,培养了足够多奥特曼这样的人才。这种文化因素与人才培养间的关系在告诉我们,对于顶尖人才,可能并不适宜去做太多条框化的“引领”,而是更简单、天然地让其自由成长,给予其宽容,这对前沿领域探索尤为重要。
二是,要解放企业,支持他们轻装上阵、大胆探索。 中美科技博弈,以大模型为代表的AI前沿科技发展,突破的希望更多在科技企业而非高校院所,这一点已在国内业界得到广泛认可。此类前沿探索,兼顾理论,但更重在应用,只有依托业界充足的财力资源和行业一线观察感知,才可能在大量算力和海量数据的基础上,涌现出更顶尖的AI大模型成果。
美国的情况就是这样,DeepMind、OpenAI及其背后的谷歌、微软,一方面依赖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这样的顶尖大学,但就应用发展本身来说,又必须面向消费市场。作为一条创新铁律,中国也必须如此,未来假如中国AI有质的突破,大概率不在高校与科研院所,而在科技企业。
当前,一个不乐观的形势是,从投资环境讲,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总金额在逐年稳步上升,中国则出现下降态势。
据公开数据显示,2023年上半年,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共计发生融资1387件,筹集融资金额255亿美元。其中中国国内人工智能领域仅161件,总金额61.74亿元(折合不足9亿美元)。中国的融资件数相较去年同期下降49%,金额则同比下降62%。
这也是当前中国投融资整体趋弱的一个缩影——在大环境下,不少企业不能投、不敢投,即便在最火爆的AI领域也不例外。如何面向企业给出更切实的“定心丸”,提振企业投融资信心,将之从过去一段时间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寒蝉效应中解放出来,也十分重要。
自GPT问世以来,相当多中国AI领域专家都表示,应用是中国的优势。中国科学院信息工程研究所高级工程师韩冀中指出,“包括微信也好,抖音也好,实际上它们都是由于应用领先,然后再在技术上实现反超的。”
复旦大学教授肖仰华也多次表示,“中国可以用应用发展来带动模型进步,走‘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但与此同时,技术前沿的未知性、应用的不确定性,甚至数据本身的敏感性等,使得内容安全等因素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悬在各家企业头顶,多多少少使得大家心存芥蒂。
创新往往是会犯错的,不可能有不犯错误的创新。如何激活数字科技企业,让他们少一些忌惮、多一些踏实,更大胆去投资、去探索,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AI发展,需要一个“富人朋友圈”
当前AI发展,乐观一点说,中美同属于第一阵营。但如果看第二阵营的名单,就会发现,那些国家也是美国阵营里的。从AI应用来看,美国的企业借助自身国家的政治影响力或者所谓的“盟友力”,叠加英语天然的国际优势,能获得更多的有效国际市场份额,进而使其更好推进AI技术的应用和发展。
(英国传媒机构Tortoise Media发布的2023年全球AI指数排名)
之所以用“有效国际市场份额”这个概念,是因为数字科技行业和卖服装、玩具还不一样。对于传统、相对低端的制造业,拓展海外市场意味着赚取外汇。由于技术门槛相对低,更多是劳工熟练程度、企业成本管理等方面的考验。罗马尼亚人、尼日利亚人、澳大利亚人——谁买义乌的玩具,对义乌玩具制造而言,没有本质上特别显著的“反向影响”差异。
但AI技术的应用,本身就有相对较高的门槛。作为资金密集、知识密集型的新兴产业,其对算力、设备等有一定需求,客观上难免有“嫌贫爱富”的特征。
这好比两个不同的大家庭——一个大家庭里,多个小家庭都生活富裕,往来间经常能互通有无,相互帮衬。与之对应的是,除美国以外,还有加拿大、英国、日本、韩国、荷兰等等,在从半导体硬件到人工智能软件领域,美国及其盟国间既有丰富的人才和技术储备,也有完善通畅的科技交流合作与协调机制。
而另一个大家庭里,只有一个或少数小家庭还发展不错,但其他小家庭则相对能力欠缺、发展不足时,往往要么是单向帮扶,要么是鲜有往来,而难以形成有效的“互助网络”。
举个或许不恰当的例子,中国和巴基斯坦、塞尔维亚、朝鲜这些国家,即便在工业、农业、能源、资源等领域合作空间广泛,也很难在数字科技这个特定方向上,让这些国家和中国“教学相长”。和这些国家开展数字合作,它们对技术和应用的诉求,很难从合作中反哺自身,实现创新迭代。
目前,我们面临的一个几乎已成既定事实的困境是,并非中国不想和加拿大、英国、日本、韩国进行技术合作。即便对于美国,我们也强调反对“小院高墙”、“脱钩断链”。但上述国家的“中国安全威胁论”已逐渐根深蒂固,使得中国企业在拓展这些国际市场变得难上加难。而对于“一带一路”沿线不少国家,即便我们确信这是未来中国经贸往来的重要对象,也必须正视其对最前沿科技研发和应用的能力和意愿都相对有限的事实。
这也是为什么有不少技术专家认为,未来可能形成“中美分别领导的完全独立的AI发展体系”。这种前景里,一方面中国需要自力更生、自立自强,这本身是值得骄傲的。但另一方面,作为大国博弈、中西之争中,如何避免技术落后,是必须要思考与应对的。
这同冷战时期,中国自主实现核武器研发还有很大不同。原因是,一旦拥有核武器,就理论上获得了“相互确保摧毁”的安全保障——原子弹摆在那里,就是威慑;核弹头能持续生产与维护,哪怕存在代际技术差异,也并不在根本上影响国家安全。但AI不是原子弹,不是放在弹药库里就有用的。
AI需要面向市场、接入应用,需要在社会生产生活方方面面的场景中发挥价值。技术的落后,就意味着国家经济活动和整体生产效率的落后,这将带来的是社会层面的总差距,绝对无法自欺欺人。由此而言,前文中提到的发展经济、壮大企业、解放思想、善待人才,就显得更加重要。
以上三点,是在技术快速迭代与中国乃至世界AI发展“喧闹”背后的一些“冷思考”。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从AI起点看,早在1956年,常青藤名校之一的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召开了人类第一次AI研讨会,首次提出“人工智能”概念。之后,美国政府和私营企业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资源,推动了AI研发和应用。
而中国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逐步开始有对AI的研究。直到本世纪初,才开始大力发展AI技术。在起跑线落后了数十年,几经追赶缩小了距离。在此关键时刻,中国需要先稳住差距,再持续追赶。
本文系凤凰网评论部特约原创稿件,仅代表作者立场。
编辑|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