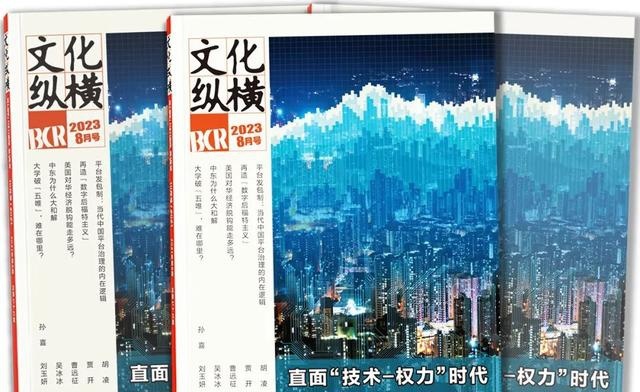“数字后福特主义”:中国互联网平台的唯一明路?|文化纵横


独家抢先看
↓ 进入公众号置星标 ↓
防止内容走丢
《文化纵横》2023年8月新刊发行
点击上图或文末左下角阅读原文查阅
投稿邮箱:wenhuazongheng@gmail.com
《文化纵横》邮发代号:80-942
✪ 贾 开
电子科技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
【导读】数字技术的发展是否必然导致封闭与不平等?近年来,“困在算法里的骑手”曾引起热议,但困在算法里的何止骑手。
网约车司机、主播、甚至是消费者…… 互联网已演变成一个高度中心化的生产组织,大型互联网平台成为瓶颈资源控制者,占据生产管理的主导权、控制权,经由数字技术罗织出数字版本的“福特主义”。
这引发了人们对于互联网分配前景的担忧。
不止如此,生产率停滞的现状也让人们担忧当前的互联网生产组织方式是否陷入了新一轮的“索洛悖论”:技术创新并未提高劳动生产率。问题显而易见:“数字福特主义”的生产组织方式在分配上已饱受质疑,如果连“做大蛋糕”这一承诺都受影响,那么就必须对当前互联网生产组织方式进行全面反思。
本文讨论了我们应当如何改造互联网生产组织方式。恰如作者所言:同一技术创新,在不同条件下会导致不同的生产组织模式,从而带来不同的分配性、生产性后果。但数字技术创新也不必然导致“数字福特主义”,以“开源软件”为代表的更具开放性、包容性的生产组织方式,也可能带我们走向一个更靠近“共同富裕”的“数字后福特主义”的未来。
基于此,本文指出:第一,在选择技术路径时我们必须摆脱“技术最优主义”,主动将更多的治理需要纳入数字技术选择与演化进程的考量中;第二,必须将探索多种形式的数字组织作为数字生产方式改革的重点;第三,必须反思 “技术答案主义”,真正将价值性、人本性关怀内化到数字化转型改革中。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3年第4期,原题为《再造“数字后福特主义”》
。
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再造“数字后福特主义”
数字技术创新将如何影响生产要素重组,以及生产组织变迁?
在数字技术创新应用日益普遍而深入的今天,对此问题的探索性回答不仅是满足数字未来想象的理论需要,也是在实践层面回应数字化转型困境的必然要求。事实上,当前我们可能正陷入新的一轮“生产率悖论”。上世纪70~80年代,与蓬勃兴起的计算机革命相伴随的,却是长期停滞的生产率,罗伯特·索洛在1987年即提出,“计算机在除了生产率统计数据之外的所有地方”。类似的,当前,以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数字技术创新(或称“数字化转型”)已经随处可见,并受到人们的追捧,但再次停滞的生产率是否预示着新的“索洛悖论”的到来?
上一轮“索洛悖论”的解决最终依赖于信息通信技术成本的大幅下降,以及企业信息化改造所带来效率的巨大提升。而当前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却远不限于此,不仅传统企业的运行方式正在发生变化,新的生产模式、商业模式同样层出不穷,以致既有的产业划分边界日益变得模糊;“零工经济”等新就业形态的兴起,则对传统治理框架带来了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数字技术创新究竟将如何推动生产组织变迁,以及在此变迁过程中我们应该如何主动引导或选择生产组织的新结构、新模式,便成为决定能否突破第二次“索洛悖论”的关键。
探索此问题的另一时代迫切性还在于,当前我们正在经历数字化转型的“转折点”。以上世纪末万维网的发明为起点,彼时人们对于新的数字时代的到来充满了憧憬:以开源软件、维基百科为代表的分布式生产方式的出现,既包含着大众生产、开放创新作为新生产力变革的希望,也昭示着一个更平等、更包容数字未来的可能性。但在经历二十余年的快速发展之后,分布式生产仍然仅局限于早期经典案例,并未上升为一般性生产方式得到普及;而数字平台的崛起在维系开放性的同时,也带来了零工资本主义、监控资本主义等质疑与争议。包括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尤才·本科勒(Youchai Benkler)在内的诸多代表性人物近年来对此的集中反思,也反映了对未来数字生产方式变革的新探索。
本文试图基于过往技术革命的历史回溯,区分功能性和结构性这两种生产方式变迁的分析视角,并在解释数字生产方式变革具体体现的过程中,以“数字后福特主义”的理论再造来重塑对数字生产方式变革的未来想象。
▍生产组织方式变迁的滞后性困境
技术创新将如何推动生产组织方式变迁,是历次技术革命中都会引起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但对此问题的追寻却呈现出明显的时间滞后性特征。尽管人们坚信技术革命必将导致生产组织方式变迁,但身处技术革命之中的人们,总是难以观察到变迁现象的发生:往往只有在经过技术革命爆发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生产组织方式变迁的普遍性和深刻性才逐渐体现,并被人所发现。电气化革命便是一个典型案例。
当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工厂开始电气化革命时,彼时人们以为这仅仅意味着动力来源由蒸汽替换为电力。但更长时间维度的观察却发现,“群驱系统”(group drive system)向“单驱系统”(unit drive system)的演化过程,才真正揭示了电气革命在生产组织层面的深刻影响:在蒸汽动力下因能量传输困难而不得不集中驱动的生产组织结构,在电力系统下却因电力传输的便捷性而能够分散排布,并由此为生产管理、车间布置、工厂规划等系列生产性活动带来了更大的灵活性。这一系列变迁,在工厂做出电气化替代的决定时并没有出现,也难以被提前预知。
尽管滞后性限制了我们对生产组织方式变迁具体内容的理解,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将始终处于“未知”的阴影之下,技术史的回溯性分析仍然有助于把握技术革命引致生产组织方式变迁的基本规律。一方面,如电气革命研究所显示,从集中式向分布式的结构转变,是建立在电力比蒸汽动力传播更为灵活的功能性特征基础上的,换言之,技术革命在功能层面的突破将为最终的生产组织方式变迁准备前提。另一方面,功能层面的突破并不必然决定生产组织方式变迁的方向与内容,后者的具体演化受到更为复杂的环境因素影响。例如,关于信息技术如何影响零售业变革的一项研究指出,相同的技术革新(条形码和扫码器的发明与应用)在不同国家却带来了差异化的生产组织结构变迁,并对不同主体产生了异质性结果:在美国形成了沃尔玛式的垄断结构,并抑制了供应商和工人的博弈能力;德国和丹麦却出现了大型零售商与供应商、工人共享规模经济收益的情况;英国和法国则是工人共享收益,供应商却在大型零售商的垂直并购中被边缘化。
于是,当我们试图揭示数字革命背景下生产组织方式的新一轮结构变化之“谜”时,功能分析与结构分析便构成了双重框架。作为结构变化的必要非充分条件,我们需要理解数字革命究竟为生产组织过程带来了何种功能性变化;当功能革命打开了结构变迁的“机会之窗”后,进一步的分析则需要聚焦环境因素,以展现生产组织结构演化的多重可能性。
▍“功能-结构”框架下的数字生产方式变革
根据生产组织过程所要解决功能性问题的不同,可从多个角度对数字技术创新引起的功能性变化做出类型化总结。例如,继承马克思对于一般机器功能的“三类型”划分框架,后续研究进一步突出了数字信息技术“控制”功能的延伸与发展。在马克思看来,机器之于生产组织过程的功能性作用主要体现在三点:动力(提供动力来源)、传输(调节、改变运动的形式并将之分配至工具机)与工具(按照特定目的作用于劳动对象)。但数字信息技术将原本从属于人类智慧的“控制”功能独立出来成为第四种机器功能,通过数据的收集与处理来实现生产组织过程的调度与调整。这一功能性变化被认为不仅改变了生产过程的组织形式(如形成福特制流水线),同时也深刻影响了生产过程中劳动者与机器、劳动者与管理者(及资本所有者)的相对博弈关系。
值得指出的是,数字技术创新的功能性变化不仅体现在对原有生产组织流程的再划分,还体现在对原有生产组织环节的再改造。例如在劳动过程管理领域,一般将管理工作划分为分工(定义工作的内容、流程与要求)、评估(界定劳动者工作绩效与偏差)与规训(对劳动者按照评估结果进行奖惩)三方面。尽管数字信息技术并没有带来新的劳动管理环节,但管理者完成分工、评估、规训的方式与形式却发生了重要变化:利用算法来推荐/约束劳动者的行为选择、全过程记录并多维度评分、动态替换劳动者与实时奖惩,正在成为新的、不同于工业革命时期劳动过程管理的新机制。
但正如前文关于电气革命历史回溯所显示,功能性变革即便不是可被完全预知的,至少也可以通过技术应用实践加以总结。与之相比,结构性变革的内容与方向更为模糊而不确定。
一般而言,数字技术创新与应用往往被认为与分布式、网络式结构改革紧密关联。自肇始之初,互联网端对端的扁平化结构从技术上绕开了第三方主体对信息流通的集中式控制,因此被“网络例外主义者”赋予了“乌托邦”式幻想。而2013年以来引起诸多关注的“比特币革命”(或更一般的“区块链革命”),同样延续并发展了数字技术推动分布式结构改革的历史路径,并进一步催生了去中心化自治组织、Web3.0等新业态或新思想的兴起与传播。在走向分布式、网络化结构的过程中,大众生产、开放创新等生产方式变革随之而来。处于边缘的终端生产者(如开源程序员)被更广泛地纳入生产过程,他们多样化的生产动机与能力不仅满足了“长尾市场”的非标准化需求,也挑战了以雇佣关系为边界的传统企业组织。
但是,分布式、网络式结构变迁并不必然意味着大众生产、开放创新等新型生产模式的胜利,其同样可能演化为传统生产模式的翻版乃至强化。一方面,数字平台在释放分散生产力的同时,仍然维系了对生产过程的控制力,它打破了由“资本所有者-管理者-劳动者”构成的“委托-代理”与“二元雇佣”结构,取而代之的是由“瓶颈资源控制者-开放生态参与者”构成的“集中式网络”结构。所谓“集中”,是指数字平台及其所有者仍然占据着生产管理的控制权、主导权;所谓“网络”,强调的则是打破传统工厂、公司边界后,此种生产组织结构的可延展性(随时加入或退出)、可累积性(新加入者将增加网络价值,而退出者并不在同等程度上减损网络价值)与可配置性(生态参与者的劳动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形成的生产关系可以被调整或干涉)。
另一方面,生产组织的分布式、网络式结构变迁模糊了生产要素的流动边界,数字平台等新的生产组织在演化为新型基础设施,并在各领域引发外部性的同时,也逐渐呈现出“社会公地资源私有化”的重要特征。与大众生产、开放创新等边缘生产力的蓬勃兴起相匹配的,是分布式网络作为新型基础设施的逐渐成形,并往往以数字平台或通用技术协议的形式而体现出来。斯洛文尼亚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即指出,比尔·盖茨能够获得巨大财富,并非因为微软的产品售价更高或成本更低,而是缘于它创设了能够使全世界人民进行沟通的新媒介,且该媒介的价值并不来源于单个个体的使用价值,而是全社会共同使用所带来的公共价值。事实上,对于不同数字生产与收益分配过程而言,它们所依赖的“社会公地资源”大致都可被理解为人类公共知识或交往关系的积累,并在不同场景下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社交媒体平台体现为用户间的社会联系,搜索引擎平台体现为用户搜索信息的偏好,电子商务、出行等撮合平台则体现为交易历史数据。在此视角下,数字生产方式变革的重要特征之一便是对“公”“私”边界的再定义,并以社会基础设施为载体将社会公共性活动纳入商品生产与分配过程之中。
于是,我们从功能和结构两个层面对数字生产方式变革的内涵做了描述性分析,接下来的问题便在于,当前如何走出第二次“索洛悖论”困境,并在近年来的集中反思基础上,引导未来数字生产方式的持续性变革?本文接下来的分析将指出,数字生产方式的未来变革并不一定是要“另起炉灶”,而是仍然可以从过往成功或失败的经验中汲取营养,以最终释放数字技术革命的潜在生产力。在理论上,这可被称为“数字后福特主义”的历史困境与未来再造。
▍“数字后福特主义”的历史困境:开源的成功与失败
“福特-后福特主义”的比较框架,是已有研究对工业革命时期生产方式变革两条主要路线的总结性梳理。肇始于福特汽车公司的生产管理实践,福特主义(Fordism)构成了一套基于工业化和标准化大量生产和大量消费的经济、社会体系,并被视为工业革命时期生产方式变革的主流范式。但是,“灵活的专业化”(Flexible Specialization)作为生产方式的“另一条道路”,始终未被排挤出工业革命的时代浪潮。“灵活的专业化”具体是指高技能工人在使用通用机器过程中生产出小批量且多样化产品的生产模式,在生产组织层面体现出自组织、分散化、临时化等特征,并因此不同于批量生产模式的一体化整合特征。以此为起点的后续研究逐渐演化为后福特主义的理论主张,并体现在强调精益生产的“日本丰田主义”或从流水线转向生产岛的“德国道路”等具体实践之中。
崔之元教授曾将福特主义与后福特主义的关键差异精练为两点:“技术分工”与“社会分工”是否一一对应,以及在生产关系上是经济专制还是经济民主。一方面,福特主义难以看到分工框架下管理者与执行者相互促进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及二者融合以形成新的分工框架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福特主义将政治从对技术和经济的分析中剥离出来,将后两者视为能够“自我实现”的独立系统,从而忽视了对技术和经济的分析离不开对生产关系的分析。正是在对福特主义的反思基础上,后福特主义的重要性才逐渐得以体现,并被认为更适合数字技术革命背景下正在兴起的知识经济新体系;而开源软件、维基百科等新生产模式正好作为佐证赢得了人们的赞誉与希望,由此形成了“数字后福特主义”的新模式。
以开源软件为例,它的初始定义是指源代码可以被任意获取的计算机软件,但更具革命意义的解释来自生产过程与管理视角。不同于集中式、科层式的软件生产过程与管理模式,开源软件以代码的开放性包容了分散参与者的多元动机,并基于自由对话、共识决策、以个体网络联系为主的小群体联盟形成了规模化集体行动。无论是就生产过程还是结果而言,开源软件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仅遍布全球的程序员愿意免费且能够有效参与开源软件开发进程,甚至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公司也纷纷将本具有私有产权属性的软件代码贡献给开源社区,更不用说Linux、Apache、Android等开源软件产品已经成长为数字世界的基础底座。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有理由欢呼“数字后福特主义”作为一种生产方式变革的胜利,并希望能将其拓展至更多领域,以充分释放分散主体的潜在生产力。但遗憾的是,这种移植努力并没有成功。
以开源软件为蓝本,本科勒在2004年提出了“基于公地的大众生产模式”(Common Based Peer Production,CBPP)的核心概念,并试图在数字技术革命浪潮中确立起该模式与市场模式相并行的重要位置。在本科勒看来,数字技术的创新价值在于打开了社会化大生产的改革空间,即以开放性公地资源包容多元生产动机,而分散主体参与生产过程又进一步维系并丰富了公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事实上,作为互联网基础的TCP/IP协议、万维网协议以及多类型的开源软件,都可被视为CBPP的典型代表。但在此基础之上,包括社交媒体、电子商务、搜索引擎等在内的更大量商业应用,无不在开放的互联网层级架构之上构建起一个又一个的“圈地”壁垒,并最终回到了商业资本主义的老路。本科勒不无惋惜地在2019年哀悼了CBPP的失败原因:与松散的网络参与者相比,商业公司能够更加持续且专注地为竞争新的控制点而努力;开放网络本身也会逐渐形成内部的科层与不平等结构;开放网络在成为创新源泉的同时,也造成了有害和违法内容的兴起。
于是,在经历数字技术革命初期对开源软件的惊喜与期待之后,以CBPP为代表的“数字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变革便逐渐淡出了人们视野,数字平台在控制一个又一个“瓶颈”资源后,也完成了在开放网络空间的“圈地运动”。在此意义上,数字技术所许诺的结构性变革并未普遍发生,这自然引起了第二次“索洛悖论”的担忧,以及对于既有数字生产与分配方式的反思。
但值得注意的是,开源软件作为普遍性生产方式变革向其他领域拓展的失败,并不意味着对“数字后福特主义”的全面否定。恰恰相反,为释放分散主体的潜在生产力,“数字后福特主义”需要得到更大程度的肯定与推广,这在当前便体现为其再造进程。
▍“数字后福特主义”作为未来的再造:技术与治理
当前正处于数字生产方式变革的过渡时期,其关键特征之一就是“数字后福特主义”的再次兴起,这又具体表现为理论与实践的三个“转变”。
第一,在摆脱技术最优选择的固化思维的基础上,数字技术的多重路线探索日益引起多方重视,并因此要求将更多的治理需要纳入数字技术选择与演化进程的考量之中。传统思维往往认为,不同技术方案之间的竞争是有最优标准的,因此在技术选择与演化时应更多遵从技术专家或管理者的意见,反对技术在应用与生产过程中的持续优化与调整——这正是福特主义对待技术创新规律的基本态度。但近年来针对数字技术创新应用的反思,体现了对此固化思维的修正。例如,斯图尔特·罗素即提出,当前以优化确定目标为基本思路的人工智能开发理念尽管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存在不可控的潜在重大风险,他认为在模糊目标引导下的“人-机”合作路线值得更多关注,后者更强调在与人(或社会)互动过程中不断修正人工智能算法优化目标。
第二,在反思整体性组织架构的可行性及合法性的基础上,多种形式的数字组织再次成为数字生产方式改革探索的重点对象。利益相关方往往认为纵向或横向的一体化整合是数字化转型的必然选择,其目的在于打通不同层级、不同领域的数据壁垒,以数据的整合共享来替代或简化现实复杂性,从而实现生产与治理过程的自动化闭环改造。但这一带有典型福特主义特征的转型思路在近年来同样引发反思,当前的实践改革也体现出从整体性数字化解决方案回退的新趋势。例如,一些互联网企业率先开始调整原来强调“大一统”的“数据中台”组织架构,转而重新聚焦分领域、分场景的数据生产与应用,这不仅代表着对于日益强化的数据治理监管要求的回应,也意味着数字平台本身组织架构调整的多重可能性。
第三,在修正“技术答案主义”作为主导理念的基础上,价值性、人本性关怀逐渐成为数字化转型改革的重要理念。“技术答案主义”认为人类生产生活的所有问题都存在技术解决方案,并试图在效率优先的外衣包装下,以透明、确定、最优的技术方案替代模糊、多变、多元的治理过程。这一理念被广泛应用于数字化转型的各个领域,其隐藏假设是以功能性目标代替人类生产生活活动的政治性或社会性目标;但这种替代的后果可能“南辕北辙”,甚至可能进一步恶化人类社会的治理问题。例如在教育领域,预先设定好目标(往往体现为考试通过率)并细化为数字指标,然后通过全方位数字监控来督促学生满足要求的技术解决方案,事实上与教育的本质背道而驰。教育需要开放性的师生互动,并在实验试错、即兴创新中完成培养人的过程。显然,仅凭数字方案无法实现这一点,教育过程仍然需要价值性、人本性的治理回应。至少教育目标的设定就不能仅仅由技术或管理专家决定,师生的共同参与和协商调整才更重要。
上述三点转变还很难说已经形成主流性影响,但作为萌芽已经明显呈现在数字生产方式转型的探索道路之上。尽管这三点是从不同视角出发提出的差异化改革方案,但它们的共性特征都可被概括为“数字后福特主义”的再造,因为它们都试图将“人”(而非技术)重新置于数字技术革命的中心。尽管数字时代的分工框架可能经历重大变化,但这并不代表数字生产方式将成为“自我实现”的独立系统。无论是对多重技术路线的探索,还是在承认社会复杂性的基础上对规则的尊重,抑或是将技术方案视为实现价值的工具而非目的,都是对过往“数字福特主义”式理念的修正。所谓“再造”,则是对彼时以开源软件为代表的“乌托邦”式理念的修正。在本科勒的反思中,开源软件式生产方式之所以没有在更广大领域得到拓展,根本原因还在于彼时的理想主义者仍然陷入了“技术决定论”的思维窠臼,他们认为端对端的技术架构将自然带来分布式生产方式的胜利,而没有预料到数字平台才创造了更高质量的数字化商品与服务。
正是在认识到过往不足的基础上,当前改革才更加重视“技术”之外其他治理因素的重要影响。无论是多条技术路线的竞争,还是多重组织方式的探索,抑或人本目标的再定位,都是对简单化“技术决定论”的抛弃,并试图在技术与治理的互动中找寻新的数字未来。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才可能最终通过数字生产方式的改革——不仅仅只是数字技术革命本身——来突破第二次“索洛悖论”,并胜利渡过数字化转型的“转折点”。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3年第4期,原题为《再造“数字后福特主义”》。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
打赏不设上限,支持文化重建
订阅服务热线:
010-85597107
13167577398(微信同)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早8点至晚8点
“特别声明:以上作品内容(包括在内的视频、图片或音频)为凤凰网旗下自媒体平台“大风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videos, pictures and audi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the user of Dafeng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mere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pace serv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