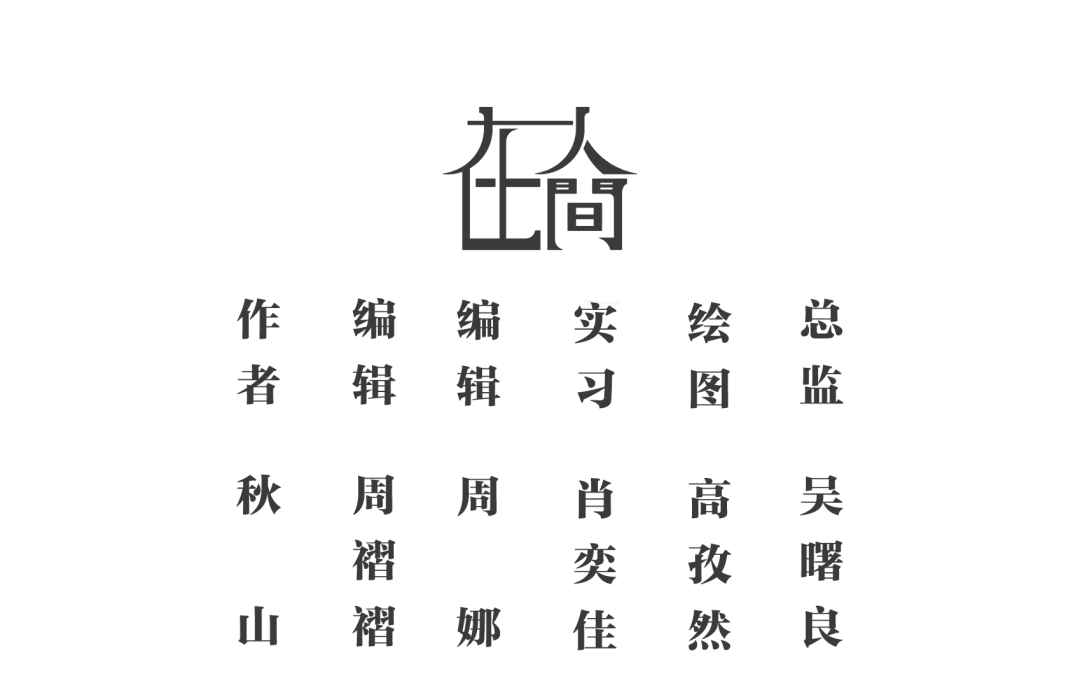在人间|等待被裁的人


独家抢先看
撰文| 秋山 编辑|周褶褶 周娜
一切并非来得毫无征兆。今年刚入夏的一个傍晚,临近下班,主管拍拍我的肩膀,说:“我们出去聊聊。”
彼时,这家互联网巨头刚刚经历了几乎史上最大的一次组织调整,曾经人满为患的工区人员寥寥。那天下午已有几个人被陆续喊出去谈话,但回来后无人交头接耳,办公室里,只有双手飞快敲击键盘的声音。
跟着主管走在会议室的路上,我开始猜测,她会给我一个什么样的答案,是宣布一切戛然而止,还是会告诉我另有转机?
在逼仄的小隔间里,主管下达了“判决书”:一个月时间找转岗,否则等待我的就是1.5+1的裁员赔偿。这是我放弃了铁饭碗、跳槽来到这家互联网巨头刚刚一年多,第一次正面迎上“裁员”这头巨兽。
我强作镇定地点点头,那一刻头上仿佛出现一根血条:only 30 days left……
不是每个人都能准确回忆起警报是哪一天响起的,但自从听到那声遥远的狼嚎,人便如同身处远古的夜晚,战战兢兢,要为接下来每一天的生存枕戈待旦。
“裁员”仿佛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悬挂在人们头上。剑在一寸一寸下落,不日将直抵眉心。
收到裁员通知后的第二周,我接到HR的约谈,她说,之后这一个月可以不在工位上待着,只要在有需要时来公司即可。
我突然想起前同事小A,一个性格很好、经常在脑暴会上提供创意的姑娘。在去年某天早上被叫走后,她迅速收拾完工位离开了。直到她账号自动注销退出工作群,没有一个人公开问过一声:她怎么了?
当时,这场心照不宣的沉默令我感到诧异,但对此也不敢说一个字。如今我也快成了那个“突然消失的人”。
在企业内部,裁员就像房间里的大象,无论外面传得如何沸沸扬扬,但内部人们都保持缄默、避而不谈。只有在咖啡馆里,偶尔会看到两人对坐,漏出一两句唉声叹气。
关于去年的那场“裁员”风波,李华也是亲历者之一。她事后回忆起来,自己其实早早地接到了信号。
去年2月,一位中层朋友告诉她,公司可能要开始裁员了,已经对管理层进行了培训,细节甚至达到如果对方可能作出攻击姿势、或掏出凶器,只要大喊保安,保安10秒钟内就会出现。
平时大大咧咧的她没想到,这么快自己就变成了“要被防备的人”。
一个再正常不过的聊绩效会议上,主管突然告知,不会跟她续约。
当时,她刚转入这个新岗位不到一年。6年前,她以应届生身份进入杭州这家互联网公司,她清楚地记得,当年招聘应届生的标语是——“来阿里上大学”。之前,她干了6年技术工作,是淘系大促组的重要成员,她想换个部门再闯一次,尝试更贴近业务的产品经理一职。
这意味着从半个新人开始。但她没想到,此时职场环境与刚毕业时相比天差地别。从前着急起来,她可以在会议上对着领导拍桌子,主管对新人的态度总是“你第一次做错了,没关系,但下一次要改”;但这次,“哪怕你做得对,主管都会说没有达到我的预期,对你有点失望”。
在煎熬中度过半年多,每周996,身体很累,但她觉得自己在飞快成长,再来一点时间,就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产品经理”。
就在这时,突然而至的解聘通知给了她重重一击。刚离开不过半个小时的工位,霎时变得张牙舞爪了起来。
她站在人群中,觉得自己像一个弃婴。“他们都热火朝天地讨论工作,只有我是个即将要走的人。虽说我人在这里,但没有人看得见我。”
她开始主动自我“隔绝”,很难再把精力集中在工作上,开会也只做个旁听的观众。她对食物失去兴趣,中午去找组外的朋友打听消息,在公司晚饭开餐前回家,拌一拌网上买的速食凉皮,和着水吃下。
那段时间,有相似经历的不止她一人,“大家都在盼着这波裁完能安心做事,而不是每天陷在害怕恐惧中”。
有时HR聊完一个部门,刚觉得“稳了”的另一个部门过几天就开始被约谈,有些藤校毕业的学生入职不到1年就要走人。李华听说有些同事甚至连结个婚都偷偷摸摸,不敢让公司知道。因为据说在裁员的优先级里,已婚未育的女性是歧视链的底端——尽管HR往往不会道破这一点。
经历了三次裁员的马冬已练就了敏锐的嗅觉。去年秋天,她又嗅到了一丝熟悉的气味,把自己的担忧写在了匿名的社交平台上——“随时可能被裁员的感觉”。
包括百度在内,39岁的她一共换过四五份工作。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很多人不理解她为什么这么拼。她说她喜欢销售这份工作带给她的成就感,每签一个大单、谈拢一个客户,都让她能开心地吃一顿大餐。
当时,她所在的科技公司空降了一位新总裁,似乎专门为“裁”而来,裁完一批应届生,又把销售团队缩减了100多人。“公司投资快花完了,想上市,领导一头包,我也能理解”。
居安思危,她开始投简历,也收到过几个offer。部门经理看出她“心思有点活络”,便主动找她谈话,“你不要想太多,我们部门目前还是非常安全的,只要安心把手头的事做好,就没问题”。拿着这份保证,她拒绝了别家公司的橄榄枝。
不想一个月后,这位经理也慢慢“隐身”了,一个月才出现一次,请假时秒批,汇报工作不再回复,马冬感觉暴风雨在迫近。
“公司内部有啥消息也没人告诉我们,孤岛一样,也像案板上待宰的鸡鸭,随时等待自己的命运”。写完这句,她又试图给自己一点鼓励:“北京的秋天来了,大自然的规律始终是无法阻挡的,那就开心迎接吧。”
在亲友更多的朋友圈里,她仍保持3天可见、岁月静好的状态,一切风平浪静。
我开始止不住怀疑,到底是哪一环出了错:年龄?绩效?还是身在已婚未育的“歧视链的底端”?
不甘心的时候,我在内部转岗平台刷了一遍又一遍。对口的岗位不多,更新时间停止在好几天前。我开始放下所谓的矜持,大量联系朋友或朋友的朋友,对一些人旁敲侧击地询问有没有岗位,对另一些人直言相告我的 last day。
那段时间我深刻感受到“相对论”的存在,一个月很短,但每一天很长。有时一天要应对两三场面试,有时一整天躺在床上,心就像在滚筒洗衣机里搅了又搅。脑海里只回荡着刘建宏老师那句著名的解说:“留给中国队的时间不多了。”
但糟糕的消息接二连三,一些面试无疾而终,一些联系好的面试官告诉我:“对不起,我们临时关闭了岗位,所有的HC都锁住了。”
血条越来越短。我开始害怕亲友的微信,我怕他们询问:“你工作怎么样了?”
与之成反比的是更加勤奋地跑健身房,在曾经厌倦的一遍遍重复动作中,异乎寻常地,我找到了一种可以让内心平静的确定性。
在确定性到来之前,没有人能独善其身。马冬也不例外。在忐忑的心情中,她迎来了部门总经理的离职散伙饭,从此任务不再有人安排,连客户过来都不知找谁对接,“所有人都知道我们待不久了,但不知道到底哪天走,就是这样的状态”。
但办公室里,四五个人每天还是如期而至,按时打卡签到上下班——如果考勤不合格被辞退,是拿不到N+1的。
即使上厕所,他们还要时不时对上其他部门同事的侧目和窃窃私语,“哟,你们部门还在呢?”马冬大多数时候选择沉默,偶尔回怼一句:“我说你大点声,都能听见!”
直到在朋友圈刷到其他同事朋友圈发的公司年会视频,她才确定,自己的部门是被彻底遗忘了。
他们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如蚂蚁搬家一般,每天带走一些私人物品,直到桌上只剩下一台办公电脑和一本笔记本。大家苦中作乐,每天各带一包零食,往空桌上一倒,闲聊天、读书、看电视剧。马冬甚至重读了一遍《骆驼祥子》。
这几年,她陆续听闻了一些朋友被裁员,都会有一笔不菲的赔偿金,有人领完“大礼包”就给自己放个小长假,去出国读书、旅游,在家修身养性。但对她来说,“这一切看起来像带薪休假,内心还是很焦虑的”。
在马东漫长的等待中,出现过一个小插曲——
部门空降了一位总经理,大家仿佛看到了一线希望,纷纷跑去对接手头上的客户、项目情况。但后来这个新经理也“崩不住了”,暗示说整个办公室只能留下一个人。
当时马冬的心一下子悬起来了,“就像那个大逃杀游戏,我们要开始互杀了”。
不过这场闹剧还没开始,HR先传来消息:你们部门一个都不留。
等待被裁的时光里,李华开始整晚不睡,几乎变成一个哲学家。对她来说,这仿佛是第二次毕业——没有鲜花和掌声,而是略带悲观地,认清工作的本质,“世界上哪里没有我都一样。没有我,也有一万个我们会给他们打工的,我们只不过是时代的一粒沙。”
当读到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那本《毫无意义的工作》时,她摘出这段话:
“雇用你的时候,你感到自己是因为有用才获得了这个岗位,结果却发现事实完全不是如此,但又不得不配合表演……
这种先让你产生自己有用的错觉,然后再被全然否定的经历,不仅仅是对自尊感的摧毁,还直接动摇了自我意识的根基。一个人一旦停止对世界产生有意义的影响,那这个人就不复存在了。”
不同的职阶,对应着不同的被裁脚本。如果说职场中低层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自尊感被摧毁的无意义感,高层的被裁之旅大概率会凶险更多。
职业经理人老张告诉我,等待被裁的那一年,是他人生中最煎熬的一年。
疫情前,他当时任职的公司空降了几位资方领导,一些人开始做好“被干掉”的准备,他也不例外。业务会议时,一位被他亲手从普通职员一路提拔到副总的下属,不再坐到他身旁,刻意保持距离,假装不看他;他一发言,这位下属就一改往常,开始唱反调。
老张从此对“远近亲疏”有了新的理解,“其实很多时候,人性根本经不起检验”。
然而等待他的远不止人情冷暖。资方叫来了八九个审计,在公司最大的那间会议室里,对他开始了长达三个月的审计。资方轻描淡写说是董事长的意思,要查查账。但在老张等高管的眼中,这明显是冲着他们来的。
所幸,老张并没有被查出任何问题,但这也避免不了被反复叫去问话——老张至今不愿意回忆具体细节, “总之是非常屈辱”。他知道,尽管自己已经表达了100%的诚意和努力,“他们就是在找茬,想让我离开”。
时隔几年,忆起这段颠沛的往事,老张不禁骂了脏话:“在资本面前,职业经理人所有的理想、抱负和能力,就是用来被x的。”
当HR终于找上马冬,开始讨论裁员方案时,她和同事已分过工,谁负责录音、拍视频、核对补偿金额,都一一到位。
整体过程进行得挺顺利,拿到赔偿,她在小红书上发了自己领到的补偿金额,写上“39岁中年妇女重新启航”,她没想到一下收获了3597个赞,成为浏览点赞人次最多的一条状态,也是通过这条状态,我认识了她。
在这条状态下,高赞大多是同龄人的留言:
“我37,刚被约谈,预计赔20左右…很满意”;
“加油,我也39,今天去面试居然被面试官说,你都39了……”;
还有一些年轻人私信问她:“公司不会这么爽快,只会想方设法让人走,该怎么办”。
虽然觉得自己不够权威,她还是努力提供一些帮助,毕竟自己第四次被裁,也算“四朝元老”了。
而五年后再次面对裁员,Amo要打一场更硬的仗。
Amo是我在一次聚会上认识的朋友,那时他刚从深圳到北京,作为设计师的他衣着精致,话不多,时常一针见血。他也是N朝元老,被裁过,也裁过人。5年前第一次被腾讯裁掉的时候,他还偷偷躲在被子里哭过。
去年,他所在的字节跳动已传出裁员的消息。因为住得远,他不想像别人一样撑到晚上10点下班,每天提前一小时回家,被上级说过“投入度不够”。当主管给他第二次打出差绩效时,他明白自己恐怕在劫难逃。
这次,他不想再像当年一样丢兵弃甲、躲在角落。“我经历过一次,也足够了解《劳动法》,还有一点储蓄兜底。网上也有很多人分享被裁的事,裁员不再是一件很可怕的事了。”
在一对一的谈绩效会议上,主管说了一通他的缺点,Amo直接问,你明确告诉我,哪里要改,或者什么东西怎么改。
对方露出了苦笑的表情,好像在看一个冥顽不化的人。
Amo又反问,你该用PIP“激活”我了吧?
在公司里,PIP协议(Performance Improvement Plan,绩效改进计划)基本是公司发起裁员前吹起的号角,它意味着一个职工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达到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超高目标。
当时主管似乎惊住了,“可能没遇到一个自己把自己‘激活’的人吧”。但不出所料,主管从文件袋中掏出了一份事先准备好的PIP协议。
他扫了一眼,上面要求他:在两个月内完成半年的工作量。
“这对公司来说是笔合算的买卖,给你时间找工作,你完不成目标主动离职,它还不用赔偿。”此前,Amo问过相熟的同事,这里有没有人签了PIP仍能留下来?得到的答案是几乎没有。
他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态度:“我可以签PIP,但它没有任何法律效力,逼我走得给我N+1”,但主管的答复是,“公司没有这个规定”。
“如果以前签署PIP协议,我会觉得丢人,是自己能力不行,其实这个理念是领导灌输给你,并希望你也这么认为的。”
这一次,Amo决定说出办公室里那只沉默的大象。他把自己和主管的对话,原封不动告诉了全组同事。
打破砂锅的结果出乎意料。
某种意义上,Amo一跃成为公司被裁的“意见领袖”。
一些同事来问他是否需要介绍猎头,还有一些年龄比他小的同事,过来向他请教裁员过程细节,希望日后有招应对。这让他颇为自豪地感慨道:“我觉得他们比我当时要幸运一些。他们知道有裁员这事儿了,都知道要学习劳动法,最大程度保护自己的权利。”
但PIP的魔咒仍在继续。第一个月,主管还会过来对一下PIP完成的节奏,但在给“N+1”赔偿金上仍未松口;第二个月,新招的人选已入职,主管甚至放弃跟他交流,Amo明白,只有第二条路可走了。
他决定约HR进行一场正式会谈,这次他要主动发起冲锋。Amo提前花了一个晚上查劳动法和相关案例,走进会议室,面对一脸严峻的HR,他先说:“你现在不要说话,听我把这个PPT讲完,中间不要打断我。”
他开始条分缕析。开门见山是讲劳动法,开除一个人要先证明他能力不行,必须举证;然后要进行培训和调岗,要去真实地告诉他这件事怎么做,否则也要举证;他还举出了数据证明,2016年以来,公司和员工去打赔偿胜诉案的话,公司胜诉的几率是0.6%。
讲完他关上电脑,镇定地看着HR。
对方足足愣了一会,涨红了脸,说:“我没啥可讲了,既然你已经把这件事情说得这么清楚了,我可以去给你申请赔偿。”
之后,HR又带着一点佩服的口吻说:“你真的内心挺强大的,这事放在别人身上可能承受不了。”
他没说什么,回到工位,将伴随自己一年的电脑支架、行军床转送给周边的同事。
一个星期后,Amo等到了公司会给出“N+1”的答复。他舒了口气。
离开公司几个月后,李华听说,主管招进一个“关系户”。她哭笑不得。她开始复盘,如果再经历一遍,她肯定会每天正常上班,“如果主管非要逼我走,我就直接给大老板发邮件,请大老板、HR和他坐在办公室聊。但当时我只是个小白,人在很焦虑的时候很难看清自己的处境”。
在倒计时即将停止前,最后一根稻草曾出现过一瞬,一个业务部门向我抛出橄榄枝——
但最终,我还是没能“自救成功”,转岗卡在人事部门的流程上:也许因为已过30岁的年龄,也许因为过去岗位的绩效不够最新的要求,我只收到了一切戛然而止的通知,却无法找到任何明文规定来给自己一个确凿的解释。
交还电脑和工牌、拿到离职证明,走出公司后的第三天,路上突然传来一声尖锐的防空警报。
我猛然想起,这是5.12汶川地震已过去15周年了。警报声散去后,路上行人又恢复了漠漠的神情,各自前行。
我和马冬交流离职感想,她也是收拾完最后一点物件,走出待了一年的大楼,环顾四周,发现可以告别的人,只剩平时常打招呼的保洁阿姨和保安小哥。
她抱着箱子对保安说,“我明天不来了”。保安一开始露出吃惊的神情,但很快恢复平静,只是叹息了一声:“好多人都不来了。”
那时新年刚过,她还没找到新工作。她没有告诉父母和孩子自己被裁的事,而是每天按时出门,去图书馆看书、公园遛弯,参加行业的线下会议,拿回一大摞资料,维持着仍在工作的假象。“因为我也不能保证下一份工作能做多久,不如让他们觉得我一直在这里好了”。
至此,她总共经历了4次裁员,甚至总结出了一套“裁员心路历程”:“刚开始等待被裁时会感到焦虑、忐忑、害怕,然后觉得不服气、无助、不安,到最后这把‘剑’真的落到你头上了,反而踏实了,拿着这个钱悲壮地告个别,回家找到下一份工作后,就可以自嘲这段经历了。”
此前马冬干得最长的工作是在一家做安全软件的外企,福利高,干得好还可以出国领奖,待了五六年,“那时候真想待一辈子”。但在她休完产假后,情况突然急转而下,这家外企决定裁撤大批中国境内部门。
她很快找到了下一份工作。那是2017年,她30岁出头,觉得一切向好,未来可期。
今年春天北京风沙大,她顶着飞扬的尘土去面试,有时还会感慨一声:“我怎么这么狼狈,混到这份上来了?”她经历了职业生涯最长的一段gap期——两个月。降薪入职新工作后,她已不再想这个问题。
对老张来说,被裁反而是一种解脱。回归到不用凌晨两点突然被召集开会的生活,他感觉身体各方面指标慢慢恢复正常。
他开始沉下心写作,闲时读苏轼的诗句,从“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到“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再到“此心安处是吾乡”。
“人生总会经历一个再次寻找和选择的过程,内心的安定是最重要的,要真正相信自己的能力。”老张说道。
拿着赔偿金,Amo开始学习一些心理学课程,部分为开解自己,部分为了帮助别人。很多事情在学习后慢慢想开,比如裁员经历对一个人的精神摧残,“公司把你招进来时,会让你觉得工作是有一定贡献和价值,但用裁员否定你后,你之前建立的价值感突然之间就崩塌了。这个情绪如果没有发泄出来,憋在心里,人是会慢慢生病的,就像身体的代偿机制。”
曾经,他被“裁员”困扰两年之久,以为是自己的能力问题;现在他终于意识到,“裁员并不意味着你是一个loser,这不是一个唯分数论的世界,你也不是最后一名”。
这次离职,他偶尔会听前同事说,隔壁组长还会在周会上提及他的名字,警告员工如果不努力,下场就会像他一样。他不再有任何情绪波动,只是付之一笑。他很快收到了两个offer。
入职新公司的第一天,傍晚6点半,已有人陆续离开,他不敢起身,默默观察。快7点一抬头,公司只剩两名同事,也在收拾东西。
他不敢置信地问道:“我们这个点下班?”
同事一脸奇怪地回答:“对啊,怎么了?”
他陷入一种摆脱996的巨大的眩晕中,第一次感觉夜晚可以完全属于自己。背着包走出公司,夕阳尚未落下,整座城市不再是黑色建筑群里意兴阑珊的灯火。
那一刻他迎着夕阳,忍不住手舞足蹈起来。
*文中李华、老张、马冬、Amo均为化名
*本文插画均使用 AI 绘制
凤凰网原创栏目持续招募优秀的作者,千字500元起
简历和稿件请寄:zhouhl@ife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