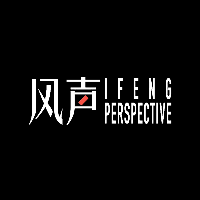风声|钱学森之问后又有“颜宁之问”,或许她问错了?


独家抢先看
作者丨刘正
Simon Kucher 战略咨询顾问
自从普林斯顿辞职之后,颜宁最近又火了。作为深圳湾实验室主任,颜宁在博士生推免面试时向年轻的申请者们提出了“灵魂拷问”:
假设时间来到10年后,你已经成为一名PI(Principal Investigator, 即独立带领一个实验室的博导),你拥有所需要的所有资源(优秀的科研团队、充足的经费、完善的实验设备、大把的时间),那你最想探索的科学问题是什么?换一种说法,这一辈子有什么科学问题或者技术难题,你能解答或者突破,就觉得今生无憾了?
但令她失望的是,没有一个人能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大部分学生只敢在过去做的研究上弱弱的提出一些微小改进的想法,或是泛泛而谈自己的科学热情,而更多的学生则“诚恳”的表示还未想过这类问题。
颜宁之问不适合本科生回答
初看起来,这是中国教育扼杀学生创造力的畸形后果:尽管坐拥日渐丰富的科研资源,我们的学生只是机械的沿着“好学生”的“成功路线”浑浑噩噩的前行,把科研当作刷分打榜的游戏疯狂内卷,却不知向何而学,也不知为何而学,没有学术梦想,缺乏独立思考。
真正读过博士的人,比如我,则觉得这个问法不好。
其实颜宁自己也意识到,这种问题对本科生未免过早,这实际是博士毕业工作面试才该问的问题。一个刚毕业的本科生,他对科学的认知大都来自课堂上的二手观点,或是实验室小课题上撷取的吉光片羽,并不具备对学术领域遍历全局后凝聚的科学品味和直觉,理解往往比较幼稚和局限。
在这种大问题上如果侃侃而谈,即便不是好高骛远,也多少有点拾人牙慧,半瓶醋晃得凶。假使同样的情况放到华为,说得最多的那位一定会被任总评价“此人如果有精神病,建议送医院治疗;如果没病,建议辞退”。
这些聪明孩子在人生路径的重大分叉点,自然清楚什么是最理性的选择。在这种几乎没有先验信息的短线博弈场景下,你不知道面试官提这个问题的意图,也不清楚自己会不会答到“拿分点”,或是和面试官的学术观点相左;因此,风险最小的最优解只能是避而不谈。
当然,也有人讽刺这个问题谁提都可以,但从颜宁嘴里说出来就多少显得不那么真诚,因为颜宁自己就属于“唯论文影响因子”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一直以来,做着科学品味不高的结构生物学课题,靠着“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的勤奋,24小时不睡觉肝试验,凌晨抢发论文才有了今天。如今功成名就,反而怪后辈们缺乏学术梦想和独立思考。若是退回二十年前,她自己是否能答好这个问题呢?
当代科研靠设备、管理和团队协作,并非靠“idea”
刨去这些争议,我其实理解颜宁问这个问题的初衷。
博士生推免面试并不是给她自己招学生,而是给整个深圳湾实验室考察高潜力的博士生人选。从博士生培养的理想来看,Dream Big & Aim High,不设限的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无疑是成为科研领导者所需要的品质。
但我想说,在科研的冷酷现实下,我们无法培养这种品质。而在科学的未来终局里,我们也可能不需要去培养这种品质。
无论偶像电视剧里如何幻想,今日的科研就不是什么单枪匹马的浪漫征途,或是自由无用的思维探索。大多数科研早已进入工业时代,靠的是对先进科学装置的投资建设,通过甘特图管理项目进度,团队分工集团化作战。
一个本科生能想到的任何idea,在很多年前就有人想到过,甚至都已经证伪了。这种范式下的科研成果,都在一条可预期的研发规划图上,无论谁来做,终究会获得一个结果。
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蒲慕明院士说得很现实,“实验科学界经常说ideas are cheap, show me the experiment data(想法不重要,把实验数据拿出来)。大家都知道什么是重要的问题,谁把试验做成功,做完整,谁就有主要贡献。有人说这是我的idea,那只是你自己的'想法'罢了,事实上idea在实验科学上没有太大的意义”。
在这种冷酷的科研现实下,博士生培养的那些理想既没有合适的环境,也不满足实际的需求,只是对师徒制“美好过去”一厢情愿的追忆。
尤其在生物学这种“try error”的实验科学,博士毕业对口的是“科研工作者”,而不是“科学家”。自律,严谨,手快,笔勤,一个具有这些“清教徒”品质但天资平平的学生,如果家境较穷又不是穷到对钱过分渴望,那就足矣!
毕竟,颜宁自己的成功因素里,并不包含能答出“颜宁之问”的能力。冷冻电镜也不是她发明的,甚至是当年在暗室里一遍遍培养晶体的她都不敢想的,但当冷冻电镜问世之后,她是把这个技术用得最溜的人。
科研方向的明智远比勤奋重要
科研现实的边界条件和激励曲线,无法培养“颜宁之问”想要的品质。
有些人会发现这种现实的长期缺陷,如果所有博士生都把自己训练成一台高效执行的机器,那么谁来设定研发进度的方向呢?即便这个方向早就被设定下来,如果没有根据最新的研究成果进行修正,就无法避免陷入局部最优的陷阱,不断地内卷和打转。
“遗传特性 ‘exploration & exploitation’ 的平衡里不应无限追求效率更高的雕花,也需要为未来的可适应性留出概率性探索的空间”。进化论的这一洞见,对包括生物学在内所有科学的发展本身,也具有十足的警示价值。
所以我们看到有大佬呼吁要培养“战略科学家”,因为方向上的明智永远比行动上的努力更重要,而最糟的是愚钝又勤奋的人,他们会在其他人反应过来之前把事情推进到无法挽回的程度。
但真正理解进化论的人会意识到,名将从来不是在总参学校里培养出来的,而是在战火中被命运遴选出来的。
颜宁的导师施一公也曾说过“我直到博士毕业,对研究也没兴趣,对未来很迷茫,也不知道将来要干什么”。但当合适的工具出现时,他就能开创一个研究领域,无论你是否喜欢他的解决方式。这源自天赋,更在于机遇,是规划不出来的。
因此,向一个本科生问他科研的终局目标,无论回答的浮夸或是真诚,都不太能代表他最终会走出的路径。其实面试一直都不是个很好的考察方式,只有多视角的track record才是未来最可靠的指示灯。遗憾的是,科学界的这些“文化建构”的习惯,往往也没那么科学。
而在即将到来的AI未来中,大模型将会给我们绘好所有科学可能性的路书,就像蛋白质折叠算法对结构生物学”地图全开”那样的降维打击。这种时候什么领域的“战略科学家”都是没有太大意义的,算法的架构师真正需要的是一些出乎意料的的现象数据,在模型之外引进“变量”。
而在这个新的范式下,科学更需要的不是什么全新的想法,而是在物理世界里一遍遍测晶体的年轻颜宁。
本文系凤凰网评论部特约原创稿件,仅代表作者立场。
编辑|刘军
(本文章版权归凤凰网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为您推荐
算法反馈天下事
天下事
精品有声
热门文章
精彩视频

凤凰资讯官方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