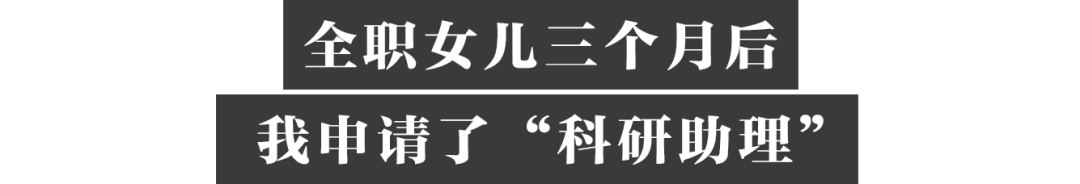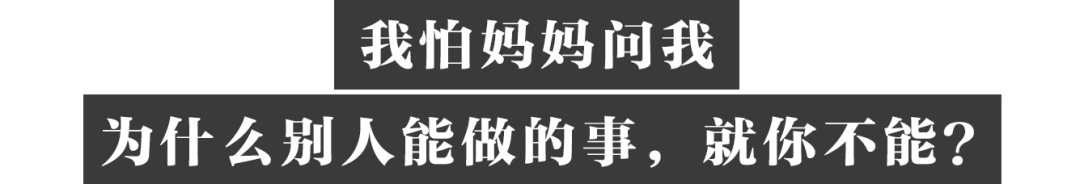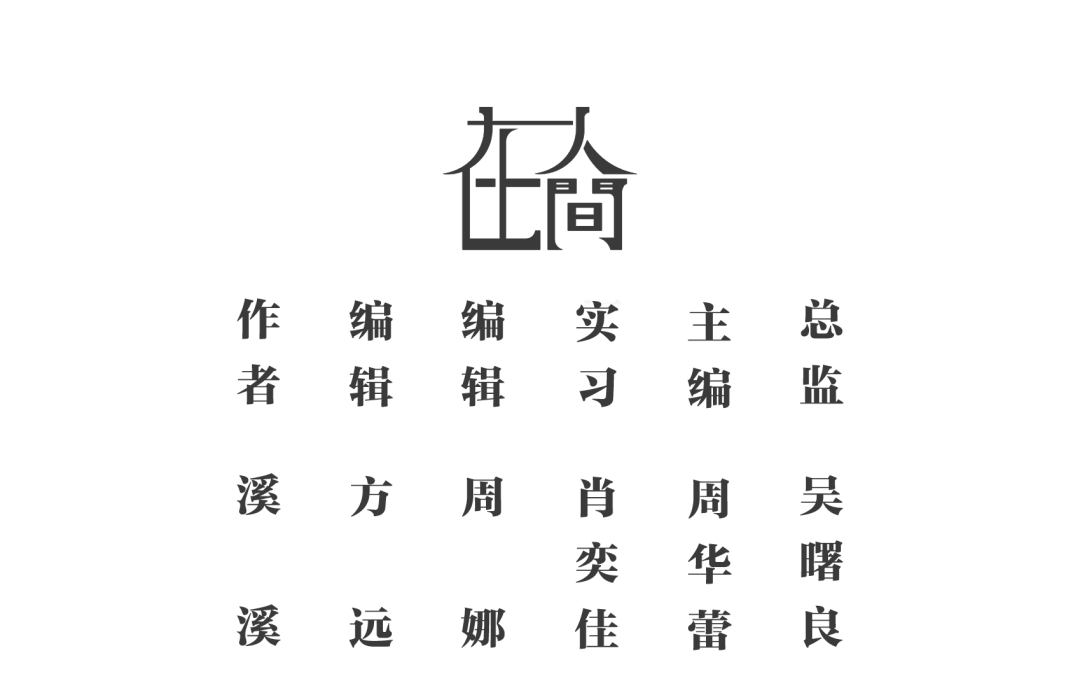在人间|我,科研助理,刚毕业被学校“收养”


独家抢先看
撰文| 溪溪 编辑|方远 周娜
高校文职摸鱼岗,每周3天工作,4天放假。"还没落实毕业去向的同学可以重点注意。"
我们在大学“上班”,没有固定办公室,只是围坐在一个会议室里。时不时有老师来开会,我们便轻车熟路带上自己的行头,去楼梯间的沙发坐着等待。大多数时候,我们并不真的工作,而是为考研、找工作、申请学校做准备,有人在雅思或考研的书上飞快做笔记,有人戴着耳机专注盯着屏幕上网课。
我们都是 2022 年的毕业生,我们的身份叫“科研助理”。月薪4000-5500元,每周工作三天,其他时间自行安排。这像是学校给我们的一段带薪 gap year。
依照学界传统,科研助理一般受雇于教授或课题组,辅助完成科研项目,许多有志于学术界的学生会把它当作从硕士到博士阶段的跳板;
但我们这种“科研助理”,更像是被安插在各个学院与部门的短期行政岗。这是愈发严峻的就业形势之下诞生的一个政策性岗位——用来缓解毕业生就业难题的。
过去一年,我顶着这个title出入学校的行政楼,直到2023年毕业季到来。
2022 年 6 月,研究生毕业前夕。陆续听说同学拿到各种offer时,各种想法还在我的脑海打架:到底是找一份坐班的工作,还是赴海外读博?
当辅导员第一次发出那个文件——《2022科研助理岗位招聘启事》,我并没有太在意。毕业的班级群里每天都有几十条招聘信息,这条很快被淹没了。过了几天,辅导员再次转发了它,特别强调:
还没落实毕业去向的同学可以重点注意。
有天我凌晨两点还是翻来覆去睡不着,突然想起了这条通知。
文件里写到,科研助理的工作内容是科研辅助、教学辅助和管理辅助。工资是本科学历 4000 元/月,研究生学历 5500 元/月。协议的适用期限一年,中途可以随时解约。
这样的科研助理并非新生岗位。早在 2009 年,科技部、教育部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鼓励科研项目单位吸纳和稳定高校毕业生就业的若干意见》,首次提出聘用高校毕业生作为研究助理参与研究工作。2020 年 4 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更明确提出“研究科研项目吸纳毕业生计划,开发 10 万个科研助理岗位”。2021 年起,我所在的大学也开设了这个岗位。
我想,这份工作听起来挺不错。
虽然没有五险一金,不交社保,但这也意味着可以保留应届生的身份——我们深谙应届生身份的宝贵,无论考公还是名企校招,都有许多职位限定应届生报考,一些城市还有专门的应届生落户政策。
虽然这也算不上高薪——刨去房租,剩下的可能还不够生活费。但是每周只需工作24小时,我有大把剩下的时间用来准备申请材料或找工作。
第二天早上,我跟妈妈提起这个岗位,她表现得非常激动。我知道,虽然她有时宽慰我暂时找不到工作没关系,其实心里非常焦虑。
在小城市做高中老师的妈妈生活圈子并不大,同事中哪个孩子去哪里做了什么工作,不到半天就可以传遍整个学校。她每天下班回家向我更新:朋友的儿子凭机器人比赛进了大疆、同学的女儿在华为做到了管理层……爱面子的她承受着很大的社交压力。作为单亲母亲,她几乎是独自照顾我,我猜她很想让我“出人头地”,在那个男人那里证明自己。
而在家待了两三个月后,我和妈妈的吵架频率越来越高,我也有点想逃离家里紧张的气氛。于是我提交了科研助理的报名申请。
筛选的过程并不复杂,只有面试环节。过了一两周,我被通知入选了。后来,我才从人事处的老师那里得知,原来录取率是几乎百分之百,我们这一届招收了 140 人左右。
他说因为大家找不到工作已经很挫败了,学校不想让大家再受一次打击。
140 名科研助理被分到各个学院与行政部门。我被分配到人事处,一共六个科研助理。
除了周一到周三工作,每周我有四天假期。我决定继续探索很感兴趣的性别研究,并开启“疯狂看论文”状态,上班路上坐地铁也会掏出 iPad 看。我通过各种渠道搜寻导师,读文献,再一封封地写邮件“套瓷”。我的目标是申请全奖或是岗位制的PhD。
但偶尔,肌肉记忆似的,我也会时不时点开招聘app和公众号,去看看编辑或运营的工作,下意识把自己往岗位要求里套。
我一般九点到学校,边吃麦当劳早餐边查邮箱,开始准备研究计划。办公室一般是沉默的,一个同学着数学书,另一个看雅思课,还有一位总在处理excel表格,后来才知道,这是她的另一份远程工作。
大多数时候老师对我们表示理解,不会派太多任务给我们。
和我同期入职的音音自认为比较幸运,她被分派到自己本科就读的计算机学院,老师们知道她要考研,并不要求坐班。她和室友在学校附近租了一个房间,房租对半开,一个月 1800 元,还算可以承受。她每天八点左右抵达图书馆开始复习,如果学院有工作,她就赶到办公室,干完活之后回来接着复习。
这些工作以行政类居多,比如给新生介绍入党流程、组织学生党支部开党会、写材料等。今年年初,考研结果公布,她被调剂去了西北一所科技类大学的计算机专业,申请了提前离职。
人事处的科研助理偶尔也有一些来自学校的任务,比如:我们花了差不多两周,把一整筐全校老师的考勤表按照时间顺序排列,文件大概有两三千份,老师的入职时间从80年代到2022年。这个工作不难,但是很费时间,我们几个科研助理把会议室门关起来,边听摇滚边聊天边整理。不过我们得小心控制音量,不然被一墙之隔的老师们听见了,多少还是有点难为情。
并不是每个部门的老师都理解这个岗位的政策属性。商贸专业的小圈被派到了财务处,她打算利用这一年来申请海外的硕士项目,但是她觉得繁重的工作让她没有足够的学习时间。“每天基本上都有干不完的活。负责管理我的老师会把我去厕所的时间精确到分钟扣掉”。
小圈认为这个工作的性质是为了方便毕业生们更好地找工作和升学,而财务处的职工坚持“拿钱干活是天经地义”。
后来小圈和财务处的领导爆发了激烈争吵,她被调到了人事处。
“其实每年都有这个问题。”学校人事处的干部王俊说,“有的学生会觉得我来这儿不是来工作的,但有的单位会觉得,你怎么能一点活都不干?”
还有一些部门从一开始就抵触科研助理的设置。“他们担心科研助理刚来,给你培养好你就走了,不敢把一些长期复杂的工作交付。”王俊说。因为协议的灵活性,科研助理可以随时离职,就算不中途离开,最多也只能服务所在部门一年。
有时候,科研助理们也会闲聊。保研、考公、出国……大家的规划大同小异,好像是有那么几条既定的轨道,但是大家都在某个地方“掉了链子”,没能成功挤上去,所以聚集在这里,度过一段类似于 gap year 的时光。
当科研助理期间,我在找工作上已基本“躺平”;几位同事在我看来已经非常努力了,还是没能在毕业时确定去向。好像在面对一个抛球机,手忙脚乱地想接住一个又错过了另一个。
黄西是英语专业硕士——我们学校的王牌专业,她本来对自己的求职状况很乐观。
她的首要目标是公务员,报考了 2021 年国家公务员考试,这个考试在 11 月底,报录比是 60:1 左右,为了战胜其余的 59 人,黄西把几乎所有精力都花在备考上,还是落榜了。于是她放低目标,开始物色国企和事业单位,因为此前忙于准备国考,她错过了秋招的黄金时期,很多岗位已经关闭。
她投了一两百封简历,颗粒无收。
黄西觉得,班上的就业情况不乐观,和国际形势也有关系。各行各业在国际业务减少的情况下,对英语专业的需求也会下滑。于是毕业前夕她再次降低要求,开始应聘本来完全不在考量范围内的外企和银行。为了保证在北京找工作时一定的经济来源,她报名了科研助理。
小山是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在毕业前的春天开始应聘小学老师的岗位,因为应届生的身份,她可以免笔试,直接进入面试环节。但直到毕业,她都没有找到心仪的工作,父母给小山的压力越来越大,她觉得科研助理是个逃离家里压力的机会。
在北京,她一边做科研助理,一边在另一所大学的继续教育学院做助教,是临时工的形式,工资是一天两百。工作繁重、通勤也远,她一度想要辞职,但是继续教育学院的老师允诺如果招聘正式员工,首先考虑她。她咬咬牙坚持了下来。
如果说黄西和小山还在努力跻身主流轨道上的列车,丁芽则算是在站台徘徊的人。由于“二本三跨”(指本科毕业于二本院校,跨地区、跨院校和跨学科考研)出身,加上读研期间并没有很丰富的实践经历,她感觉自己“从根本上就差了些东西”,加上内向的性格,她总是无法轻松自如地面对面试。
春招的时候,有个同门每天在小红书上分享自己投简历、笔试和面试的经历,复盘自己的表现。丁芽发现那个同门投了一百多份简历,暗自惊叹,评论说:“你好努力。”同门回复:“真的很怕找不到工作。”
一阵焦虑爬过丁芽的心头。
迫于就业压力,她逼迫自己去考了一次军队文职,竟然一路进入体检环节,本来觉得这个工作已经十拿九稳,却被通知是差额体检,所以最后也是陪跑。
就像校人事处的干部千山说的,“很多孩子已经非常努力、非常优秀了”,但还是找不到工作,于是怀疑自己,甚至陷入了抑郁情绪。面对这样大范围的的就业困境,很难把问题归结到个人身上。但压力却是由一个个个体实实在在地承受着。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已经是享受到有限资源的幸运的少数人了。在更广阔的二、三本、专科学校,还有那些没有机会成为“应届生”的、受教育机会更少的年轻人们,他们的命运更加难以想象。
3月春招时,我也递过几封大厂的简历,笔试环节有很多我完全摸不到头绪的数学题——这是我高考后没再接触过的东西。后来我才得知笔试题也是需要备考和刷题的。
面试环节也让我紧张。记得找实习时线上面试一个大厂,是一个负责公益寻人项目的部门,岗位是运营类。我既有公益项目的经历,也有运营类工作的经历,算是比较对口。我提前调研了相关的业务,在面试时表现得不错。
直到面试的尾声,对方突然问我:“你能接受加班吗?”彼时我的本能反应是抗拒的,于是我犹豫了几秒,说:“要看具体是什么样的加班,如有突发状况偶尔加班是可以的”。
后来看小红书上的面试攻略,原来我这样的回答是“踩雷回答”;这种时候应该坚定地回答可以加班,才能让 HR满意。
而我曾经的一份实习经历,也让我对进入互联网大厂很抗拒。研究生一年级时,我应聘上一个互联网公司的运营实习生岗位,所在的部门负责一个非虚构文学类的公众号。我经常看这个公众号,所以看到招聘信息就马上投了简历。
面试我的员工问我喜欢哪个作家,我说阿列克耶维奇,她说她也喜欢,随后我们聊了二十分钟阿列克耶维奇的作品。接到offer的时候我很开心。
但是入职后,我得到了一份几十页的共享文档,里面是排版和发布操作手册,我的工作是依据这个手册,把每一篇文章,按照段落复制粘贴进一个专门的网站,然后把图片插入事先设计好的位置,再把文章发送到相应的栏目。连按哪几个网页按钮都是设定好的。
这里的领导人很好,公司的免费食堂也不错。但是每个工作日,我坐在办公室一整天,只做几乎完全是复制粘贴的工作。虽然身体不累,也不用思考,但是感觉精力还是被榨干了。
在开始这份实习之前,我差不多每天看一部电影、每两天去一次健身房,但实习时,每天回到宿舍的我只能麻木地瘫倒在床上刷小视频。实习了五天后,我提出离职。
当然我没有把这段经历告诉妈妈,我怕她问我:“为什么别人能做,你不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别人能做到,但是我就是做不到。
妈妈也想让我考公务员或是做老师,但我从小就是一个“不会来事”的孩子。被带去参加酒局,妈妈朋友的孩子会举起酒杯对每一个叔叔阿姨说祝酒词,而我只会像大脑短路一样把头埋在桌底,或者露出僵硬的傻笑。
长大之后,这个局面也没有改善,我很难适应一些在大家看来很容易的规则,大学选课的时候,很多同学会特地打听什么样的课好拿分,甚至在校内的信息平台上交易这些好拿分的课,而我选课几乎全凭兴趣。还记得有一门花卉学,老师上课的时候会带我们走出教室,去学校的花园里教我们分辨樱花和桃花,桃花一般是单朵生长的,而樱花是团簇状开放。
大三的时候,听说有同学为了保研特意去献血拿证书、在淘宝上找人代刷网课,我才想起来去翻翻学生手册,看保研的标准是什么。我几乎是班上的“边缘人”,唯一主动参加的集体活动是和电影社团的朋友一起放电影,看些不着边际的文艺片。对我来说,做公务员或老师的挑战性不亚于在大厂做运营。
晚上在家附近的胡同散步时,我经常经过一个院子,一边是彩票站,一边是酒吧,经常有喝大的年轻人在院门口玩刮刮乐,一张接一张地刮,兴奋地大叫着,看起来无忧无虑。
有时我也会穿过这些年轻人,去彩票站买一张刮刮乐。偶尔会刮到“再来一次”。没人能保证再来一次的结果是什么,但至少新的机会能带来新的希望。
科研助理有点像我们人生的“再来一次”。
我们普遍觉得从科研助理这个政策中受益了,虽说工作层面上能力也许没得到太大锻炼,但是不算太少的报酬,给大家在北京的生活提供了经济支撑,工作时间上的自由度,让我们能专注于自己的人生规划。
目前,科研助理一年的协议时间即将结束,第二次刮奖的结果也逐渐揭晓:黄西拿到了一份外企的 offer,将在9月入职;小山还继续在那所高校兼职,期待能有一个转正的机会;音音则即将在 8 月读研,开始新的学习阶段;小圈拿到了一所美国理想学校的硕士 offer。而丁芽还在迷茫,短期内,她想再在北京留一段时间,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工作,同时暂且逃离来自家里的催婚压力,和小城生活的鸡毛蒜皮。
至于我,可能要让妈妈失望了。
我知道,她在跟同事聊天时,会语焉不详地说我在学校工作,但并不会说明这份工作的性质和短暂的有效期。一年即将过去,我还是没能找到一份“稳定又体面”的工作。
但我也不准备回应她所有的期待。在这一年里,我完成了博士申请的研究计划,联系到几个博导,但只有一个学校有五个全奖名额,我第七名,进了waiting list 。
我现在不那么急了。我最开始想读博,除了对学术的热情,也有一部分是急于想逃离求职的压力。但过了一年,我觉得找到合拍的导师更重要。
这一年里,我进行了一些女性主义的文字创作,链接到了一些女性主义的社群和媒体。虽然这些经历并不能直接帮助我申请,但我渐渐明白,申请PhD不是目的本身,申请的过程、这些文字创作与社群链接,都是我探索自己和探索世界的方式。
我向来不大能感受到朋辈压力,因为我打心底里没有把自己嵌入那一套价值坐标。我不打算出于“到了什么年纪就应该 xx”的理由做任何事,结婚、买房、生孩子都不在我的人生清单上。所以我目前不需要户口、也不需要那么多钱。我用体验和探索的心态对待我的人生,而非比赛,我不想往上爬、也不想战胜任何人。借用一个朋友的比喻,我希望我的人生是坐车,看到好玩的风景就下来转转,玩腻了就继续去新的目的地。
最近,我移居到了离北京不远、有“睡城”之称的河北城市,这里物价很低,我和朋友合租了人均 800、有很大窗户的房间。大多数时候不务正业,看闲书、拍照、去河边看云彩、做尚未盈利的街头艺术公众号,偶尔也写稿赚取一些稿费。我准备在这里过完夏天,然后去探索云南的数字游民社区,同时做一些艺术项目。
我卸载了 boss 直聘、不再点开招聘类的公众号,至少是暂时地,我背过身离开了那条轨道。在新的房间,我睡了几个在找工作时从未有过的好觉。
* 文中提及的同学和学校职工皆为化名。本文头图源自《请回答1988》,文章配图由作者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