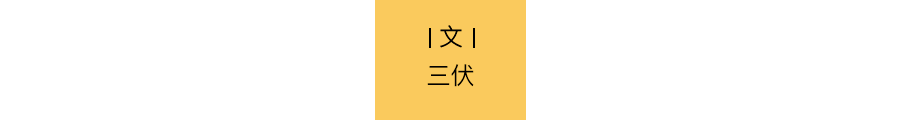他跳楼自杀,但故事没有结束


独家抢先看
2014年,一颗螺丝落在地上,许立志一跃而下。
跳楼自杀后,他成了名人。他的诗集被众筹发表,翻译成多种语言广泛传播,有关他的纪录片《我的诗篇》拿下国际大奖。
但去世之前,许立志只是几亿农民工中,再普通不过的一个。
流水线、螺丝钉、铁做的月亮,拼凑出他的生活。他无法与命运握手言和,只能咽下滚烫的愤怒。
他将苦楚诉诸于诗歌,把川端康成、太宰治和三岛由纪夫视作好友。在日复一日的挣扎中,他写下死亡。
一颗螺丝掉在地上
在这个加班的夜晚
垂直降落,轻轻一响
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就像在此之前
某个相同的夜晚
有个人掉在地上
——许立志《一颗螺丝掉在地上》
某种意义上,许立志还活着。
2014年10月1日,他去世的第二天,一条事先设置的微博定时发出。这是他写的最后一首诗,内容是:新的一天。
9年时间过去,每天依旧有人来这里报到。人们没有忘记这位“打工诗人”。
许立志微博下截图
工人、诗人,两种身份交织在许立志的身上,让他的灵魂发出强烈的战栗。他对工厂生活负隅顽抗,转身在纸上写下凌厉的句子。
死亡,则将他的名声推向了更高峰。他的生命终结在24岁,短暂,刺骨,令人哀惋。
可回头去看,悲剧的到来并不突然。
许立志
翻阅许立志微博里的1000条记录,他人生的终场清晰展开。
2011年2月,21岁的他进入富士康——彼时世界最大的电子产品生产商,更为知名的是苹果公司最大的代工厂。
许立志是深圳富士康的一名普工,试用期9个月,每月薪资1700元,转正后2300元。
上班的第一天,许立志轮到了夜班。夜班的出勤时间是晚上8点到早上5点,若加班延长到7点。第二天,他开始加班。他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其实忙也很好,不必想太多不该想的”。
那时,他也不会想到,自己会在两年之后写下《夜班》这一首诗,字里行间流淌着血泪。
我几乎是爬着到达车间
这昼夜不分的刑场
夜色中我打开体内的白炽灯,这咳嗽的霓虹
照亮机台黝黑的内脏,再划破血管
上班第三个月,他找到了一家图书馆,大喜过望,“于是在接下来的每一天,我都为自己找到了活下去的理由”。
他痴迷于书籍。他记录下自己的购书单、摘抄的读书笔记以及许多条读后感,这些书来自书城和网上商店,也有的来自地摊,十块钱买了三本。
还有账本。“十二月开销2131.5元,比上月多花了598.7,应是书与衣服的缘故。”
流水线上安放不下的青春,被一页页书承托着,转化成一行行喷涌的诗歌。
许立志出租屋中留下的书籍
2011年春天,许立志开始给刊物寄出自己的作品,他写道:“已发出去,信心十足”。
7月份,一位编辑给他发来回复,说主编把他的诗撤了,理由是太昏暗。
秋天,他的4首诗被发表在一本叫做《打工诗人》的民间刊物上,一个月后,他接到了一通电话,邀请他去惠州参加创刊十年的纪念诗会。
主编罗德远还记得这次与许立志的相见,还记得那是一个腼腆的年轻人,长得精瘦,身高175cm左右,脸上还有青春痘。
“他给我打电话,说请到假了,高兴得不得了。”罗德远回忆,在诗会上,许立志朗诵了一首诗,顾城的《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
许立志微博中提到顾城
参加完诗会,许立志买了一本《写稿赚钱18技》,他的微博也多了些踌躇满志。“再一次看到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那种自豪感和满足感是多少金钱都买不到的。旅程才刚刚开始。”
2012年开始,他在厂刊《富士康人》上发表自己的作品,也被冠上“打工诗歌接班人”的头衔,他在微博上写下“改变”的字眼,但一切都没有改变。
三年时间,他从作业员变成仓管,又变成了线长。他的左手用作白班,右手给了夜班,蓬勃的灵魂被标准作业指导书死死禁锢。许立志站成了流水线上的兵马俑。
车间,流水线,机台,上岗证,加班,薪水……
我被它们治得服服贴贴
我不会呐喊,不会反抗
不会控诉,不会埋怨
只默默地承受着疲惫
流水线旁我站立如铁,双手如飞
多少白天,多少黑夜
我就那样,站着入睡
2012年的春天,他和一位姓高的诗人吃了顿饭。饭桌上,许立志对高抱怨了压抑的工作和无从安置的未来,高说:“立志知道他手里握的应该是钢笔,而不是锤子”。
灵魂似乎就是这样一片片被撕碎的。
我谈到血,也是出于无奈
我也想谈谈风花雪月
谈谈前朝的历史,酒中的诗词
可现实让我只能谈到血
血源自火柴盒般的出租屋
这里狭窄,逼仄,终年不见天日
挤压着打工仔打工妹
失足妇女异地丈夫
卖麻辣烫的四川小伙
摆地滩的河南老人
以及白天为生活而奔波
黑夜里睁着眼睛写诗的我
许立志
2011年,许立志刚来工厂不久,他写:“最近嗜睡严重,一躺床上就没了知觉。”那时,他身体疲惫,但灵魂尚且完好。
但时间线走到2014年,“嗜睡”变成了“失眠”,内心在不断发炎、溃烂:
失眠是一坛陈年佳酿,怎么尝也尝不够;
失眠的夜晚冰冷的生命整夜燃烧;
夜宵是失眠者的早餐……
他说自己的好朋友川端康成、太宰治、三岛由纪夫——均是以自杀结束生命的作家,对他迟迟没有赴约表达不满。“我说一直要去的,就是订不到票,你们再等等,他们就都不理我了”,许立志写。
他还写樋口一叶,这位已经逝世多年的日本女作家给他打来电话。许立志问她,这些年你都去哪里了?樋口一叶说自己也不知道,但这里很舒坦,“保证你喜欢”。
他在微博里提到抑郁症,也似乎得了厌食症。他越来越擅长写墓地、写鲜血、写亡灵与死亡。
每个夜晚
当我躲在窗帘后面
偷窥树梢吊着的
通红的月亮
我都在犹豫
是否也要
把自己的头颅
拧下来
吊在窗台上
2014年8月8日,他写下一行文字:“秋天了,请把我埋好。”
8月11日,他为自己挑好了葬礼上的背景音乐,是久石让所作的《入殓师》的主题曲。
这期间,他还挣扎了一瞬,在9月27日,他写:“不要给自己施加太大压力,不要压垮自己……只要命还在,阳光总会到来。”
9月30日,他乘坐电梯抵达一座大厦的17层。他站在窗口眺望了5分钟,然后爬上去,跳了下来。
一颗螺丝掉在地上,垂直降落,震耳欲聋。
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
他们管它叫做螺丝
我咽下这工业的废水,失业的订单
那些低于机台的青春早早夭亡
我咽下奔波,咽下流离失所
咽下人行天桥,咽下长满水锈的生活
我再咽不下了
所有我曾经咽下的现在都从喉咙汹涌而出
在祖国的领土上铺成一首
耻辱的诗
——许立志《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
许立志去世后,诗歌评论家秦晓宇推开了出租屋的门。
这是他最后居住过的地方,一个十平米左右的单间。每个月房租350元,水费电费路灯费加起来还要37元,许立志在诗里描写过这个逼仄潮湿的房间。
每当我打开窗户或者柴门
我都像一位死者
把棺材盖,缓缓推开
许立志的出租屋
秦晓宇小心翼翼收拾着这个房间。一张床,一把塑料椅子,一个书桌。他还有一个帆布材质的蓝色衣柜,最上层塞满了书籍。
“他在顾城和海子的诗集上划线,十有八九的句子都和死亡有关。”
但这些文学的碎片,许立志的家人浑然不知。
许立志的衣柜
有记者采访过许立志,问家里人是否知道他在写诗,许立志否认:“没有让他们知道。一方面他们可能也不是很理解,另一方面,有时候你里面写了一些苦的东西,被他们看见也不好。”
他的预想十分精准。
许立志的哥哥说,每次打电话回家,许立志都闭口不提痛苦。当时富士康陷入跳楼丑闻,家里人也劝过他:“如果压力太大就不要在那里干了。”
许立志回答:“没事,各方面还行。”
他选择在微博上写下当时的内心独白:“每次在给家里打电话之前都会犹豫一番,因知道打完后必定心情沉重,想到年迈的父母,想到拮据的经济,想到碌碌无为的自己,想到未来的漫长的日子……”
从左到右:许立志的哥哥、母亲、父亲
报喜不报忧的性格,在他成长的过程中就有迹可循。
1990年,许立志出生在广东揭阳的东寮村,家中弟兄三个,他是最小的一个。
他从小就喜欢读书,小学时的阅读量就超过了五百本课外书。中学时,他在玉湖中学就读,成绩名列前茅。
但在乡村中学,成绩不代表一切。许立志的班主任曾说,仅许立志同届的学生就有五十多人退学。退学的人都去打工了。
许立志仍在坚持。中考时,他以全班第一的成绩毕业,但离县重点高中还有十几分的差距,家里掏不出借读费。
于是,他继续在玉湖中学高中部就读。到了高考,他落榜了。
父亲轻易地接受了他的失败,他始终不赞成孩子读大学,“不可能考上名牌大学,一般大学读出来也没有出路”。
许立志小学时的作业本
高考后,家里人劝许立志出去打工,要挣出来盖房子的钱,娶媳妇用。家里儿子多,要盖三间房子。许立志别无选择。
母亲形容许立志是一个内向懂事的孩子:“我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很乖,很听话。”
可在2014年春节,乖巧的许立志却突然辞掉了富士康的工作,没有告诉家里人。
3月份,他回了老家一趟,给了父亲2000块钱。家里用这笔钱给许立志盖了结婚用的房子,还差2000元。这也是父亲最后一次见到许立志。
父亲还记得,许立志曾和他说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在广州读书的大学生,但女生家里不同意。“证实了他在社会上没地位没钱。”父亲认为。
至于写诗的成就,在父亲看来也并不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
“在我的印象中,现在写诗好像就没什么出路,比起这些搞科技的、搞发明创造的,相比较这个价值就差得很多。”
许立志去世之后,父亲翻阅了他的诗,觉得里面充斥了太多负面的情绪。
“他的思想落得这么消极,是很对不住父母的。他内心的痛苦,没有人给他解开,这也是没有办法。至于他的诗是好是坏,我们水平不到也不知道。”
当然,这是后话了。
辞工的这段时间,许立志给深圳市中心书城写了一封自荐信,里面罗列了自己的作品。
在这封信里,他写道:“我羡慕所有在书城上班的人,他们可以在书海里畅游,时常能见到来书城做活动的著名作家,获得更好的学习机会。”
但他没有得到这个机会,许立志似乎认命了。9月26日,他回到富士康,签了一份月薪1900元的新合同。
就在许立志回到工厂的一个月前,秦晓宇计划拍摄一部纪录片,聚焦在“打工诗人”这一群体。
如果说背井离乡是打工者的常态,艰苦朴素是被人追捧的品格,那么,诗人们笔下的每一道血痕与呐喊,都是不可忽视的时代所发出的声音。
他邀请了十位诗人,这其中,许立志是他计划里“纪录片最重要的角色之一”。
2014年8月底,许立志给秦晓宇发来消息,拒绝了他的邀请,他也是所有诗人中唯一拒绝邀请的人。
他告诉秦晓宇:“我不写诗了。”
我。抽出一把刀,砍断河水
她不说痛。
她没落下伤疤
以至于我产生了恨意
家乡的河水实在太柔软了,以至于每碰到一粒砂子
便绕道走开
河水实在是太干净了
镜子养育的鱼虾,十八年还是那么瘦小
而。叛徒已经长大
——郭金牛《重金属》
打工的这些年,许立志写下了195首诗。
秦晓宇整理完他的诗篇,发现许立志虽偏爱“死亡”主题,却也写过不少有关爱情、梦想以及乡愁的句子。
任凭那弯弯的月亮
一次次地
把我瘦瘦的乡愁
割出血来
乡愁,是打工者无力躲避的情感。“农民工”一词的背后,是逃离凋敝的乡村,是冷硬陌生的城市,是乡愁被悬置,灯火万盏,异乡人饮醉故乡。
嘉兴的充绒工吉克阿优,就徘徊在这个主题下。
故乡很远,我在一碗粥里
只搅出几声方言
于是没有放盐
他是彝族人,老家在四川大凉山。彼时,大凉山还没有被直播的喧嚣侵袭,有的只是贫困、闭塞和颓圮的老屋。
在外打工7年,阿优第一次带儿子回了老家,去过彝年——彝族的传统节日。
围在故乡的灶台前,阿优和妹妹们聊天。一个妹妹说:“出去打工的话就心疼父母,想到自己一走就不能帮父母干农活了。但是看到朋友们打工回来,衣服很漂亮,钱也挣回来了,感觉自己很不争气,挺窝囊的。”
城市的发展挤压着古典的乡村,这个原本有着56户人家的寨子,如今剩下不足20户,多是老人和孩子。
阿优感到荒凉:“自己不去保护自己的文化,跟着潮流走,慢慢地,自己民族的文化就没有了。”
阿优家族合照
祭祀结束后,阿优和父亲坐在火堆前,他告诉父亲如果没钱就打电话,“我们也没有多少工资,但还可以省下一点”。
明灭的火光映在父亲沟壑纵横的脸上,父亲开口,没有提钱。他只说:“我的黑头巾,我已经缠好了,等我死了,你们就可以直接戴在我头上了。”
吉克阿优不说话,他拿起面前火堆里还未燃尽的树枝,摔打着,摔出无奈的火星。
过完年,他又坐上了长途客车。
好些年了,我比一片羽毛更飘荡
从大凉山到嘉兴,我在羽绒服厂填着鸭毛
我被换作“鸭头”时遗失了那部《指路经》
阿优(左)和父亲
土掌房成为歇脚地,更多的时候,这个彝族小伙被关在车间的阳光房里充绒。那是被称为车间最艰苦的地方,绒毛纷飞,还有难闻的气味,“领导检查都不愿意来这里”。
他试图用纸笔记录下工厂的日常,把罚款、愤怒、无法被剪去的野心都藏进诗里,再藏到鸭绒中。
有一天,他写了一首《工厂的夜有些黑》,这首诗发表在了《打工诗人》杂志上,被生产部的领导看见。
领导把阿优叫到办公室,对他说:“其实每个工厂的夜晚都是这么黑”。阿优反问他,你懂不懂诗?
工作因此变得艰难,比如在2011年弄坏的那条皮带,两年之后,他收到了赔偿通知。
阿优并不意外:“只有在诗里,我才活得人模人样。”
那是2014年。
阿优在充绒
我不会诉说我的苦难
就让它们烂在泥土里
培植爱的花朵
——邬霞《我不是没有想到过死亡》
2014年,32岁的邬霞在深圳一家服装厂打工。打工对她来说,是命运的轮转。
邬霞的父母是第一代外出打工者,邬霞是第一代留守儿童。
邬霞
邬霞的老家在四川内江,7岁时,父母去往深圳打工,她和妹妹被留在了四川。
后来邬霞初中辍学,被带到了深圳。那时她14岁,工资是600块左右。
邬霞很不快乐,每天郁郁寡欢。刚到包装车间工作不久,她就加班到了凌晨四五点,周围有女孩边干边哭:“妈妈呀,妈妈呀,我的妈妈睡得很香,不知道女儿在加班受苦!”
邬霞不敢哭。她的妈妈就站在距离她不到5米的流水线上,她不想让妈妈难过。
邬霞在车间
不仅是身体上的劳累,精神上的折辱更让她难以忍受。
彼时邬霞在一家日资服装厂工作,有一天,她坐在一个坐桶上剪线头,突然坐桶被狠狠踢了一脚。她转过头,看到了厂里的男翻译,对方面无表情,觉得她挡了道。
邬霞记录下自己的眼泪,4年时间哭了200多次。她还试图自杀,一只脚跨过了窗沿,被母亲拉了回来。
写作,成为了她宣泄的一个出口。
刚开始,她写言情小说。躲在昏暗的、恶臭的厕所里,她写俊男靓女的爱情故事,男女主都是有钱人,爱情的结局甜蜜美满。与她截然不同。
邬霞的丈夫是个赌鬼。
2009年,27岁的邬霞经人介绍认识了那个男人。男人是包工程的,两个人都穷,邬霞本觉得无所谓。
没过多久,她意外怀孕,男人问父亲借了钱,带她去打了胎。又过了一段时间,她再次怀孕,邬霞决定结婚。
也就是在跟男人回老家办结婚证的时候,邬霞听见男人对老乡说“打牌输了十几万”。但她已经来不及后悔了。
预产期那天,邬霞想去医院,男人以“还没发动”为由拒绝。第二天邬霞开始阵痛,疼到必须弯下腰身,男人说:“吃了饭再去。”
某一年春节,邬霞陪男人回老家。在大巴车上,邬霞因男人出轨哭泣,男人被吵醒,众目睽睽之下猛扇邬霞的耳光,她的嘴巴被扇肿,“当时车上没有一位乘客站出来劝阻”。
直到邬霞怀了二胎,男人威胁她“生不出儿子就不要你”,产后,邬霞抱着小女儿,毅然决然离了婚。
生活没有给她一颗糖,但在邬霞的作品中,人们却很难看到绝望。
邬霞最知名的作品是那首《吊带裙》,那是她最喜欢的衣服。
在她的衣柜里,塞满了五颜六色的吊带裙。有的是在市场买的,25块钱;有的在地摊上,20块钱。
裙子已经破旧,裙角也走了线,但她依旧不舍得扔,“因为买了一件衣服,你就对它有感情了”。
邬霞《吊带裙》
她其实很少有穿吊带裙的机会。
上工时,她要穿工装,肥肥大大的,只能等晚上加班之后,工友们都睡着了,再在床上偷偷换好裙子,穿过走廊,跑到洗手间。
凌晨三两点,洗手间里有一扇窗户,她把窗户当作镜子,旋转裙摆。“只有几分钟,可以感受到穿裙子的快乐。”
那些年,她写小说、散文,觉得还是诗歌最能抵达人的灵魂。她说:“我希望别人看到我的诗歌,能感受到美好。”
现如今,她依旧租住在深圳宝安区的城中村里,父亲在2019年突发脑出血,孩子因为没有户口只能在民办学校就读。
房子很小,她和两个女儿睡在一张床上。前夫早已经不管她们,连微薄的赡养费也不再支付。
疫情期间,孩子在家上网课,邬霞就做起了网络写手,一个月能赚4000多块钱。
为了让孩子摆脱像自己一般漂泊的命运,邬霞在这段期间拿到了自考大专文凭,还准备了中级职称考试——为了拿到深圳的户口。
邬霞与女儿
2022年7月份,一位服装设计师找到了邬霞,为她设计了一款吊带裙。
设计师的朋友记录下了整个过程。她们见到了邬霞,看到一家五口为了省空调费挤在一间小小的卧室里。
她们穿着吊带裙在海边拍了照片,邬霞一直在笑。
她最后写道:阳光或许不会晒到每个人的身上,但每个人都有照到太阳的机会。
2022年的邬霞
活着,就是冲天一喊
真情和真理,皆在民间
——陈年喜《秦腔》
可惜黑暗,才是陈年喜的伙伴。
矿洞就像是迷宫,千万米的深邃巷道中,布满了子洞、天井、斜井、空釆场。陈年喜是爆破工,与死神的关系最为亲密。
爆破的工作是从1999年开始的,写作的时间则更长,要追溯到80年代。
初中时,陈年喜就曾向《萌芽》杂志投稿,高中后开始写诗,发表了几篇,稿费不超过10块钱。
1999年,陈年喜的儿子出生,写诗不能填平肉体的饥饿,他随着大流,来到了矿山。
陈年喜
矿山深远,他沿着山脉前行,最长的时候,他要在山里住半个月,与世隔绝。
在河南灵宝,他与其他两位爆破工一起从矿洞的天井上下去,后面的人无意间踩下一块石头,石头滚落,砸破了前面人的脑袋——尽管佩戴着安全帽。死神来得很快。
他的妻弟也是爆破工,在某次炸药炸响前跑错了方向,代价是粉身碎骨。陈年喜为他处理了后事。
十几年爆破生活中,风钻使陈年喜的耳朵失聪了大半,好在,写字的双手完好无缺。
陈年喜在爆破过程中
矿上的活太累,空闲的时间只够写诗。山里也没有纸,他就写在烟盒的背面,或者雷管的说明书上。
那些年,他写了七八百首诗,很少投稿。
一夜成名的美梦不适合这个秦岭汉子。父亲常年瘫痪,家里仅靠他的工资生活,他早就学会了与世俗打交道:“我能把写作和生活分开来,在生活当中尽可能地和大家打成一片。”
陈年喜的诗
2013年,他在南阳的一处矿山连续工作了四个月,没有休息一天。
有天夜里,他刚从巷道里爬出来,母亲给他打来电话,说查出了食道癌,晚期。
一瞬间,陈年喜觉得自己就像要炸裂一样。第二天,他写下了一首《炸裂志》:
我在五千米深处打发中年
我把岩层一次次炸裂
借此 把一生重新组合
我微小的亲人 远在商山脚下
他们有病 身体落满灰尘
我的中年裁下多少
他们晚年的巷道就能延长多少
我身体里有炸药三吨
他们是引信部分
就在昨夜
我岩石一样 炸裂一地
陈年喜在矿上写诗
这个铁骨铮铮的男人曾说:“我觉得人生本来就是战斗,甚至是以弱抗强、以卵击石的战斗,如果你向它妥协,那你就是失败者。”
但现实是,母亲患病的一年后,陈年喜无故被矿上开除,两个月工资被扣押,他无奈回到老家。
2015年,矿工的职业病将他扑倒,他做了颈椎病手术,离开了矿山。2020年,他被确诊为尘肺病——粉尘被长时间吸进肺里,肺变成了“石头”。
他写:
一张黑底CT影像胶片里
是我半生的倒影
“我们眼看着人生的终期就在前面,一天一天地往那个地方靠近。”陈年喜说。
陈年喜和父亲对话
写作,这个原本他聊以慰藉的爱好,成为了陈年喜当下的生活支柱。
时间有了大把,他不再执着于诗歌,开始写散文。散文可以把诗歌里盛不下的命运铺展开,散文的稿费也更多一点。
他将自己的作品视作小人物的白描,好比杜甫的“三吏三别”。尽管人们都没有去过唐朝,“我们从这个作品当中,可以看到政治的动荡下颠沛流离的底层人的生活”。
2023年,陈年喜拍摄的妻子在读他的书
有人曾问他,当一些农民工读到他的作品时,希望他们从中获得什么。
陈年喜摇了摇头,说农民工大概不会看他的作品,因为他们的生活已经足够丰富。
就像他之前写过的那句:“再低微的骨头里也有江河。”
所有听说过我的人们啊
不必为我的离开感到惊讶
更不必叹息,或者悲伤
我来时很好,去时,也很好
——许立志《我弥留之际》
“很多年后,当我们再度回忆起这段中国经济崛起史的时候,这些诗句是不应该被遗忘的。它们是大历史中的一些小配件,也许微不足道,但若缺失,则其他真相,俱为谎言。”
协助出品纪录片《我的诗篇》的作家吴晓波曾这样说。
许立志去世后,秦晓宇决定将他的诗集整理出版,希望用这样的方式,延续许立志的生命,让更多人关注底层打工者的命运。
那是2014年的岁尾,众筹从12月1日开始,为期45天。最小额度为2元,付出1000元以上的支持者姓名将出现在诗集中。
10天之后,超过982个支持者为这本诗集筹措了118756元资金,远远超过了当初设置的6万元目标。
在当时,人们更多的是在惋惜,一位网友发文称:“这个世界,不适宜于诗人的生存。诗歌——不能果腹,不能买房,不能获得爱情,不能赢得尊严,你所视为生命的东西全无用途。”
一个月后,诗人余秀华的第一本诗集《月光落在左手上》发行,首批15000册一日售尽,让人悲欣交集。
纪录片《我的诗篇》片尾
诗句作者杏黄天
诗人拒绝了时间,留在了2014年,但诗歌的生命,一直延续到了现在。
2014年10月15日,按照老家习俗,自杀者不能入祖坟,许立志的的骨灰被撒入深圳南澳的海水。
9年过去了,许立志的微博被岁月尘封,如他所期待的那般,没有人再动这片精神净土。
陌生网友的留言日复一日滚动翻新着他写给人间的最后那句诗篇,好似对诗人无声的吊唁。
“听说你去了天堂,若有空,请寄一朵云给我。”
“特别声明:以上作品内容(包括在内的视频、图片或音频)为凤凰网旗下自媒体平台“大风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videos, pictures and audi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the user of Dafeng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mere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pace serv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