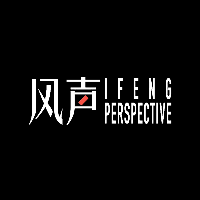风声|老人带娃要“带孙费”败诉,亲情就该无偿使用?


独家抢先看
作者丨王泽荣
德国柏林洪堡大学宪法学博士候选人
近期,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介绍了一起“丧偶式”育儿引发的离婚经济补偿案件。王先生因辞职创业总在外省而夫妻分居两地,宋女士为了更好地陪伴儿子辞去高薪工作,全职在家照顾孩子、操持所有家务。与丈夫协商未果后,宋女士提出离婚,根据《民法典》“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王先生被判支付离婚经济补偿人民币10万元。
但是,除去家庭主妇式带娃外,中国经常出现夫妻双方忙工作,父母辈帮忙带娃的情况。近年,妻子操持家务的价值获得了社会的普遍认可,但父母辈帮助带娃的价值尚未进入大众视野。2月26日,北京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民法典通解通读》节目,围绕的便是“姥爷讨要‘带孙费’”这一疑难案例。
据节目介绍,本案原告之女与被告在婚姻期间育有一子,原告应自己女儿的请求,从老家辞职去北京照看外孙,其女与被告离婚一年之后,原告要求被告向其支付一万元的劳务费;被告则抗辩称,与原告从未签订照看孩子的劳务合同;鉴于外祖父并无抚养义务,法院认定原告帮助被告照料孩子的行为构成无因管理,但鉴于原告未能提供其“合理支出”证据,法院最终没有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带孙”劳务费,法律支持吗?
在《民法典》构筑的家庭图像下,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教育和保护义务;在一般情形之外,有负担能力的(外)祖父母对于父母已经死亡或者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外)孙子女有抚养义务。
然而,(外)祖父母帮助照看年幼的(外)孙子女,(外)祖父母作为辅助甚至主要照料人,其实是当今中国家庭的常规模式之一。
面对“老人讨要带孙费,您听说过吗?”这一问题,镜头中的三位路人均表示反对和不理解:“不可思议”、“反正我是不会那么干的”、“哪有还要钱的,那都倒贴钱的”。当问题换成“老人帮忙看孩子,这是义务吗?”时,路人的回答则有分歧:“确实不是他们的义务”、“这个,带孩子应该的嘛”。
与市民相比,案件的原告斩钉截铁地表示,自己讨要带孙劳务费是符合“《民法典》规定的”。
关于“带孙费”似乎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识:
一种基于传统道德上的义务观念,认为辅助子女照顾孩子是应该的,反感将对孙辈的亲情付出经济化;
另一种则以《民法典》为依据,主张(外)祖父母对(外)孙子女不负有抚养义务,进而要求得到相应的报酬。
在节目讨论的案件中,判决所立足的显然属于第二种:从外祖父不负有抚养义务出发,到最后肯定老年人在辅助子女抚养(外)孙子女过程中的“付出和劳务”。在说理的核心部分,本案判决将原告的行为认定为无因管理之“债”,这无异于用经济化的方式来评价传统朴素观念中老年人“应该的”付出。
此外,判决虽然将本案原告认定为无因管理人,致使其仅可要求受益人偿还必要费用或适当补偿损失,但判决结尾也提示老年人可以与子女签订书面协议,似乎允许另一种“债”的可能:劳务合同。
判决书的自相矛盾之处正在于此,判决认定无因管理而非劳务合同,这导致文书最后对老年人劳务价值的肯认沦为口惠之辞。此外,必要费用不包含无因管理人自身的劳务费,却不排除管理人向他人支付的劳务费(“保姆费”)。
如此一来,如果有预付能力,老年人将辅助抚养涉及的劳务外包给市场主体后,反而能得到偿还;没有预付能力的老年人亲自提供照料服务,却无法得到法律的认可。这其实体现着一种相对保守的司法取向。
老年人在不负有义务时(辅助子女)抚养孙子女或外孙子女,通常涉及被照料儿童生活的方方面面,且往往连续或不连续地经过较长的时间跨度。在这种情况下,将无因管理制度适用于如此复杂且漫长的事业,恐怕有削足适履的嫌疑。
在辅助抚养的情形下,辅助抚养人与抚养义务人经常要就具体事项时时沟通、达成一致,此时将老年人辅助抚养的行为笼统认定为无因管理,将造成一种自相矛盾的结论:一个大的一般的无因管理却包含着许多小的具体的(委托)合意,即便这些合意大概并不涉及劳务报酬。
认定无因管理与否定劳务关系,其实互为表里,但法院不能为了适用无因管理而否定劳务关系,相反只能在认定劳务关系无果之后才能认定无因管理,以便保障抚养承担者至少能向抚养义务人收回其支出的必要费用。
此外,法院若为了避免承认事实合同而谨慎认定劳务关系,那么在认定无因管理之后,就应当考虑到老年人在担任辅助甚至主要照料人时所付出劳务的经济价值,将“劳务费”纳入必要费用的范畴,并考虑到“管理”事务的复杂性和时间跨度以及老年人在家庭与社会中的弱势角色,在举证责任方面对老年人有所倾斜和照顾。
“带孙费”前后的家庭系统性压力
我们应当如何对待家务劳动的价值?”(外)祖父母辅助抚养(外)孙子女”的现象看似发生在家庭内部,在根本上却源于市场对家庭的系统性压力。
因此,当这种系统性压力在某个家庭爆发为具体的冲突时,比如讨要“带孙费”,我们就不能将其单纯理解为家庭成员间的关系问题、或隔代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而应该在更大的视域下鸟瞰家庭与市场之间的结构问题。
日本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一书中,将“市场—家庭”与“市场—自然”的关系结构相类比。在她呈现的图式中,市场从名为家庭的外部环境中获得健康劳动力,同时将不被市场需要的老人、病人、残疾人纳入家庭环境。于此,家庭作为市场的外部环境而存在,但为维持家庭而付出的劳动成本却不适用市场的评价机制。
这也是家务劳动始终遭受贬低甚至无视的根本原因。
面对家庭与市场的外部结构问题,一方面,政府应当扼制市场对家庭在职人员的不合理压榨,保障职业男女有时间精力尽到家庭责任和义务;另一方面,应当适度缓解家庭为抚幼养老目的而在市场的成本支出,譬如通过税务减免或社会保障政策,2022年3月28日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设立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个人所得税专向附加扣除费用》便是如此。
讨要“带孙费”的个案冲突在进入法官或公众视野时,已经表达为家庭内部的关系问题。发生“带孙费”冲突而诉至法院的家庭关系,往往要么处在解体的边缘,要么干脆已经破裂。如节目中的案件,便发生于原告之女与被告婚姻关系结束之后,且由于原告与其女的父女关系并未破裂,因此原告仅对被告一方提出支付劳务报酬的诉求。
在此情形下,亲情的关系实则转变为陌生人的关系。关系破裂的“家庭”成员之间,不仅在将来要以“市场”的逻辑相处,而且对于在“家庭”关系存续期间从市场得到的收益与被市场转嫁的成本,也必须按照“市场”的逻辑加以清算才算公平。
《民法典》第1062条规定的夫妻共同财产问题就预置了类似的逻辑:即便夫妻中一方在“市场”工作、而另一方在“家庭”主持内部事务,法律依然认定在“家庭”的一方对另一方从“市场”得到的报酬和收益有同等贡献。“共同财产”在分割之前,已经蕴含着一人一半的分割可能。
于此可见,在市场之外的家庭其实也可按照市场化的方式结构来看待,即便是在“家庭”关系不完全解体的情况下、甚至在美满友爱的“家庭”关系下。原因在于,“家庭”关系承载着比“市场”关系更为丰富也更加复杂的内涵。
本案判决书提示老年人为保障自己权利,在承担对孙子女的照料时,最好与子女签订合同明确权利义务关系,也是出于着同样的理解。
我们愿意相信:为了建立“平等、和睦、文明”的家庭关系,更应当尊重且客观评价家庭成员的劳务和付出,而不能将亲人的牺牲和服务视为理所应当。
本文系凤凰网评论部特约原创稿件,仅代表作者立场。
主编 | 萧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