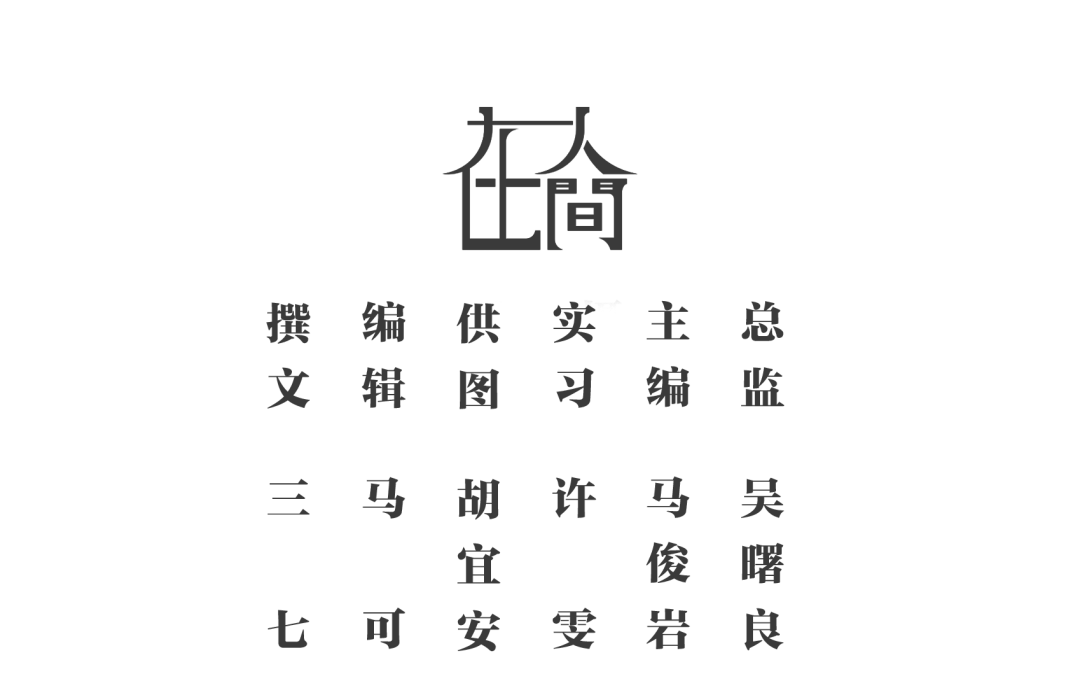在人间|校园生死课:写遗嘱 参观殡仪馆 讨论死亡


独家抢先看
撰文|三七 编辑|马可
广州大学教学楼,晚饭过后六点半,天还没完全黑,风柔和细腻,座位上的脸庞青春稚嫩。这是一堂选修课,上座率不错,只剩零星几个空位。教室里静静的,他们在这里讨论如何面对死亡。
60岁的胡宜安是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他是国内第一个在大学课堂开设《生死学》课程的人。除了教《生死学》,他还教毛泽东思想概论。衬衫加西装长裤,典型的思教老师形象。不说话时胡教授有点严肃,但学生们对他的印象是,爱笑,在课堂上常开些玩笑,他笑得开朗。还有人评价,“初看普普通通一位中年人,但去听他的课,或者和他聊天,会觉得他心底里有一种非常敏感和感性的东西,一种很人文的东西。”
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记者潜入他的课堂,课堂链接的是外面的新闻事件,或者与死亡相关的各种情态。课堂上过热搜,清明节等特殊日子,最近这几年疫情造成的不安情绪,也让课堂内容常被提起。
写遗嘱,是死亡课里最重要的一项。有时是课上到一半,有时是到最后,“气氛到了”,胡宜安就会安排,“根据需要随机”。一旦安排下去,课堂里生出一阵新奇感叹,学生们都知道“这个”肯定要有,新奇过后,接着是“有点凝重”,他看出学生脸上的表情,“不知道从何下笔”。
忌讳一直存在,得知有一堂课作业是要写遗嘱,有父母不让。在胡宜安看来,生活中如果没有死亡的话题,就少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内容,因为死和生都是人本能关心的事。在大多数人眼里,生死学可以学,死亡也可以被讨论,但大多是抱着旁观者的心情,茶余饭后,讨论遥远的车祸火灾,都是别人的死,一旦自己变成主角,就会逃避,变得不吉利。胡宜安觉得,父母一反对就不用写,故意不跟父母说,也不必要。
“作业”交上来,有人给自己的财产列了表格,有人交代遗体处理方式,一般是火葬,还有说明火化之后把骨灰制作成一个什么物件。有人希望到了最后阶段不要抢救,不要搞告别仪式。甚至还有细致到,自己不喜欢什么颜色,坟上献花时,不要这个颜色的花,还有不要播放哪样的歌曲。胡宜安感到,和学生所处的年龄和时代有关,“很现代性的东西,很个人主义”。
遗嘱看似是漫无边际,在胡宜安看来,其实只有真正着笔,人才会想到该处理些什么事,该和什么好好告别。比如很多学生在遗嘱里提到跟父母亲的关系,过去不理解父母,可能会造成一些无法弥补的伤害,有人会反思反省。他知道万一有一天他的亲人,父母亲走到这一步,他会怎么处理。包括自己的遗产分配和身后事,有人提出要捐出自己的器官,这是一种死亡自觉,和对后代的一种责任心,这是中国人非常在意的东西。
在胡宜安办公室,收着一大叠的“遗书”,这是他特意收上来的。“因为它毕竟是一门课,不能把课等同于现实,这是两码事。学生的理性思维能力还没到那个高度,生死课不是说时时刻刻要唠叨这个死亡。”在他看来,下面这些孩子能站在生命的终点站,回过头来观察当下,起到这个效果就行。
写遗嘱、讨论死亡,甚至是去殡仪馆参观,二十多年前在高校里开一门关于死亡的课,并不容易。中国人忌讳谈死,更重要的是,人们很容易把死亡课和学生自杀率联系。2009年的《信息时报》评价他的死亡课“神秘奇葩”,认为是作秀、造噱头。
变化发生在2015年前后,医疗系统和殡葬业更加规范化,社会情绪的变化延展到了课堂,“好像就不再用新奇的字眼去描述,课程更多地结合一些实际问题,比如该不该实行安乐死,安宁疗法的好处等等,这个课推广解决实际问题,考试也考这些问题。”胡宜安告诉《在人间》。
2017年在广州大学开过一个研讨会,医疗一线人员、殡葬行业从业者、社会理论研究机构人员都来参与。大家从不同的方位连接,探讨个体到了生命最后阶段,该怎么去面对,要抢救还是不抢救,关于死亡的议题越多,死亡教育的重要性也越被提及。
“到了最后阶段才去对人进行生死教育吗?为时已晚。教育是往前移的,要在年轻的时候,身体健康的时候。”
胡宜安关于死亡最早的回忆是几岁时,在农村里老人下葬,小孩跟着看热闹,棺材板一盖,放入那个深幽幽的坑里,往棺材上面堆土的那一刻,胡宜安感到,这里面的人永远永远出不来,一种莫名的恐惧升上来。到后来他研究死亡学,知道这是一种“微死体验”,小孩这时候是需要人去引导的。
在胡宜安看来,传统社会有一种死亡启蒙传承。过去农村里办丧事,村里的人都来帮忙,大家共同面对生死,布置灵堂、请和尚、宴请乡里等等,遗体也要在家门口放三天。在这个过程里,人接受死亡有一个适应,一个预习与储备。但如今生活节奏快,很多事都在变化,“亲人过世打个电话给殡葬场,你交钱,办业务,指定时间点去告别,在哪个时间结束,很商业化的这套”。
这里面会产生很多的困惑,比如葬礼上该怎么做,一个亲近的人过世应该怎么处理恰当?学生们似乎对这些都比较陌生,“对他人的生死,我们肯定要敬畏,有情感的反应,有行为的反应。比如说面对别人非常悲伤的事,你怎么能够快乐地唱歌呢?你要表达同理、同情。死亡是一个大事,你不是说,哎呀,我还有一个更大的事。什么大事比死更大?这个时候都不能让人共情。”
■ 胡宜安在课堂上。
每个学期,胡宜安要带学生们去参观一次殡仪馆。在广州番禺殡仪馆,学生们会去冰冻冷藏室,有些遗体不能立马火化,比如因为刑事案件,或是死因不明的,必须放在这里,等待医学鉴定之后,才能处理。“这也表达了对生命的敬畏。”在殡仪馆,人在里面躺着,变成一个物体,几号几号。胡宜安知道,这时候每个人都有一种碰撞感,一种颠覆,是死亡造成的冲击。
这时他会和学生们讲起在美国一家死亡博物馆里的故事,小格子间放只已死的兔子,另一间放一只活的。小朋友触摸,活蹦乱跳的,很可爱的小白兔。另一边一摸它不动不跳了,死掉僵硬了。人会产生恐惧,但不能老是停留在这个画面,要进一步去思考,肉体、生理的死亡是什么?包括形成自己的生死观,有对家人、亲人的生离死别的知识储备,后面就不至于张皇失措,不至于无所适从。
在参观殡仪馆时,一位女学生的反应引起他的注意。其中有一个环节叫礼仪展示,告别亲人。这位女生驻足了很久。结束之后才知道,女生的外婆过世之后,父母担心她的学业,不让她参加葬礼,说回来很麻烦,让她安心读书。但是从那之后,女生一直觉得非常内疚,总会想起外婆,想到她走的时候是不是很孤独。
在办公室,女学生和胡宜安谈到,在殡仪馆参加礼仪展示时,她心里一直在想外婆,心里念着和外婆说的话。礼仪展示使她明白外婆的告别仪式大概就是这样子的,她心下释然了,觉得外婆走得应该不会太孤单,自己也像经历过那个现场,真正参加了一次外婆的告别。从那之后,她的内心渐趋坦然,不再为当初未能参加外婆的告别仪式而内疚与不安。
对于很多学生来说,处理死亡总是一个充满挫折的过程。胡宜安的学生王嘉仪在上课之前,对死亡的理解是觉得很遥远,“气死,烦死了”这样的口头禅也常挂在嘴边。她感到自己小说看得多,对于死亡没有太多实感,小说里很多殉情、以死相挟等等,死亡都是非常浮躁和轻易的。
好几年前五一黄金周,胡宜安听说,某班一位男生出车祸走了,他是一位很活泼的男生,大家都非常喜欢他,班里所有同学都参加他的追悼会。但是有一位女生在那之后找到他,说总觉得男生还活着,总是往他经常坐的地方看,一进教室看到那个位置,就没办法安心学习,人也是恍恍惚惚。
胡宜安告诉这位学生,同学的离世表明他不再是现实中的真实存在,“不应该让他弥漫在你的生活中,要接受同学死亡的事实,并通过追思将与这位同学间的过往友好关系变成你人生中的一段美好经历。”
要抵制这种弥漫,胡宜安建议这位女生找几位和这位男生关系很亲的同学,找一个特定时间来缅怀他。也可以搞个群,写想对他说的话,甚至可以涂鸦,把想念表达出来,暗示自己大学期间曾经那么一个很好的同学,很可爱的,很遗憾他走了,我们永远都记住他,但绝不让学生赶快把他忘了算了。
在胡宜安看来,他人的死亡事件对于每个人都是一个非常深刻的事件,即便像是旁观车祸,也会转换成对自己开车行为的纠正,不能是简单的遗忘,而是需要转化成一种人生中的宝贵东西。
“比如说家里人去世之后,过去说不要让这个人出现在生活里,免得睹物伤情,但是要知道一个人,假设他有在天之灵,是不希望被遗忘的,这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共鸣期待,我们也不希望被遗忘,我们可以怀念他,追思他,追思的过程中,不一定就是悲伤,可能是非常轻快的,他走了,我们谈起他过去的那些事,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曾经有这么一个可爱的人,爱我们的人,是我们人生一个很幸运的事情。既然是一个很幸运的事情,那是一个愉悦的心情。我们对亲人朋友的怀念,也是我们生活本身的一种内涵。”
由于体质较差,胡宜安经常要跑医院,时常遭遇到医生态度生硬、就医体验糟糕的情形。比如,去年8月,由于晨练时小腿肚子剧烈疼痛,联想到一年前进行肾结石微创手术拍片时被医生告知可能有腿部动脉血栓,当时没细究。此次跑步中产生疼痛便挂了一个运动医学专家号,讲到自己病情反复的经历。谁知医生就一句话怼来:你说那么多干吗?有了疼痛还去跑步,真是活得不耐烦吧!
这些生活里的事,他常常会联系到自己的课堂,意识到很多事是纯粹的医学解决不了的。在他看来,医学不能够简单得就是救死扶伤。在发达地区有80%的人是在医院里去世的,在生命最后,选择痛苦无尊严地活着,还是无痛苦有尊严的死?人有没有决定自己死的这个权利?还比如老龄化、校园恶性犯罪等等问题,都需要生死教育给出一个解释框架。
死亡权在他看来,是一种个体自然死亡权利,不人为延缓也不加速,首先还是不加速。人的本能还是“念生惧死”的。
胡宜安注意到,有好几年两会都有人提安乐死的议案,新闻里也经常看到,哪位国外的老人去瑞士安乐死。安乐死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是,个体生命到了最后不可逆的死亡阶段,承受着巨大的病痛,令他尊严尽失。但是现代医学可以让患者在最后阶段的痛苦得到有效的控制,在这个情况下难道还要谈安乐死吗?
医疗如何面对新的社会变化,他倡导一种方式叫安宁疗护。安宁就是缓和安宁,控制病痛,减缓个体在最后阶段的痛苦。不单单把病人看作一个生物学机体,更多是看作一个人。
曾经有一位专家是胡宜安的朋友,去医院病房里看望病人时,有位病人道出自己的心声,觉得他的到来,像是一位死亡使者。医生专家朋友目瞪口呆,从来也没想到自己在病人心中是一个死神代理人。胡宜安认为,如果要病人不再有等死的感觉,在生命末期不再做无谓的抢救,充分利用最后一个阶段提高生活品质,没有痛苦地跨过死亡之路才是关键。
《最好的告别》作者葛文德说,“善终绝不是好死,而是好好的活到终点站。”
■ 胡宜安在课堂上。
了却尘事,是走向死亡最重要的一步。在胡宜安看来,人世间还有很多恩怨情仇,亲人、子女、长辈,总而言之,有无尽的爱,要去道别、道爱、道歉,不能拖泥带水,不能带到坟墓里去。有了这个道歉或道爱,生命质量会不一样,尘缘的事了了,走得洒脱干净,这个洒脱是对抗死亡恐惧的重要一步。
此外,不介意临终者失去了什么,要关注他还有什么,不必要关注他已经不能够做什么,关注他还能做什么。在胡宜安看来,在走向死亡时,家的意义非同小可。在央视的纪录片《人生第一次》第9集开头有这样一个问题,问一个人上午被确诊为癌症,他中午会干啥?答案是吃饭,一起吃饭的地方就是家。生命末期,躺在病房里的癌症患者就是想喝老婆炖的汤,想吃妈妈煎的一条鱼,这是人能够获得的唯一的心灵慰藉。
但有时候不一定有条件来营造家的氛围,但至少要有关怀。胡宜安认为,在最后阶段临终者面临最大的人生脱轨,一旦进入到病程的末期,所有正常的生活都不存在,很多老人回到动物状态,做出出格的举动。失智者自己没有意识到,就只能靠看护者、陪伴者通过不厌其烦的照顾,帮助他维持尊严。法国学者樊尚·托马曾提出这样一个公式,死是临终者与幸存者的关系,死不单单是死人的事,还是活人的事。
究竟如何走进死亡这扇门,人们尚未了解,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消除孤独的善终,一定有人陪伴,因为此时的临终者无疑是最弱势的。有一项调查研究表明,96%的患者表示希望与医护人员讨论性和亲密关系的话题,并得到专业的帮助。在生命末期,患者对性与亲密关系的表达发生变化,不一定指性行为,是指进入一种亲密关系,也是人最终走向死亡之门时的内在需要,一种深层次的链接,像妈妈和婴儿那样共生。
柏勒·罗斯在研究临终心理时谈到,“不要从临终者身边逃走,按照我们传统观念,走向死亡的人是多恐惧、多不吉利、多糟糕,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想法,我们真的要躺下,要陪伴,要在场,自己可能由此获得一种终身受用的东西。”
疫情下,很多人在经历恐惧与焦虑。一开始,是身边的同事、朋友一个个染疫,在恐惧中轮到了自己;在病痛中找药、买抗原、抢水果及生活用品。然后,担心家里的老人,每天看着铺天盖地的新闻。也有很多人失去亲人,或者失去抢救机会。这些生死场面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在胡宜安看来,瘟疫的影响是全社会性、全民性的,生死重大问题上大家很容易把自己代入。这种死亡焦虑、不确定性会造成很多心理问题。胡宜安觉得,必须有一种方式,把对于死亡的焦虑,抒发出来,不要让它累积在内心,变成非理性的东西。他有一段时间,在课堂上让学生讲自己的故事,谈论自己与死亡相关的经历,有学生讲到至亲的人死去他怎么都难以承受,讲完之后,都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课堂之外,他也觉得,可以与伴侣、家人或亲密伙伴毫不避讳地聊聊。
从小到大一直到老,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有生死的主题,都要跟进教育。什么才是一个好的死亡?在胡宜安看来,一般的,好的死亡就是自然死亡,一个生命到达一定衰老年龄,当然也可能是,“酒店打烊要走”,“勤劳的一生换来甜蜜的长眠”,很普通朴素的死亡的认识。但是失去了传统社会的传承,中国人没有面对死亡的能力了,遇到死亡,惶恐不安,焦虑、恐惧,一直到最后都是这样。
胡宜安认为,生死观,死和生是连在一起的,死亡教育,其实探讨的还是生的意义,希腊一个警示语,特拉普修道者的一句问候语,“请记住,你将死去”。“比如就这么几天要死,还会去刷那个电视剧吗,会花那么多时间在一些比较无聊的事情上吗,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经历过真正的面对死亡是幸运的,会对他的生命有一个提纯的作用。”
死亡体验里,也分不同程度,有些是在细节里。《红楼梦》里有黛玉葬花,黛玉一边葬花,一边吟咏,对面山坡上宝玉听到最后,兜着的花散落一地,这个人一下子就懵了,在胡宜安看来这是“微死体验”。再比如,“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这也是微死体验,流水不息,奔流到海不复回,人生何尝不是如此。心思很敏感的人,回家看见妈妈在那掉了一个东西,弯腰捡时,突然发现母亲好像老了,原来可是很麻利的,再仔细一看,两鬓出现白发了,这也是微死体验。
那个体验,会让人在那一瞬间意识到人生有另外一面。胡宜安谈到,911事件之后,有一位中国人是搞金融的,本想争取到世贸中心去上班,世贸大楼倒塌了,他反复求证,因为那是自己心目中的圣地,第二天知道是真的,马上迸射出一种明天再好也要活在当下的念头。在这之前,他跟女朋友谈恋爱两三年,一直拖着,这三天就决定跟他女朋友结婚,买家具,开始考虑生活里具体的事。
胡宜安感到,活在疫情之中,很多事情不堪一击。但在那个时刻,真的能想到很多本质的东西,在日常生活中发现不了的东西,那才是人生的真相。
比起微死体验,濒死体验更进一步,是指人曾经有过重大疾病,在鬼门关走过一遭。有一些研究把这叫做NDE (Near-Death-Experience)。有人通过时光隧道,看到自己,看到已经失去的至亲好友,还有从来没有见过面的祖先。 还有一种是天花板视角,灵魂出窍,看着下面这些人,围着他忙碌得不得了。经过濒死体验的人,整个人格、人生观都有所改变。
“他们更加珍惜亲情、身边的人,不再像以前那样,那么争强好胜,那么斤斤计较,锋芒毕露,他们非常柔和,愿意放弃一些不必要的名利,愿意花更多的时间陪孩子、亲人,更加珍惜这些东西。但同时,他也不再惧怕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