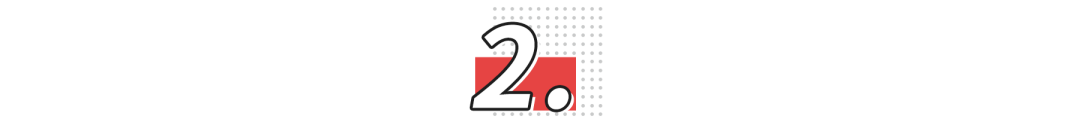唐驳虎:韩国人、日本人、土耳其人都来自中国东北


独家抢先看
文/凤凰新闻客户端荣誉主笔 唐驳虎
核心提要:
1.这篇引发不小轰动的论文,是由德国教授Martine Robbeets牵头,该团队利用跨学科方法去研究语言。他们综合历史语言学、考古学以及分子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提出泛欧亚语系(旧称阿尔泰语系)的发源地在中国东北,更具体而言,在辽河流域的西部。
2.这篇论文论述的是,大约9000~7000年前生活在中国辽河流域的农民发明了一套语言。后来随着他们向东或者向西,迁徙到西伯利亚、韩国、日本,把这套语言带到了那里。也就是说韩国人、日本人、土耳其人,还有中亚各斯坦(塔吉克除外)、西伯利亚的通古斯人,在遥远的史前史上,老家都来自中国东北。
3.对于国家形成之前的语言/族群传播,农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驱动因素。但因为原始农业是一种自然农业,它的兴衰也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所以,气温可以为文明的诞生创造必要的条件,同时一个文明的陨落也和气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4.这篇论文提出“三角验证”的研究方法,在还原人类历史等诸多方面大有作为。通过语言学、考古学和遗传学的融合交叉,三个学科的结论能够互相印证,说明结论可信度高。
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一直是科学研究关心的问题。
传统的考古学、历史语言学和近年来兴起的基因人类学(分子人类学),被认为是人类史前史研究的“三驾马车”。但仅仅通过单一学科的研究还不足以全面阐明人类及文明的演化史。
2021年11月11日,电商双十一,人民空军成立72周年,陀斯绥耶夫斯基诞辰200周年,《自然》(Nature)杂志在线发表了题为Triangulation supports agricultural spread of the Transeurasianlanguages的封面重磅文章。
这篇犹如炸弹一般的文章,结论是韩国人、日本人、土耳其人都(史前史)来自(今天的)中国东北。标题翻译应为《三学科联合研究支持泛欧亚语系的农业传播》,Triangulation又是地图测绘的三角测量、三角定位,颇有一语双关之意。
这篇论文的轰动,就在于它可能颠覆了语言学界几十年的认知。最后还结合考古和基因,溯源到了地点,或许完成了人类史前史一块重要拼图的构建。
语言学否定之否定
泛欧亚语系大致以北纬40°为轴线在欧亚大陆传播,从东面的日本、韩国、西伯利亚一直延伸到西面的土耳其。旧称通古斯语系、阿尔泰语系(Altaic languages)。
欧亚非大陆的四大语系,是世界语言的主要分类,分别是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印欧语系(印度、伊朗、斯拉夫、欧洲)、闪含语系(西亚、北非)。
最早将阿尔泰语言联系起来的人是菲利普·约翰·冯·斯特拉伦伯格( Philip Johan von Strahlenberg)。他是 18 世纪的地理学家,发现了这些语言之间的相似之处。
芬兰语言学家马蒂亚斯·卡斯特伦 (Matthias Castren) 首先提出阿尔泰语系,总结其主要特点为语序为主-宾-谓结构,以及黏着语词缀等。早期他还把芬兰语纳入这个语系,后来发现不对,单列为乌拉尔语系。
但在语言学上,泛欧亚语系的五个语族(日本语、朝鲜语、通古斯语、蒙古语和突厥语)是否来自同一个共同祖先,甚至是否确应归为同一语系,一直是高度争论的热门话题。
这是因为其中的各个语族,都存在大量借用、混杂其他外来语族的情况,语言面貌非常复杂。而且泛欧亚语系的起源和传播也一直存在很大争议。
此前较为主流的一种“牧民假说”认为,泛欧亚语系的起源大概在公元前2000年到1000年(距今4000~3000年)左右,是由从蒙古草原向外迁徙的牧民传播开来的。
还有一些研究人员认为,泛欧亚语系起源于大约5000年前中亚的游牧牧民。
有些人甚至推测起源地区可能包括阿尔泰山和西伯利亚南部叶尼塞河谷上游,该地区现在是俄罗斯的图瓦共和国。但这些假说又很难解释得通日韩人群的来源与迁徙。
实际上,最近几十年,在语言学术界,越来越多的语言学者认为,朝鲜语跟日语一样,都是孤立语言,他们跟世界上已知的语系都没有关联 。
如果谁还坚持认为朝鲜语跟日语是阿尔泰语系,几乎都被认为是“民科”。
还有专业学者认为,朝鲜语跟日语都源自遥远的南岛语系,也就是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但这个来由也太奇怪了,比“中亚牧民”假说更不靠谱。
▎ 蒙古语族分布图,大约有 610 万蒙古语使用者。还有约43万卡尔梅克-卫拉特语使用者,22万布里亚特语和20万东乡、裕固语使用者
而对于欧亚大陆剩下的三个语族——通古斯语、蒙古语和突厥语,这三个语族之间是否有亲缘关系,语言学界依然认识不同,分成两个学派。
一派认为有亲缘关系,也就是在三个语族各自的共同语之上,还有一个“原始阿尔泰语”,正在进行它的构拟工作。
▎ 通古斯语族分布图,包含满语、锡伯族语、鄂温克语、鄂伦春语,真正的使用者不到5万人
另一派认为三个语族之间没有亲缘关系,这些语言是互相接触而非同源的,它们虽然在语法和词汇上有相同之处,但更多是相互交流、借用而来的,并非源自同一个祖语。
总之,阿尔泰语系这个概念,近年来在专业学者当中已鲜有支持者。语言学界普遍认为阿尔泰语系不符合语系的定义。
▎ 突厥语族在三个语系中的使用者最多,而且不同语言的人数差异很大。包括土耳其语(超过 8500 万使用者)、乌兹别克语(近 2700 万)、阿塞拜疆语(近 1400 万)、哈萨克语(约 1300 万)和维吾尔语(超过 1000 万)。总共有1.9亿人使用突厥语
学界主流将通古斯语、蒙古语和突厥语视为“语言联盟”而非语系。因为要成为一个“语系”,所有语言都必须来自同一个祖先。
然而,主流语言学者的猜测与分析,在更强力的科学证据面前,可能又再一次被粉碎。历史认知再次走了一次否定之否定,螺旋式上升的学术道路。
数学方法定量研究下的考古溯源
主导这篇论文的,是马丁·罗贝茨(Martine Robbeets)领导的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学会的人类历史研究所考古语言学研究小组,包含了来自中、日、韩、俄等国的博士生、合作学者。
他们综合历史语言学、考古学以及分子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提出泛欧亚语系(旧称阿尔泰语系)的发源地在中国东北,更具体而言,在辽河流域的西部。
既然定位为考古语言学研究小组,该小组近年来的重要基础工作便是构建了一个跨语言基本词汇数据库。
其中收集了98种泛欧亚语言254个基本词汇概念的3193个同源变化集,并应用数学方法,对泛欧亚语系各语支进行系统发育和定年分析。
正如阿尔泰语系的支持者认为,阿尔泰语系比欧亚大陆的大多数语系要古老,是现代阿尔泰语言同源词保留较少的原因。
而马普人类历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重点研究了迄今为止泛欧亚语系最全面的农牧业相关的基本语言词汇,通过计算机模型研究同源性。
其中包括与耕作有关的(“田地”、“播种”、“种植”、“生长”、“种子”),食品生产和保存(“研磨”、“酿造”);
以及纺织品生产(“织布”、“缝”、“剪”、“麻”),以及关于定居生活的(“猪”、“狗”和“房子”)。
因为语言演化过程会遭遇不计其数的文化碰撞,这些基本词汇传承是相对稳定和穿透时空、文化的。而借用词汇很多时候与文化、特别是外来文化相关 。
回溯运算结果表明,泛欧亚语系的各个语言当中,这些词汇及演化是互相关联的。
原始泛欧亚语系的起源时间为距今9180年(公元前7160年),分支语系“原始阿尔泰语”(突厥语、蒙古语和通古斯语族的共同祖先)与日韩语的祖源分化时间为距今6820年(公元前4800年)。
日语与韩语的分化时间为距今5460年(公元前3440年),蒙古语与通古斯语的分化时间为距今4500年(公元前2500年)。
这也验证了阿尔泰语系支持者的早先预计——日韩语言与阿尔泰语系的关联,“会比我们目前的知识状况所能想象的更加复杂和遥远”。
接下来,在考古学方面,对东亚、东北亚和中亚地区所有已经发表的考古学数据(陶器风格、丧葬风格)进行重新整合聚类。
研究者建立了东北亚地区新石器至青铜时期(8500年~2000年前)255个考古遗址的数据集,包含172个考古学特征的定量化数据以及157个植物遗存C14测年的数据。
同样基于数学分析,考古学家发现了韩国的篦纹陶器文化、日本弥生文化与西辽河地区青铜时代文化在考古学定量化分析中的相似性。
之前的考古研究发现,完全驯化的小米(栗)、黄米(黍)至少在6000年前就出现在中国的辽河流域。
而新的考古发现,这些作物在距今约5000年(公元前3300~2800年)便传到朝鲜半岛,并在距今3000年(约公元前1000年)左右传到日本。
最后,遗传学家分析了生活在9000年~300年前的23个古人的DNA,这些人生活在现在的西伯利亚、蒙古、中国、韩国、日本和琉球群岛。
同样使用计算机算法来构建这些人彼此之间,以及与2000个现代人之间的关系。
通过对朝鲜半岛古人类基因组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朝鲜半岛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群在遗传上含有绝对比例的来自中国北方农业人群的遗传成分。
并且在距今6000年前后,朝鲜半岛就与日本绳纹人发生过不同比例的基因交流。而在随后的历史过程中,绳纹人的祖先成分再次被来自中国北方的农业人群所替代。
关于日本的情况,30年来语言学、考古学、遗传学的不断研究发现,日本主体人群是绳纹人和弥生人的混合。
绳纹人主要是38000年至18000年前从亚洲大陆分离而来,以狩猎采集为主,只有小规模耕作。
弥生人主要是公元前1000年左右从朝鲜而来,以小米和水稻农业为生计方式。
通过进一步分析日本九州的弥生时代农业人群的基因组,表明日本群岛从绳纹文化向弥生文化的转变过程中,不仅包含文化和农业技术的变革,同时也受到最终来自于中国北方农业人群的遗传输出。
所有这些证据表明,现在说日语、朝鲜语、通古斯语、蒙古语和突厥语的人有共同的基因和语言学上的祖先——大约9000~7000年前生活在中国辽河流域的农民。
兴隆洼文化与红山文化
也就是说,按照这篇论文,韩国人、日本人、土耳其人,还有中亚各斯坦(塔吉克除外)、西伯利亚的通古斯人,在遥远的史前史上,老家都来自中国东北,西辽河流域。
“我的家在东北辽河上,那里有那满山遍野的小米高梁”。或者说,“宇宙中心在通辽”。
这篇引发不小轰动的论文,其实只是研究者们计算研究成果的概述,没有具体涉及“东北老家”、“辽河上下”的考古背景 。
但对于对中国史前考古有所了解的人来说,辽河流域史前史,那就是大名鼎鼎的红山文化(公元前4000~前3000年,距今6000~5000年)及其祖源兴隆洼文化。
兴隆洼遗址,位于内蒙赤峰市敖汉旗宝国吐乡兴隆洼村东南丘陵西缘,是新石器时代早期先民聚落遗址,占地面积达6万平方米。
兴隆洼遗址有部分红山文化半地穴房址,但主体遗存经C14测定年代距今7470±80 ~ 6895±205年(约公元前5500~前4900年),与红山文化前身有关,可称“前红山文化”。
尤为引人注意的是,兴隆洼文化的历史年代,完美对应了计算语言学的泛欧亚语系的分化时间——距今6800年。
兴隆洼文化是目前已知的东北亚地区文明的第一个历史高峰,而后继的红山文化更为有名。
红山文化研究始于1935年对赤峰东郊红山的遗址发掘,此后发现并确定属于这个文化系统的遗址,遍布辽宁西部(辽宁朝阳)和内蒙古东南部(内蒙赤峰、通辽)地区,几近千处。
红山文化除了留下房屋遗址、陶器外,更留下了极为丰富的玉器。
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是世界最早且精良的玉器组合与工艺技术,逐渐向东和南传播。
大约从距今6000年前(公元前4000年)开始,逐步进入中原地区,形成龙山文化时期的玉礼器组合的体系性制度。
玉文化到达浙江沿海一带,代表性器物是余姚河姆渡文化出土的玉玦。在约5000年前的凌家滩文化和良渚文化达到史前玉文化生产的巅峰期。
并从中部地区进一步传到西部和西北地区,抵达河西走廊一带,以距今4000年的齐家文化玉礼器体系为辉煌期。
红山文化玉器文化还传播到今天的外东北(俄罗斯远东)、日本等地。
▎ 红山文化C形龙(中华第一龙)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塔拉出土,现藏于国家博物馆
与玉器齐名并存的,还有红山文化对龙文化的崇拜。这也是中华民族“龙”神话信仰的起源 。
农业在语言族群的扩散中发挥重要作用
红山文化时期,先民们不但创造了发达的手工业和内涵丰富的文化,更根源和最根本的是创造了农业生产。
2002~2003年,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植物考古学家赵志军对兴隆洼遗址进行3次考古发掘,获得经过人工栽培的炭化粟黍籽粒。经C14测定,这些炭化粟黍最早的距今7700~7500年。
结合定居村落的出现及成熟的掘土、谷物加工工具的制作和使用,证实距今7500年左右的兴隆洼文化已经形成了旱作农业系统。
2012年,兴隆洼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评选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从红山文化遗址来看,粟和黍是当时的主要农作物。
粟,俗称小米,其野生祖先广泛分布于欧亚大陆。粟的主要优点是耐旱,特别适合半干旱地区种植。
黍,俗称小黄米,其特性和地理分布与粟相似,都是C4类植物,也是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的主要粮食作物。
兴隆洼文化的先民们在长期采集、渔猎经验的基础上,驯化并成功栽培了适合半干旱地区的粟黍类作物,农业就这样产生了。
在欧亚大陆东端这片广袤的土地(今天我们叫它“中国”)上,形成了以粟作为核心的北方农耕文化与以稻作为核心的南方农耕文化。
对于国家形成之前的语言/族群传播,农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驱动因素 。
当一个群体自发或习得农业/畜牧技术后,由于有了稳定的生存资料来源,因此人口增长得更快,相对狩猎-采集者而言,具有明显的生产力-人口优势。
当人口增长到一定程度后,或者自然环境的变迁导致生存环境的人口容纳量减小后,该群体的至少一部分人口被迫向外迁徙,寻找新的生存环境 。
当他们迁徙到原来无人居住,或仅有狩猎采集者居住,或有农/牧民但生产力明显比新移民低的情况下,新移民群体具有明显的物质文化与人口优势,自然变化为优势族群、统治者,乃至土地的新主人。
这一过程,自然也伴随着部分原居住者同化入新移民的过程。总之,具有优势的移民族群,他们的语言与其他文化也随之传播开来,形成地理和人口的大规模扩张。
这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模型,语言不过是上层建筑而已。欧亚非大陆的另三大语系——汉藏、印欧、闪含,基本上都可以采用以上模型。
印欧语民族的祖先,生活在南俄草原上,他们是第一个进化出消化非人类乳制品(牛奶)乳糖耐受的族群,是第一个完成对马匹驯化的民族,更是最早掌握原始冶铁技术的族群。
铁骑加上马拉战车,让欧语民族横扫亚欧大陆,向东灭了印度河文明,向西打到大西洋边。让一大片地方都讲印欧语。
但此前阿尔泰语系的自身构建都不清楚,能否成为一种语系都非常存疑,使用族群的来龙去脉更是扑朔迷离,根本没有可能还原阿尔泰语系族群的历史变迁。
这篇论文完成了对阿尔泰语系基本的定性和定量分析,它可能颠覆了语言学界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认知,或许称得上是划时代的论文。
气候变化对族群的迁徙分化起到促进作用
但是,要进一步构建阿尔泰语系族群的历史变迁,还要补上论文研究者没有提到的另一个领域背景——历史气候变化。
距今11000年,最后一个冰期结束,温度快速提升,全新世开始,也为人类发现可驯化动植物和发明利用农业创造了条件。
距今8000~3000年的中全新世,是全球气温最高、气候最适宜农业耕作的时期,被称为“中全新世大暖期”,在中国称之为“仰韶暖期”。
那时的中国北方地区,平均气温比当代高3~4℃,气候温暖湿润,植物繁茂,水源充足,土地疏松肥沃 ,这些适宜的生态环境为农业的孕育起源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温床。
当时的农业自然条件要明显优于现代,伴随着降水增加和植被带的北迁西移,仰韶、龙山、红山等文化系统应运而生 ,中国出现了满天星斗的文明格局。
根据孢粉及其他古植物、古动物、古土壤、古湖泊、冰芯、考古、海岸带变化等多方面研究资料:
其中距今7000~6000年是稳定的暖湿阶段,即大暖期的鼎盛阶段。
距今6000~5000年,气候波动剧烈,影响文化发展。
距今5000~4000年,气候和环境较前改善恢复,文化遗址数量猛增。
距今4000年(公元前2000年,夏朝之前)左右,气候一度恶化,出现大洪水灾害,成为尧舜治水、诺亚方舟等传说的背景。
此后直到距今3000年(公元前1000年,西周早期)左右,气候仍相当暖湿(夏代、商代)。
到西周中期(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850年),一次迅速而强烈的降温(西周冷期)结束了“中全新世大暖期”。
气温可以为文明的诞生创造必要的条件,同时一个文明的陨落也和气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
因为原始农业是一种自然农业,它的兴衰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
以论文定下的年代结构,结合其他考古学等证据推测,随着人口扩张,从距今6000年开始,从西辽河流域的部分兴隆洼-红山人向西北迁徙至亚欧大草原。
公元前3500年左右(距今5500年),辽东半岛沿海农业人群给朝鲜半岛带去了小米农业和原始泛欧亚语 。
到了公元前1500~前1000年左右(距今3500~3000年),伴随着稻作农业的传播,大量农业人群从辽东、山东移居朝鲜,再从那里作为弥生移民来到日本列岛。
水稻的传播对原始日语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也导致了日语和朝鲜语的最终分离。
当然,由于考古遗址发掘不多,青铜器和铁器时代欧亚大草原上跨欧亚地区的人口流动、语言传播和文化变迁,尚存许多空白之处。
而另据吉林大学崔银秋课题组的研究表明,自红山文化时期开始,西辽河流域已受到向北扩散的黄河流域仰韶文化人群的遗传贡献;
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人群已经与仰韶文化人群在遗传结构上无显著差别,这显示出黄河流域农业人群对西辽河农业人群转换的显著影响。
但这种影响并没有体现在大部分的蒙古语和通古斯语人群中,与汉族有关的遗传成分在铁器时代才出现于蒙古高原和东北亚地区。
▎ 推测泛欧亚语系各语言支系在新石器(红色)和青铜时代(绿色)的地理分布
这也说明,原始阿尔泰族群(今天通古斯族群、蒙古族群和突厥族群的先祖)已经在距今6000~5000年开始,离开西辽河流域迁移。
在此后的气候变化降温中,他们在漠北草原应该遭遇了艰难时世 。但是随着获得来自西方世界印欧人的驯化马、牛、羊,幸存者们又转换生活方式,进入了游牧时代。
这些曾在辽河流域繁衍的部落,有的的往北跑到蒙古高原,再从蒙古高原跑到了现中亚,还有的一直跑到了小亚细亚 。
总之,从距今6000~3500年,阿尔泰语系族群随着农业文化的传播而依次离开了西辽河流域。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与其他文化发生了分化和融合,至今分布在从博斯普鲁斯海峡直到北海道的广袤空间。
由此大致完成了人类史前史的一块重要长期缺失拼图。再后来的历史,就逐次进入传说、史料时代,才开始真正进入民族国家的历史。
有人会问,土耳其人的面貌很欧化,怎么会和日本人、韩国人是同一起源呢?
因为突厥族群在西迁过程中,融合了众多印欧人群的基因,也完成了一次次文化的演替。另外,突厥族群不按人种划分,而是语族划分,也完全符合这次论文研究的主轴——语族的传播与扩散。
各类语言在扩散的过程中,自然会发生人群的基因交流和不同文化的演替。所以要结合考古学、分子人类学,才能完成历史的构建。
结论
同时使用语言学、考古学和遗传学方法做研究,并非这篇论文首创,但如此颠覆性的决定级成果确实少见。
由于研究小组的学术背景,在语言学方面的研究非常强,可能是对几十年来学界主流观点的一个颠覆,完成了阿尔泰语系的基本构建和溯源研究。
但在考古学、分子人类学上的,样本和证据还是太少,所能勾勒的族群变迁形态也显得粗糙 。因此,这篇论文涉及了跨学科证据共同研究,但还谈不上深度交叉融合。
这篇论文的另一个意义,是用数学和计算机工具跨越语言学、人类学、考古学等专业,提供了可靠的定量模型 。
实际上,任何社会科学在深度利用数学工具和计量统计之前,都不能称之为真正的科学。
语言学本身勾勒出古代人群的基本分化,要对泛欧亚语系人群的史前历史进行全面重建,还需要更多更丰富的考古学、古DNA材料。
但把这篇论文,和两年半之前《自然》的另一篇重要文章一起,或许已经大体搞清了亚欧大陆东端,也就是今天所说的中国人类族群起源和演变 。
另一篇重要文章是什么呢?是复旦大学所做的汉藏族群迁徙传播。同样是基于汉藏语系(汉语、藏缅语、苗瑶语)的溯源计算反推。
作为中华民族的主体,想必很多人对汉藏语系族群的历史变迁更感兴趣。这是解释还原“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的根本框架问题与答案。
限于篇幅,只能在以后有适合时机的时候再做介绍了。
从目前的基因分析结果看,到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4000年),兴隆洼-红山文化的人群遗传基因在当地都已被中原仰韶、龙山文化所取代。而兴隆洼-红山文化后裔,大都已作为泛欧亚语系人群,在中国历史开始之前,向东向西向外迁徙。
毕竟,6000年前还没有民族概念,更没有国家概念,大地上只有一个个部落或者部落联盟,可以到处迁移,这种史前迁移与现实的当代民族国家版图划分无关。
总之,通过语言学、考古学和遗传学三方面的融合交叉,用数学工具从不同的角度对古代人类的史前变迁进行追溯,可以更加全面还原历史上不同人群的迁徙、融合历史。
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必将在还原人类历史等诸多方面大有作为,会得出更准确,更令人耳目一新的历史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