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彦浩特羊杂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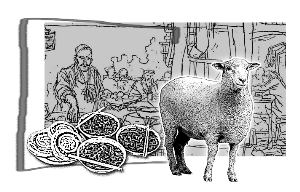
定远营(今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镇旧称)还是定远营,城门和城墙又一夜间奇迹般地矗立起来了。不过,那棵大树是永远地消失了。大树底下的人聚了又散了,不知经过了多少代。古城名字早已改成了巴彦浩特。这几年人们目光盯上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于是便想起了定远营这个已经久远了的名字,想起了定远营古城(1730年始建,1733年落成)许许多多的事情。
早些年间,巴彦浩特时兴吃的是那种汤汤水水、漂着羊油辣子、顶上缀以香菜末的羊杂碎。舀在碗里,红是红,绿是绿,香气扑鼻,煞是诱人。另外,那时卖羊杂碎是挑着担沿街叫卖,一头是很厚实的黑瓦罐,一头是碗筷等杂物,伴着一声声长长的吆喝,在二道巷子、牌楼下回旋。不像现在是在铺子里卖,等客上门,有点守株待兔的味道。就是前十几年,一位姓闫的老汉在头道桥用白帆布围了一圈,里面摆了几个小板凳,人们坐在那里唏溜唏溜地吃,辣辣的吃,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吃出巴彦浩特羊杂碎的正宗味道来。
这些年,在巴彦浩特的街上仅存的羊杂碎馆也就三五家了,不知是人们的口味变了还是生活水平提高了,人们几乎将这道美味逐渐淡忘了,就是进了羊杂碎馆的,也多是外地游客或牧区来的老人,图的是尝口鲜或回忆一下当年的老味儿。但是羊杂碎还在继续,还在消费,只不过吃法变了,已经升级换代。人们在大馆子或酒店派头地要上一盘辣爆羊头或清炒肚丝或锅仔羊杂,重温一下久违了的感觉,他们痴迷的是觥筹交措,醉眼朦胧的气氛,最后还不忘喊店家一嗓子,“羊脑子上了没有?”最让人难以释怀的是巴彦浩特人对血肠和肉肠的理解和依恋,也就是这两道经典蒙餐的粉墨登场,才大大丰富和凸显了蒙餐羊杂碎系列的光辉,然而这两种美食却是阿拉善古已有之的。特别是在遥远的牧区那些遥远的年代,人们吃着装了碎肉的灌肠,嚼着羊肚,吃一块切一块,讲究纯粹地手工操作,别人割下来就没味道了。一口烧酒一口血肠,一口烧酒一口羊肚,一口烧酒一口沙葱,唇齿留香,满嘴都是浓郁的戈壁滩散发着原生态气息的美好感觉。
当年在定远营牌楼下或二道巷子那个戴黑毡帽老汉的羊杂碎却是羊杂碎中无以伦比的精品,特别是汤好,老巴彦浩特人好的就是那口。他的那只黑色砂罐永远是热乎乎的。他的勺头永远那样精准,舀得稠稀得当,品种均衡,冒尖的总是馋人的肚丝和羊脸,而肝或肺则总潜伏在碗底,那时的香菜也格外绿,并具有浓浓的香菜味,不像现在香菜没个香菜味儿。记得那时,卖羊杂碎老汉的挑子边,总围满了吃的和看的人。吃时要蹲在那里,从从容容,唏溜唏溜地喝汤,慢条斯理地咀嚼,还要就上一个茴香饼子,三角的,这就是吃家了,谓之正宗;不会吃的则是站在那里狼吞虎咽,风卷残云,啥味没品出就已经碗底儿朝天了。而旁边一定有几个光屁股小孩在咽口水,或跑回家问妈要钱,要不上就哭。还有,呼和浩特的羊杂碎也颇具特点,着色深红不说,调料中有大茴香,还要佐以酱油,而又很少辣子,但土默川的父老乡亲依然吃得激情流溢,真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
那时,我住在巴彦浩特老城二道巷子一间大杂院,也是四合院。每当晨起或半晌,最瞭人心魄的便是卖羊杂碎老汉那声纯正当地口音的吆喝:“羊杂碎噢……”这也是当时巴彦浩特唯一的带有市场气息的声音,一种原汁原味的贺兰山以西的叫卖。而决不是现如今用电喇叭加工过的卖酸奶卖便宜货的南腔北调。
我在巴彦浩特老城里短暂且又深刻的栖居经历,给我的童年打上了深深的西部印记,至今我还痴迷那条幽深幽深的、洒得湿漉漉的二道巷子,怀念卖羊杂碎老汉给古城送来的美食和快乐。
现在羊杂碎之于我已经不香更不馋了,而我就是从定远营的类似瓮城的城门走出,就是吃着那种漂着羊油辣子碧绿碧绿的香菜的羊杂碎走向遥远的现在。
我是吃着羊杂碎长大的,那时的羊杂碎,就是我心中的大餐,心中的希望和盼头,总想着到什么时候能敞开肚子吃够羊杂碎,能天天吃、顿顿吃就好了。现在不要说羊杂碎,羊腿也不怎么稀罕了,还怕血脂、胆固醇太高,得了高血脂病呢。文/董培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