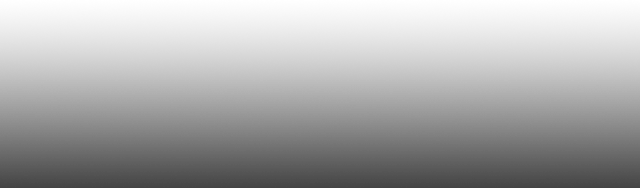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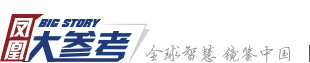 No.49
No.49
林达看古巴(三):
终将告别革命之苦
Go To Cuba Before the Americans
作者:林达 2015年6月2日到了古巴,发现它的网确实是不普及的,就连涉外旅馆,也各不相同,中等城市的涉外旅馆不准许旅客用自己的电脑上网,必须买票上它的电脑;哈瓦那的涉外旅馆已经有了WI-FI,可以用自己的电脑上网,去买密码必须登记护照。先富起来的人用上手机,但是手机和上网,还都不普及。不过,已经有人因为写博客被捕后又被释放。我对古巴朋友说起这个事情,说我看到新闻,那个博客手是在国外压力下释放,他很不买账地回说:“明明是我们这里自己抗议后释放的。”我说“好吧”。
从《天使报喜》看个性恢复
变革也发生在艺术领域。古巴女艺术家安东尼娅·爱丽兹,闻名整个拉丁美洲。她的现代画介于变形写实和抽象之间,风格浓烈、造型怪诞,有着极强的隐喻、象征和黑色幽默。她的《天使报喜》画在六十年代,是一副骷髅骨架的“天使”,飞来告知在缝纫机前的圣母,据说,是在通知她,已经怀了“革命”这个胎儿。她的《听众》,是一个空空的讲坛下的一群民众,构图和色彩极具她的个人特色,据说是在表现在官方话语之下,听众的被动和个性消亡。
安东尼娅·爱丽兹在六十年代的这一系列创作,当时受到古巴政府的批判,最终她不能继续展出作品,还是可以在学校教艺术课,她此后长期停止绘画,转而研究和教小孩子们古巴手工艺。她最终移居美国,成了迈阿密那个“小古巴”的一员。在美国她重拾画笔,直至去世。
现在,哈瓦那的国家美术馆展出了安东尼娅·爱丽兹的系列大型作品,包括最有名的《天使报喜》和《听众》。今天,讲解员已经在坦率讲述女艺术家曾经和革命政府的冲突、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和她的海外生涯。在国家美术馆,也陈列了一幅现代画《革命家庭》,表现了古巴革命初年的一个家庭在革命装束下的刻板。
民间NGO开始活跃起来。在哈瓦那,有一个瘦小的美国女人办了一个小小美国书店,是以文化中心的名义做的。她是多年前爱上个古巴人,已经一口地道哈瓦那口音。书店临街,去的那天那天阳光灿烂,各色美国杂志,包括《时代》这样的新闻周刊,就放在临街院子的一个架子上,谁都可以进来看。杂志都是西方游客的捐赠,她说很多游客回去后给她寄书,我问她能收到吗?她说至今没有问题。我和她提到一百年前巴黎的“莎士比亚书店”,她马上笑了,说她知道。她晒得黑黑的,一看就是女汉子类型。我又问了另一个古巴人,他也说海外寄书似乎至今还没有问题。纽约的犹太人已经在哈瓦那建立了犹太文化中心,里面年轻的现代舞者已经走遍世界在演出。

价格介于古巴比索和库克商店之间的自由市场,工薪阶层还是觉得价格昂贵。
一开放,虚幻的平等就立即打破
古巴一向骄傲自己达到了平等的目标。但是强行一律贫困、也遏制个人经营、致富才能的制度,一经开放,虚幻的平等立即就打破了。
开放必然导致一部分人率先脱离了原先的贫困,可是,很多人还留在贫困中,那就是旅游区域背后的那个破败古巴。社会差距立即拉开了。古巴社会再三强调的无歧视种族平等、种族收入一致,也被现实打破。古巴的黑人和黑白混血(在美国都归在黑人一类,在古巴称呼分开)比例非常高,超过人口三分之一。而外逃后定居海外的古巴人,也就是海外汇款人,他们绝大多数是白人。家庭汇款令第一波收入差距拉开。旅游业兴盛之后,虽然一些黑人能够靠音乐舞蹈的表演进入旅游业,但是能够有资本和技能建起私人企业的,黑人比例明显远低于白人。
去古巴之前就知道,古巴号称是当今世界上唯一还在实行货币双轨制的国家。一开始,是容许私人接受国外汇款和和使用美元,同时在全岛建立了一批美元商店。但是后来改为美元必须换成库克(CUC)才能使用,美元商店又改成了“库克商店”。 外国人进入古巴也一样,不是换为当地古巴人使用的古巴比索(CUP),而是只能换库克。我经历过中国的外汇券时代,理所当然做了类比。到了古巴才知道,相比从1980年开始使用了将近十四年的中国外汇券,库克有本质不同。原则上说,二者都是因为长期闭关锁国、在突然开放时,试图作外汇管制。但是,中国启用外汇券的重要起因,是有一系列“内禁品”不容许中国人购买,所以设立了中国人禁止入内的“友谊商店”,外汇券杜绝了中国人用人民币私下托海外人士购买“内禁品”的渠道。但是原则上不算两种货币,因为外汇券和人民币的币值是等值的,只是在黑市略有差异。古巴的货币双轨定价令人难以相信,库克的币值是古巴比索的二十五倍,在换美元的时候,古巴政府还额外征收百分之十的税,加上手续费,所以,最近的实际比价,就是一美元换0.873库克。
更大的不同是,古巴遍布分别使用两类不同货币的商店,收古巴比索的商店几乎什么都没有,还挂着小黑板,写明用 “俄国本子”的本月可购商品的限量是多少。而大量库克商店里,商品正常而丰富,欣欣向荣的样子。古巴原来是没有税收这回事的,现在只要是国营工作以外的任何收入,就是百分之十的税收。税收甚至包括海外亲友的汇款,既然收到汇款必须换为库克,一换,就被收去了百分之十二点七,很雁过拔毛的感觉。
外国游客的费用,住宿吃饭交通等等,都和在自己国家的花费差不多,有时甚至更贵些。在去古巴之前我想过,游客应该可以去换点古巴比索,开销就便宜啊。去到比索商店,才知道自己的想法很可笑。真正古巴人光顾的收古巴比索的国营商店,游客买不成,需要“俄国本子”,更何况,比索商店里空空如也,你要的东西什么都没有。在小广场上,几次遇到索要肥皂的老人;对那个广大劳动人民的“古巴比索阶层”,圆珠笔、打印纸,电池,都是紧缺的东西。后来发现,唯一的可能,是先在黑市用库克换古巴比索,再去自由市场买些肉和蔬菜水果,它的价格介于比索商店和库克商店之间,但是一般古巴人还是嫌贵。而“库克阶层”包括庞大的有海外汇款的家庭和有能力赚外汇的人们。
人人想往“库克行业”靠
旅游业是一半以上的国家收入,所以库克阶层在迅速扩大。这也是古巴政府、民众都热切盼望美古建交的重要原因,对政府,它是给国家送来硬通货;对民间,它给更多人带来立即“暴富”的希望。
两个阶层的差距,不仅是两种货币之间二十五倍的差距,还有一个鸿沟:一方不仅低值,而且收入量的低端封顶;一方是高值而收入量普遍高且不封顶。
尽管古巴官方解释说,你们看到的所谓低收入是没有看到它事实上隐含的高收入,例如,这个低收入要加上他们都有自己的住房,没有美国人买房、租房压力;他们有美国人没有的公费医疗、公费教育,那又是一大笔钱。还有退休金等福利。所以,其实不低。站在古巴,亲眼看到那个古巴比索阶层的生活,你会知道这没有任何说服力。古巴和类似在改革的国家显著不同,它“相对暴富”的人口比例大,是瞬间出现的:一有政策准许收取海外汇款,近三分之一的家庭就突变了。
可是,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没有学会游泳的那些国民,国营企业的工人、雇员们,在担心再改下去,他们连基本保障也没有了。
例如,现在的“俄国本子”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全部口粮都是超低价,而是一个政策下来,就变成一部分超低价、一部分显著提价;再不够、或者要吃得好一些,就是进自由市场,在那里,照古巴人的说法,就是“钱说话”。至少到今天为止,劳尔·卡斯特罗还是坚持“三个不变”,就是免费教育、免费医疗、以及“俄国本子”上的基本供给和退休金这样的基本福利等不变。公家雇员是不交收入税的。但是,交着百分之十私营税收的人们,却认为这是制度的不公平,自己勤劳、“养了懒汉”,所以要求经济制度向着市场化的方向,有更多的推进。

使用古巴比索的商店,需要被称为“俄国本子“的配给本才能购买低价配给品的商店。
一半以上的古巴人还在原来的国营工作中,挣着两百至三百古巴比索,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是因为“懒”,而是无奈。只要有一点点可能,谁不希望往“库克行业”靠。听过一群美声无伴奏合唱的国家演员的演唱,问下来,工资是二百八十古巴比索,也就是十一库克多一点。但是,唱歌是旅游业的相关行业,只要有空,找个空屋就可以给游客表演,然后卖CD或者DVD,卖出一张,就比一个月的工资还多。所以,不断唱,不断卖CD。由于二十五倍的荒唐比价,普通古巴人一年甚至几年的收入,那些和旅游相关行业的人,可能几个小时就挣出来了。在古巴的库克商店,看到在卖像模像样的出租车黄色顶灯。一些有私车的人,随时给自己车顶上放上个,就可以冒充合法出租车拉外国游客挣库克了。游客也被警告说,这样的车有时是不安全的。
文化还在,记忆也在,基因都在
我遇到一对年轻男女的黑道或者“准黑道”诈骗,虽然一开始就感觉来者不善,好奇心过重的天性还是令我一边冒险一边防守地跟他们进了一个当地人的酒吧,极简陋,人造革的折叠椅处处破出海绵,半片墙上是几十张黑白革命老照片。他们没有很多耐性,很快摘下面具露出真相,我一个对四个加一个旁观者,僵持到最后侥幸全身而退。最长见识的,是我出来立即报警,才发现年轻的警察根本不敢和他们较量。这时我想起那个台湾女孩告诉我的故事,她的德国朋友如何在古巴被骗光和痛殴。夜幕降临,我回到海边的安全地带,独自看着乌云压下落日、海礁一次次击破巨浪、落日余晖中炸出万千金色细片碎沫,平复心情,也回想如何有人飞速向我掀开和拉上这座美丽城市的帷幕一角,让我不幸或者说有幸看到幕后黑暗的一现。
这个由六十年代建筑法规保存下来的老哈瓦那,让我感觉,和其他国家的革命相比,古巴隐隐有它“不同”的一面。我去过哈瓦那的哥伦布纪念墓园,这是世界上最大墓园之一,一百三十五英亩,它建于十九世纪末,里面有各个时代的名人墓地,有着精美绝伦的大理石雕像。这样的墓园在古巴各个城市都有,我去过的中部城市辛弗戈斯(Cienfugos),它的墓园也是这样,只是没那么大。那些雕饰最美的墓,自然大多属于革命前的富人和阶级敌人。我问过看墓人,问过几个古巴人:这些革命对象、甚至敌人的墓,怎么就没有被砸掉呢?他们都万分惊讶地看着我:“这是逝者啊!怎么可以!”眼神中的意思,好像我怎么就邪恶到这个地步,能提出这样的问题来。我只好难为情地落荒而逃。这是一个宗教根源深厚的国家。一个女教授说,她的祖母是虔诚天主教徒,做梦也想不到,孙女会去嫁了个共产党员的犹太人,而他们的女儿,又决定“回归传统”,十年前进了修女院。
“特殊时期”开始的显著社会变化之一,就是教会的迅速恢复和扩大。教会有一些民间自助的作用,他们能够从国外兄弟教会得到一些援助,就在“特殊时期”的饥荒中接济饥民;也在私营企业起步的时候,做管理培训,开课教授会计等课程。但是,开放以后,作为信仰的宗教精神迅速回归,还是非常明显。在劳尔·卡斯特罗发起改革建议大讨论的时候,一个很热的议题是要容许教徒入党、或者说容许党员信教。在这种很深的宗教根基下,进入改革时期后,教会和政府的关系迅速改善。虽然天主教会也不断对政府有批评声音,但是,双方总的来说还是良性互动。教皇保罗二世和教皇本尼迪克特十六世分别在1998年和1912年访问了古巴。在哈瓦那的主教堂里,还留着当时教皇访问的照片。在这两次访问中,教皇都分别会见了菲德尔·卡斯特罗。现在,古巴天主教的主教都由梵蒂冈任命。天主教会充当了民间社会和政府之间的协调,2010年至2011年间,经天主教会的斡旋,在2003年被判的那七十五名改革建议者,和之前被判刑的一些异议人士被释放。现在,天主教会和政府维持一种谨慎互动的关系。

商品丰富、高端大气的库克商店。
旅游业,那就是革命前古巴的基本生活。美国人留下的大酒店,因为都被收归国有,有人管修,所以里外都保存得极好。赌场都在,只是一直空在那里。进入古巴国家大饭店,大堂里若要拍个类似“布达佩斯大饭店”的电影,不需要布景,只要把穿T恤的西方游客赶出镜头就可以了。跨出大堂,就是长廊下的室外酒吧。也有规范标准的侍者,穿行在草坪上、临海的餐桌间,乐队无所不在。老乐队,萨萨舞,无伴奏合唱,现代舞,美国黑人的说唱Rap,这是一个酷爱音乐舞蹈的国度。
回来以后我听了一场“甲壳虫”,在场的大多都是美国老人,那是他们年轻时的偶像,四十年了。可是,说起来真是难以置信,“甲壳虫”红遍全球后的几十年,古巴听“甲壳虫”一直是违法的。近年刚刚准许可以听,“甲壳虫”立即红遍古巴。旅游业需要英语,在古巴学校里,苏联一消失,俄语立即被抛弃,而在大学里,老一代不乏英语流利的教授。
一个前英语教授告诉我,在革命后的古巴大学里,虽然重俄语,英语教学没有断过,只是规定不准许教“听、说”,只能教“阅读和写作”,但是,他一口流利美式英语对我说,“我从来没去过美国,我的英语就是古巴老师教出来的。我们当然会自己学着听和讲。” 国家大饭店里有个历史画廊,都是他们引以自豪的名人住客,除了几张今天政治领导人物,如习近平、潘基文、查韦斯等国家领导人的鲜亮彩照之外,满墙老照片,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在这个大饭店住过的老歌星、艺术家、球星和各色名人。整个审美趣味,令人不可能不联想到上海。上海不是中华文明的京城,上海没有故宫的底气,它曾经是个不起眼的小渔村。
上海和北京不一样,那种不一样不是北京人眼中的不一样。它建立和发展就是殖民的结果,洋人造就了上海,对老一代上海人,你怎么教育都没有用,外滩的高楼和西区洋房,生生摆在那里。犹太人一直感激上海人在二战期间对他们的接纳和大度,他们不知道,这是太简单太自然的上海逻辑:他们崇洋,严格地说是崇尚西洋文化。 东洋是中国的学生,不在他们眼里。而老上海人又是人格分裂的,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带来根深蒂固的乡土根基,他们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当西方被封闭在外面,就像外星球一样遥远,而轻视自己文化根基当然是个罪过,崇洋媚外是个沉重而不想承认又摆脱不了的帽子。而那个民间古巴,他们理所当然就“崇美媚西”了,他们理直气壮,西方文化本来就是古巴人的文化源头,他们说的是西班牙语,美国文化是现代古巴的根基。
整个哈瓦那,他们的首都,他们历史上引以自豪的方方面面,都和美国文化有割不开的联系。哪怕在他们封闭的年代,美国从来没有远去,那是三分之一古巴家庭有亲人居住的地方,是他们向往的天堂(事实上不是天堂那是另外一回事情)。这就像在改革开放前,你再怎么对广东人进行革命教育,不论广东政府如何斥责港英帝国主义,广东民间没有一刻停止过对香港的向往。所谓在台面上“对不对”,常常是一个“政治正确不正确”的政治判断,而民间那种自然感情,不是政治指导可以阻挡和扭转的,它暗潮汹涌、势不可挡。这是美古关系在古巴民间的现实基础。

城里人被安排下乡协助收获。
菲德尔·卡斯特罗已经是“历史”了
我对一个非常聪明的古巴朋友说,“我来之前问过朋友:我要去古巴了,你最想知道的是什么?朋友回说:最想知道菲德尔·卡斯特罗去世后,会发生什么。”古巴朋友狡黠地笑了笑:“几乎每个西方人来,都会问这个问题。看了那么多,你已经知道答案了,”他说,“我总是回答他们:‘会怎样?会有一个葬礼。’”在古巴人心中,菲德尔·卡斯特罗已经是“历史”了。
他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也已经明确表示,他将在2018年正式退休。在2013年,古巴的领导层已经大量换成年轻专业人员。何塞·马查多·番多拉,成了现在的第一副总统,也是呼声最高的劳尔·卡斯特罗接班人。在古巴,这还是第一次,有一个革命之后出生的人,进入最高领导层。
古巴的革命初年,那些选择打回来、最后死在猪湾的古巴人,那些跑到山上去打游击打了几年的古巴人,现在去看,他们几乎命中注定在当时不会成功。当时有的是革命支持者,革命掠夺了别人的财产分给许多人,他们会跟着革命和你拼。在猪湾博物馆里,一排排的“烈士照片”,印象最深的是黄黄老照片上的一堵墙,歪歪斜斜的“菲德尔万岁”几个大字,是一个革命士兵临死之前用他的血涂在墙上写成。但是现在,都是八零后了,他们的童年记忆就是“特殊时期”的饥饿和改革开放市场化进程的生活改善,面对猪湾博物馆一进门的大字“社会主义赢了”,他们已经有了自己不同的理解。历史自有它的逻辑。
以前,美国和古巴之间的任何互动都是秘密,都是在街头巷尾传递的小道消息;现在,每个古巴人都知道劳尔·卡斯特罗即将访美,都知道他们要讨论人权议题。一个古巴人对我说,古巴政府根本不会担心这样的话题有什么压力,肯定是,你说人权是“公众的表达自由”,我就告诉你人权就是生存权,就是让老百姓吃饱。这是古巴在联合国多少年来已经应付自如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但是回看改革前路,正是“公众表达自由”的缺乏,使得古巴改革走了很多弯路也有了多余的不确定性,因为它全靠高层拍脑袋式的“顶层设计”。
现在,危机显然存在。在这样收入相差极为悬殊、高度分裂的制度下,你可以想象官员腐败是个必然。因为官员公务员也是拿古巴比索的工资。在改革前的1989年,已经有第一代老革命的高官因贪腐被判处死刑和长期徒刑。现在贪腐普遍,是一个众所周知的现实。同时,古巴政府也越来越看到,这个举世无双的货币双轨制是一个地雷。非常显然,它貌似是社会的开放与变革带来的新问题,其实是解决前“非正常社会”遗留问题的特殊处理造成。古巴政府知道早晚要解决,正在准备货币合轨,取消库克,古巴人都在说,“也许,就在下个星期”,各个商店里已经都可以看到新古巴比索的宣传画,上面是一张张古巴人从未见过的高面值比索。
看来所谓货币合轨,就是取消库克。大家都很紧张,这是要高通胀吗?自己手里的积蓄要贬值多少?因为现在通用的老比索,面值是最高一百,宣传画上的新比索是最高一千。但是大家又只能消极等待那一刻的到来。这样影响大众生计的各种政策在不断出台,可是大众是被动的。古巴人只能期待不要一觉醒来,天上不是掉下一块馅饼而是一块陨石砸下来。
在这里,却一次次听到古巴人讲他们不久前的过去,饥饿,没有吃的,多少人抱着块木头投向加勒比海。古巴本来是一个太容易过好的小岛。它的旅游资源堪比取之不尽的油井。今天,大多数古巴人对古巴的未来前景相当乐观,没有理由不乐观:“我们没有民族区域问题,我们是个小岛,又马上要和美国复交了。”
一个古巴女教授说,“我们古巴人是相信要来的自然会来,等着好了。你看,美国人不是给我们等回来了吗?”这算犬儒吗?还算是智慧?同时,古巴当然也有意见相反、相信要积极参与推动改革的人,在美古宣布建交之后,还有人因策划游行被逮捕。
一个本来应该很容易生存很容易过好日子的小岛,在世界大局的起起伏伏中,居然风云跌宕。各类悲喜怒哀乐的情节,一个都没有缺。我想,既然它如此遭遇走到今天,它必要走完自己的最后一步,完善内在制度的改变。
古巴,祝你走运。
凤凰大参考专题文章为本栏目特约,转载请务必注明来源及作者姓名,违者必究。
林达
著名旅美作家,已出版“近距离看美国”系列《历史深处的忧虑》、《总统是靠不住的》、《我也有一个梦想》以及《历史在你我身边》等书。

凤凰资讯微信
扫描微信
关注凤凰资讯
凤凰评论出品
策划:易心
栏目合作:zhaoqm@ifeng.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