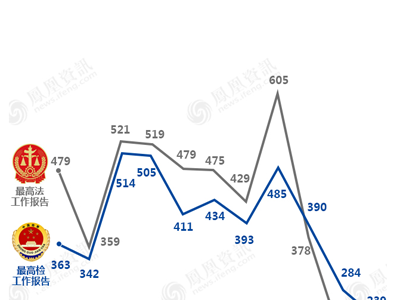邓峰:收拥堵费别只谈“国际接轨”
3月9日,交通运输部部长杨传堂在经过“部长通道”时表示,是否收取交通拥堵费,主体责任是城市,各地情况不一,应从本地实际情况出发来制定相关政策。而此前在7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北京代表团开放日上,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常务副市长李士祥称,正研究论证收取拥堵费。
征收拥堵费是不是治理雾霾和治堵最后的手段?是否符合法律上依据?如何处理公车问题?凤凰评论就此采访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邓峰。

访谈嘉宾:邓峰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凤凰评论时事访谈员 叶鹏
征收拥堵费是偷懒的管理方法
凤凰评论:交通对于一个城市来说,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如今北上广等特大型城市陷入“堵城”困境已是不争的事实,虽然这些城市已采取摇号购车、尾号限行等手段,不过好像改观不大。在这种现状之下,征收交通拥堵费是不是确有必要?
邓峰:没有什么必要,不具备合理性,也不具备可实施性,而且是一个缘木求鱼的做法。有关部门连实证数据都没有,究竟堵车的原因是什么,没有任何的调查研究,仅仅凭想象或空理论,就直接做出了这样的决策。大部分研究交通的学者都不会认为这是一个解决办法,不仅是从技术上的角度,而且从交通经济学和法律规制的角度,也不支持这种方法。
从科学决策的角度来说,出台拥堵费的方法来治堵,最起码需要两个逻辑支持:第一,拥堵的原因和上路汽车的数量之间存在更紧密的因果关系;第二,采用收费方法能够有效降低拥堵,尤其是有效区分拥堵的造成者和受到拥堵的困扰的人。
这两个因果关系,在北京政府的决策中并没有任何调查研究的数据支持。如果按照其他国家的经验,以及交通经济学等学科中的既有研究,这两个因果关系都不能简单成立。
凤凰评论:很多人认为我国的城市交通拥堵很大程度是由于道路规划不合理以及管理粗糙造成的,现在出台拥堵费举措是在转嫁责任,对此,你怎么看?
邓峰:拥堵和道路设计的关系最为紧密,现在的城市规划造成道路拥堵是一个权力配置的制度问题。比如交通部门常常抱怨,道路和交通规划在城市小区的建设中常常没有交通部门参与,直到堵起来才想起来交给交通部门来解决。这是因为城市规划的权力和交通规划的权力之间存在着配置不合理问题。在北京,诸如天通苑、回龙观、世纪城这些小区的设计显然是缺乏交通规划的。
改变拥堵同样可以采用改变道路设计的方式,这取决于具体的情形,但北京市仍然有很大、很大的改进空间,比如高架桥长通道的再建设,道路设计的调整,工作区和居住区的微调等。
转嫁责任的说法可能有些不太切题,拥堵也是一个既存的事实,尤其是在北京,这种压力,无论是来自于哪方面的,也的确比较大。不过,讨论一项公共政策的实施,还是应当的考虑有效性(effectiveness)和有效率性(efficiency)。拥堵费能够起到的作用,简言之是效用低、效果短,但是成本高,不去考虑其他的替代方案,而简单采用类似征税的方法,是偷懒、偷工的管理方法。
收费制度的代价是影响公平和平等
凤凰评论:从经济学理论上分析,城市道路并非是某些人认为的纯公共品,而是介于纯公共品和私人品之间的准公共品,不应完全由政府免费提供。是不是说治堵问题也就可以通过价格杠杆来调节?
邓峰:理论上采用提高成本,抬升价格,可以改变需求。但具体到交通经济,随着具体情况,问题就会变得复杂很多。
首先,收费并不是提高效率和创造财富的,而只是产生转移效应,收费不过是政府将堵车的等待时间变成了庇古税(由福利经济学家庇古针对环境污染所提出一种经济手段,意思是指谁造成的外部性谁交税或者谁受污染谁得到补偿)的方式收取了费用,甚至这种收费对象都没有区分造成堵车的人和受到堵车的人;第二,如果从行为经济学角度来看,当采用定价机制以罚款的方式来解决集体行动的问题,罚款最终会转变意义,变成一个价格,即你支付了价格就可以违规;第三,除非采用动态价格(浮动收费),采用统一标准的静态价格,只是减少了行驶,并没有提高社会效率,道路的正常通行难道不是和正常的经济效率、生产、交易等有正相关的关系吗?静态价格收费更多是对弹性需求而非刚性需求起作用。但是动态价格不具有可操作性。
其实不用诉诸于高深的经济学争论,已有的例子已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地铁提价之后,并没有降低拥堵。同样,现在采取的每周限号一天的措施,违规之后三个小时内罚款一百实际上形成了一个拥堵费,并且这还是建立在提高停车收费基础之上的。这些已有的经验表明采用收费的方法没有起到预期作用,但是政府既没有检讨,没有解释,也没有公开收取费用的去向。甚至已经被证明是无效的规制仍然在继续之中。
凤凰评论:拥堵费属于行政收费行为,涉及到对公民财产的征收,必须恪守合理行政行为。目前,如果要征收拥堵费,现在是否有法律上的依据?
邓峰:收取拥堵费并没有现行的法律依据。如果回到法律,因为法律包含的价值争论更多一些,问题就会更多。比如反对收费的非经济学观点中有一个很强的主张就是行车和权利是联系在一起的,既然宪法规定了工作和休息的权利,那么在工作和休息之间利用公共产品通行就在宪法权利中可以推导出来。限制这种权利既需要在实体判断上,证明公共利益得到了提高和促进,也需要在程序和合法性上获得即有的法律支持。
了解这一点,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就可以知道。1984年,我国交通部在对高速公路收费的时候,采用了“级差效益”的表述,意味着在国道等免费道路上通行是默认的权利,在高速公路上通行时因为获得了相对更快的速度,而需要支付差价。在相同的方向上基本存在着收费和免费并行的道路,这是我国法律实践中普遍接受的理论。在特定区域进行收费,对该特定区域内的拥有车辆的居民继续加码收税,收取拥堵费并没有这样的理论依据。同时,还将车流量转嫁到了非限制的领域。
不仅如此,从法律视角的话,公平和平等显然也是法律的重要价值,那么采用收费方式去治堵,代价就是影响了公平和平等。首先,统一收费并不能区分造成拥堵的人和受到拥堵的人,不分青红皂白地收费,这当然有违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原则;其次,收费对不同财富的人,不同需求的人会造成歧视。而且最关键的是,这种措施和有些规制不同,并不能真正创造社会财富的增加,而只是一个等待时间的货币化、政府收入的提高和财富转移。
这种公平和平等问题就更加突出,一个是大量低收入居民居住在一环、二环以内,一个是公车的存在。公车的存在强化了平等问题,也更多改变了需求弹性,公车支付的费用仍然是来自于纳税人,这只能造成双重征税。
不能简单的拿国外例子对比
凤凰评论:在社会公共治理上,哪方面出现了问题,政府就很容易想到收费,比如公众普遍关注的社会抚养费、交通罚款、燃油附加费、高速延期收费等等。交通拥堵费似乎也是如此,你觉得背后的根源在哪里?
邓峰:不能把这些例子都简单的归到一种情形,这些情况是不同的,拥堵费和其他的收费还是有所区别的,拥堵费的不合理在于前面所提到的这并不真正产生社会财富的增加。
当然,我们也的确存在着这种行政管理的惯性思维,采用收费、征税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首先是公共管理和行政之中,缺乏对法律的尊重。比如拥堵费收费缺乏依据,现在却要采用,这本身就不尊重法律。不尊重法律,如何制约呢?
其次,城市内的道路是否适用公路法?公路法明确规定公路收费全部用于公路建设,尽管可能会引发不平等的问题,但也大致相当于肉烂在汤里。现在收取的很多费用,都没有信息公开。如果没有机制约束,权力行使不公开透明,当然就会引发滥用。
再次,我的观点是,如果经过科学论证,在某些情形下,通过收费是可以起到促进社会整体效率提高,社会财富增加的情形。但政府机关会有一种惯性思维,就是首先想到以收费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恐怕归根结底还是一种懒政,缺乏问责的原因。
凤凰评论:谈到拥堵费,很多人就会拿出国外的例子,比如新加坡、意大利、罗马等这些大城市。但这些“洋经验”是否就能适应我国呢?
邓峰:我们不能简单地拿国外的收费例子来“国际接轨”。事实上,拒绝采用收费的更多更普遍。常常作为成功的例子,是英国伦敦在2003年在8平方英里(大约20平方公里)的中心城区,按照每辆车每天5英镑,不论是停车还是行驶来收取费用,有统计表明,车流量下降了15%,拥堵下降了30%,但是到了08年拥堵就回来了。官方解释是这时候人们转而步行或使用自行车,也会造成新的拥堵。姑且不考虑其他情形,北京的街区和伦敦的密集程度更不相同,如果转向电动车、自行车和步行,会造成更大的居民不方便和新的拥堵。纽约也曾经想复制伦敦的经验,但最终经过研究和居民抗议,不了了之。
美国国会在2009年发布了一个研究报告,这些情况在其中都有分析。国会的预算办公室充分研究了已有的收费经验,最终建议并不采取收费方式降低拥堵,其中最重要的一些结论是:第一,伦敦采用了拥堵收费,但效果并不如提高车位费;第二,存在着其他更好更具有性价比的方案;第三,造成分配问题、转移效应,对穷人和富人的影响是不同的。
去年12月3日,北京市交通委发布,2016年将研究试点征收拥堵费,并针对小客车、机动车实施更加严格的限行措施。但至今看不到北京市政府有什么信服力的数据或研究表明这种措施可以起到作用。![]()
[责任编辑:叶鹏 PN043]
责任编辑:叶鹏 PN043
往期回顾
-

邓峰:收拥堵费别只谈“国际接轨”
出台拥堵费的方法来治堵,最起码需要两个逻辑支持:第一,拥堵的原因和上路汽车的数量之间存在更紧密的因果关系;第二,采用收费方法能够有效降低拥堵,尤其是有效区分拥堵的造成者和受到拥堵的困扰的人。
-

杜鹏:政府补贴养老院不能公私有别
杜鹏认为应尽快推进养老金全国统筹,财政要为养老保险进行兜底,让公办的管理服务扩展到兼并其他性质的养老院,形成集团式管理等等方式。
-

杨燕绥:中国人接受延迟退休有个过程
人口老龄化真的来势汹汹,对企业发展成本、劳动力市场供给、个人就业、养老金制度、养老服务业、社会文化,以及两代人的利益关系等有什么影响,需要一个认识过程。
-

郑秉文:以房养老在中国“水土不服”
住房反向抵押的养老模式在理论上讲是一件好事,在美国早就成为五个养老支柱中的支柱之一,但在中国情况就不一样了,它遇到的是文化传统上的“水土不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