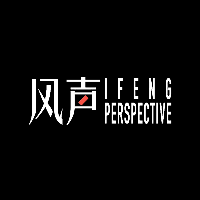风声|从鹿道森之死到宋清辉之子:什么造就了这一代人的“生无可恋”?


独家抢先看
12月1日上午10点,独立摄影师“鹿道森”的遗体在舟山朱家尖南沙情人岛海滩被发现。此时距离他11月28日晚23:28在网上发出最后的遗书,刚过去不到两天半时间。
事后推断,那封遗书是用手机设置定时发送的,他在当晚早些时候就已投海。
那天正是他25岁生日,妹妹和妈妈还在微信上祝他“生日快乐”,他拒收了妈妈的祝福红包,最后回了一句“谢妈妈”——这是他的分寸和礼貌,但恐怕他并不感谢妈妈把他带到了这个世界上来。
孩子自杀后的群体反应:
为什么有人认为“父母白养了鹿道森”?
在他那封五千字的遗书一开头,就说到自己的多重形象:“农村、留守儿童、山区孩子、校园霸凌经历者、摄影创作人、独居青年、追梦的人。”然而,在他25年的人生中,影响最深远的还是长长的童年阴影。父母对他寄予极高的期望,9岁才二年级时,因为无法跨级做出一道四年级的数学题,他被父亲狠狠踹了一脚,他说:“如果世界上只需要神童,那我这样智商的孩子,是否就应该被这样对待?”
遗书里写道,作为留守儿童,他每年只能在过年时和父母见一次面,而他们只关心他的成绩——在纸条上写给爸妈的思念,他们接过就扔掉了。在7月31日的一条微博上,他说:“要是所有人在成为父母之前必须通过入职考试就好了。”
在校园里,由于他长相清秀、性格文弱,又饱受欺凌。除了小时候的外婆,他感受不到其他人的温暖。这是一颗非常孤独、敏感的灵魂,“爱”是他留在人世的遗书中出现的最高频词:
我希望要成为父母的人明白,孩子应该在爱中出生和长大,而不是争吵。孩子也是独立的个体,而不是为了实现自己梦想的工具人,强势的控制着孩子的人生,逼他们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野蛮的灌输自己的想法,只会让他们痛苦到生不如死。不想做的事就可以不做,不想说的话就不说,不想见的人就可以不见,永远活在爱的环境里,这该多好啊。
当他还生死不明时,远在贵州老家的姑姑公开喊话,让他千万别寻短见,一切都好商量。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亲人理解他这封遗书中所传达的意思了,相反,他们在得知他最终的死讯后,普遍看法是:“他爹妈算是白养了。”
在公开的报道中看不到他父母的反应,仍是那位姑妈在解释:他爸爸只是嘴上不饶人,但“没有暴力倾向”,打工、贷款供儿子创业不容易;至于他说到的从小所受校园霸凌,家人完全不知道,也根本没给他什么压力,“爸爸妈妈都很爱他,是他自己心里想多了。”
当然,姑姑的这番话也有可能是在悲剧已经造成之后,避免再指责已经陷入悲痛的哥哥嫂嫂,但如果你以为这只是少部分人的看法,那就错了。
自媒体作者“家有小甜椒儿”和自己母亲感慨到此事,结果得到这样一番答复:“都大学毕业了,可以赚钱了,这是图什么呢?爸爸妈妈不是白养了一场吗?就不能理解自己的父母吗?都不容易。有什么不能解决的吗?小时候被霸凌过,都过去多少年了,总想着干什么……”
这是一种很典型的中国家长反应:父母也有自己的难处,把你拉扯大不容易,你应该(甚至必须)懂事,体谅这种难处,而不是闹自己的小情绪,为什么要想这么多?——在这里,一个字都没有提到“爱”,其实仍是单方面义务的“孝”。
2019年4月17日,一个17岁的男孩在和母亲发生争吵后,在卢浦大桥上打开车门,开车的母亲还没反应过来,他已头也不回地纵身一跃,坠桥而亡。在他死后,当时也有一种声音指责他太“自私”,根本没考虑这会让母亲多痛苦。
不管怎样,这种看法如此普遍,在不同事件发生出一再出现类似的群体反应,证明并非偶然,可能源于我们文化的深层。
父亲去世前对我说,他心里两件事放不下:一是不能看到孙儿长大,二是住了近三十年的老屋没来得及翻修一下。当时只觉难过,但现在想来,他这样的心理十分典型,这意味着一个深受传统影响的中国人,直至临终,遗憾的仍是未能完成自己社会角色所应尽的职责。
诸如“遗憾没能看到孩子长大/成婚”这样的愿望,乍看是个人的,其实这个“我”也是作为社会角色的自我。
那不是更个人化的遗憾,例如“遗憾我再也看不到东海的落日了”、“遗憾我还没完成自己的作品”。
@鹿道森遗书末尾的配图
中国的孩子们:
“他们承受了太多本不该承受的”
回头来说,那种指责自杀者“自私”的声音,其实也是从这一传统出发,责备他未能尽人子之责。此前有些孩子不堪霸凌自杀,遗书说对不起父母,只能来生报答,其愧疚感也源于此。
换言之,在中国传统中,“角色自我”比“真实自我”更重要,哪怕你已经苦不堪言,仍有绝对的义务尽责尽力,否则你死了,你的父母怎么办?在这一意义上,你这条命不是你自己能支配的,就算你想死,也得等自己人生职责全部完成之后。
然而,对自我意识更强的一代来说,人世值得留恋的不是人际取向了,而是自己感受到的人生乐趣。当后者压倒前者,那么对他们而言就已生无可恋。
实际上,我们整个社会都鼓励这种倾向。日前杭州疫情爆发,一对夫妻滞留浙大校园,他们16岁的女儿却婉拒社区送吃的,自己给弟弟做饭,受到当地媒体《钱江晚报》的赞扬。
这是中国社会常见的话语:不质疑权力本身,转而赞扬承受困境的弱者“明事理”。因此并不意外,这个孩子不像个孩子,而是成人期望她成为的那个样子。我们的社会文化经常赞扬这类“懂事的孩子”,但往往正是这类孩子,更容易出现心理问题——他们承受了太多本不该承受的东西。
生在这片土地上的孩子,似乎在挣扎着成为自己之前,都要先设法满足家长的期望,无法满足这一期待的,就得不到爱。
换句话说,家长眼里看到的,其实不是作为个体的孩子,而是那个“角色”——所谓“懂事”,在本质上就意味着那个孩子“扮演”好了自己的角色,尽到了为人子女的“本分”。在这种情况下,也难怪中国人对孩子最常说的赞扬是“听话”,也就是孩子依从成人的意志,履行了为他们设定的责任义务。那其实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用通俗的话说就是“做儿子就要像儿子的样子”。
可想而知,这样的视角会遮蔽鲜活的个体,上位者尤其容易看不见底下的那个“人”——因为如果你只在乎他能否扮演好那个“角色”,那么属于他个性的东西不仅是次要的,甚至是要主动压抑的。
多少父母都羡慕“别人家的孩子”,意味着他们眼里看到的是一个角色模范(role model),而不是一个独特的个体。
在这样一个“角色本位”的社会里,这是不得讨价还价的,是绝对义务,因而天经地义,别废话,照做就是。在这样的家庭氛围里,“爱”只能在夹缝里存在,仿佛是见不得人的“妇人之仁”,一如窦唯在《噢!乖!》里唱的那样:
没有一个能感到温暖的家
从来都是担心和从来都是害怕
还要我去顺从你们,还要乖乖听话
都说那是儿女对父母的报答
你们说不管出现什么情况
都要学会接受,不要说什么废话
站在一旁默默说爸爸不要吧
胆战心惊默默说妈妈不要吧
悲剧的根源:
无爱的父母与求爱的子女?
日前,曾建议“中国人假期应减少一半”的经济学家宋清辉12岁的儿子在深圳跳楼自杀,但此事引起外界关注的并非这一事件本身,而是这位刚经历丧子之痛的父亲的反应:他一再谈到自己儿子是因为不堪学业过重,认为这一悲剧对“双减”政策有参照意义。
有一位在校大学生感到很不可思议:“儿子都没了,老子还有心情一天发一条信息在网络上打卡,感觉这父亲有点消费儿子,太可怕了。”还有人质疑,孩子轻生,与家庭有着莫大的关系,但这位父亲却丝毫不曾反思自身的教育问题。
此事真正令人感到奇怪的地方,倒不是所谓他推卸责任、缺乏反思,而是儿子的死似乎没能让他动情——他仿佛是在谈别人家的一个悲剧。尽管作为外人不好揣测,他或许内心也压抑着深沉的悲痛,但至少他的公开表现给人的感觉,只能用“有脑无心”来概括:他可以从孩子自杀谈到学业重负和“双减”政策,但没表现出一点对孩子的爱。这种表现,可能本身就折射出悲剧的根源所在。
以往,对中国人来说,“活着”是不需要理由的,那是一种本能,无论如何都要活下去,但对现在自我意识苏醒的一代来说,如果连父母对自己都没有爱、家庭也不能成为自己的避风港,又没有什么美好的人或事物值得自己留恋,如此了无生趣,那么活在这世上的理由是什么?
在鹿道森去世后,网上有人认为,他的悲剧恰恰在于他对“爱”还抱有期望:“这样的家人只能放弃寻求‘爱’才能解脱,他们终其一生都不可能给到纯粹的爱,求爱只能让自己枯萎。放弃后找新的朋友,找新的联结,只能这样。”
这是一种社会性的不治之症:缺爱的孩子只有对“爱”不抱希望才能保护自己,但这并未治愈自己,只是让整个社会变得更冷漠。
多少年来,“爱”在流行文化中近乎泛滥,但中国家庭对“爱”的理解其实才刚刚开始。当很多人看到鹿道森的遗书中一再提及“爱”时,也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常见的字眼意味着什么,实际上,那其中包含着最沉痛的反思,发出了强有力的呐喊。他觉得自己的人生没有意义,但如果他的悲剧能推动更多为人父母者有所醒悟,那他的死就有意义。
维舟系专栏作家、书评人。本文原标题为“缺爱的孩子”。
编辑|萧轶
本文系凤凰网评论部风声特约原创稿件,仅代表本文作者立场。转载事宜或加入读者群、转载群请联系风声君微信:jfscs125。
“特别声明:以上作品内容(包括在内的视频、图片或音频)为凤凰网旗下自媒体平台“大风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videos, pictures and audi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the user of Dafeng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mere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pace serv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