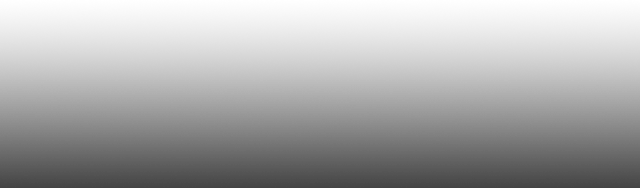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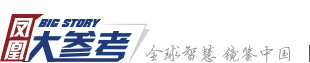 No.45
No.45
福山:
缺乏法制框架的民主是灾难
China Young Scholar Read Francis Fukuyama
作者:王鹏 2015年5月8日如今“历史终结论”已近而立,年逾花甲的福山再次来到中国,在清华大学发表题为《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的演讲。三十年世界风云变幻,民主思潮沧海桑田,福山何所思?历史何所忆?
的确,观福山近年来的思想演进,一种更为开放包容的理论关怀日益凸显,对他“民主原教旨主义者”的指责也渐渐淡去。但笔者以为,在更为根本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层面,福山仍有待祛魅——我们不得不继续追问:何谓制度之“本”?何为评价体制好坏的首要标准?人类社会真的有可能产生一种全真全善全能的“终极制度”吗?
品读福山:不变的民主信仰与常新的问题意识
2015年4月21日,在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十周年学术活动上,福山进行公开演讲,现场座无虚席。
当年的福山是作为美式民主最有力的背书者而登上世界讲坛的,而近年来面对世界各地民主化浪潮过后的挫败,尤其是民主灯塔——美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黯然失色,似乎又开始对其一贯推崇的民主理想有所反思。对此,不少论者惊呼“福山不再是福山了”;这当然是误读。细读福山近年来最重要的两部作品,2011年出版的《政治秩序的起源》和2014年的《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不难看出,他对作为纲“常”名教的民主本身的信仰从未动摇,“变”的只是对实现民主的手段及配套制度的认知。用刘瑜在《序》中的话说,这两本新书不仅不是要否定当年的“民主终结论”,而是要进一步将其完善。
福山对民主的坚定信仰从未动摇,但他的问题意识却是“常为新的”,其理论从宏观转入微观,视野的边疆也从最早的民主制度本身逐步拓展到民主与法制/法治以及问责的互动。在演讲中,他再次强调“国家能力——法治——民主”三位一体的社会秩序模型,指出只有三者间达成合适的相互制衡才能确保政治体系的良好运作,同时促进经济与社会的良性发展。
在问答环节,笔者特地请教了福山教授对民主与法治关系的看法。先生不吝教诲,援引欧洲的历史经验指出,历史上对绝对权力的制约首先并非来自民主,而是源于法律。譬如,是先有1215年英格兰国王约翰被迫签署自由大宪章,由此逐步确立“国王也在法律之下”的基本原则,而后英国才逐渐发展出有序的民主。作为对比,他特意提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认为缺乏法治框架的民主对国家和人民都只能是巨大的灾难。
祛魅福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终结者们”
三十年来,“历史/民主终结论”的话语体系建立了福山的全球声望。而当我们放宽历史与学科的视界就不难发现,福山也不是唯一的“终结者”。早在达尔文、斯宾塞的进化论风靡世界之前的数千年里,人类关于“生命终极目的”和“社会最终形态”的探索就早已展开。最早是祭司和僧侣为族人描绘各式各样的“最后之天堂”抑或“末日之地狱”。而自近代以降,或受理性主义、进步主义思潮之影响,或为人类在自然科学领域不断取得的胜利与发现所鼓舞,一种单线性进化模式(linear-progressive evolutionary model)逐渐成为东西方哲学社科领域的主要思维定势。
一百年前,康有为在糅合了公羊学三世说与近代西方进化论之后提出了“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演化路径;而在当下,与福山齐名的国际关系理论大师亚历山大·温特则认为人类世界已经从互为敌人的“霍布斯的世界”转化为互为对手的“洛克的世界”,并可能继续“进化”成互为朋友的“康德的世界”——最终一个世界政府(World Government)将不可避免地建成。遗憾的是,这种单线性进化论一方面对人类未来抱有一种近乎盲目的乐观态度,从而缺乏对可能弊病及内生缺陷的必要警惕,同时又由于过分的自信与自负而对其他诸多可能抱有偏见和敌视,从而在理论上遮蔽学者们的慧眼,并在实践上引发不可调和的对抗和无尽的人道主义灾难。

4月21日,在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十周年学术活动上,福山与中国学者交流。
米尔斯海默等学者对福山的一个主要批判就是,他所主张的自由民主(和平论)不仅未能促进世界和平,反而成为民主原教旨主义者对外发动战争的动因和借口——新保守主义的美国就是这样成为冷战后国际战争最大策源地的。
跨学科的类比总是发人深省。演化生物学中的一个经典案例提醒着人们,“进步”的具体标准往往是随时空变化而游移的,这意味着当我们评价一种“变化”究竟是“进化”还是“退化”时,不仅要在当时当地的语境下做出判断,还必须为其转型预留足够空间。科学家曾注意到,在一个海岛上栖息着的一种昆虫,并依据翅膀的长短将其划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分支。按照生物学一般常识,人们似乎有理由推断,长翅虫由于在飞行上的优势必将在捕食、求偶等活动中占据优势,而短翅虫则将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种内斗争中失利并走向绝迹,最终长翅亚种群将胜出并一统种群。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短翅虫成为最后的幸存者。对此,一种合理解释是,长翅虫恰恰因为飞得太高且翅膀受风面大而被席卷而来的海风刮进海里,短翅虫则因为飞得低而得到树丛的保护遂幸免于难。科学家们对此仍不满足,他们又将一定数量的长、短翅虫做好标记,带出海岛,然后观察其在没有海风干扰的陆地上的生存表现,结果是长翅虫反败为胜。
无论承认与否,大自然往往就是这样的“辩证”。人类社会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当地理环境、技术条件等因素发生系统性变迁后,原先的优势可能化为劣势,原本适用的制度也可能成为桎梏。譬如福山本人在书中也曾赞叹“伟大的汉朝制度”,认为古代中国的官僚/科举制较其西方模仿者先进了一千多年。在中华帝国漫长的黄金时代中,络绎不绝的外国朝拜者、倾慕者,从马可波罗到门多萨,从瓦尔特·拉雷到伏尔泰,又何尝不认为天朝体制便是最好的制度并希冀以此为模本“终结”泰西无尽的辩论与斗争呢?可在近代技术与文明的冲刷下,天朝崩溃了;在此后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一部分失去自信力的中国人又是何等自觉地匍匐在西方话语霸权的脚下?他们刻骨地反思黄土与河殇,真诚地指望通过全盘西化为蓝海文明而实现本族的涅槃重生。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怎不让人唏嘘蹉跎。但必须说明的是,对于愈加自信、奋发有为的中国人而言,此刻欢庆“中国纪元”的到来,抑或宣告“中国模式”对西方的完全胜利,也可能会犯下和福山一样的错误。
让我们回归文本,按照福山的业师亨廷顿的定义,所谓“政治制度”就是人类社会稳定的、受尊重的、反复出现的行为模式,其功能在于便利人们的集体行为。亨氏特别强调,二战后一批新独立的民族国家政局不稳并呈现“政治衰败”的迹象,根源就在于其制度不能适应环境的变化,不能适应新的社会群体的兴起及其政治诉求。由此可见,制度只是一种工具而非目的本身;作为制度的一种,民主亦只是一种工具,而不应被圣化为某种现时代的一神教(modernized monotheism),否则过度稳定的政治制度本身也会成为其自我衰败的根源。
本质上,真正决定一套制度/体制价值的普适标准,并不是看它能否具体促成某种特定人类行为或社会功能的实现(如普及投票权或提高社会治安度等),而是取决于它对新环境、新形势、新挑战的适应与应对能力,即制度弹性。任何舍“本”逐“末”的追捧或模仿,注定会为本国带来无尽的遗憾。因此,我们在判断一个体制的好坏时,不仅要客观评估它当下的表现,更应看重其自我更新与调适的能力:如果有一种制度,即便的确如其所声称的那样能够保障一定程度的公民参与,也能够为政府提供自下而上的合法性依据与问责等等,但是用动态、发展的眼光看,它正走向一种自我裹挟且难以逆转的衰朽,甚至整个社会的衰败都与之相随,那么人们就必须对其保持警惕并有所反思。
反思福山:“政治衰败”还是“社会衰败”?
数年前,清华孙立平教授曾指出,对中国社会最大的威胁可能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前者是“外伤”,指严重的社会冲突会威胁政权和制度的基本框架;而后者则是“内伤”,是社会肌体的细胞坏死,机能失效。社会溃败的核心病灶在于权力从内部失控,其表现是腐败处于失控和“不可治理状态”。

美式民主的鼎盛时期,也是美国最具领导力的时期。然而近年来,外界舆论却往往认为美式民主的灯塔日渐暗淡。
理论上看,孙教授的分析是鞭辟入里的,他的担忧也绝非杞人忧天。但对人民而言,更为幸运的是,两年来习主席和党中央的反腐利剑披荆斩棘,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社会公平公正的实现与人民对党信任信心的重建开出一条明路。想当年,“苍蝇老虎一起打”的宣言也曾被个别媒体和贪官嗤之以鼻,以为不过又是一轮政治运动,风雨过后彩虹依旧;然而事实胜于雄辩,中央高压反腐的新常态不仅赢得了全国人民的交口称赞,也在全世界树立了威信和榜样。追问:为什么原本“不可治理”的腐败终究被“治理”了?为什么这种难度极大、风险极高的改革偏偏在中国能够成功?用清华阎学通教授的话说,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的Leadership(领导力)与众不同。结合薛澜、胡鞍钢、王绍光、潘维等学者的科研成果,就是中国特定的政治体制和政治传统,能够将最有魄力、执行力、战略眼光以及自我牺牲精神的领导人从基层层层拔擢,然后以经年培养加以陶铸,最后赋予其必要的自主权,让他们能够在宪法的框架内大刀阔斧地力除积弊、锐意革新。
这种制度优势是美国所不具备的,原因就在于美式民主太完备、太稳定了,其“超稳定结构”既阻止了战争狂人或独裁者觊觎权力,同时也使整个政治体系在面对致命挑战和重大转型时自缚手脚,改革无力。
秦晖教授在观察西方国家内部党争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在那样一个竞争性选举体制下,为了赢得选票,左派永远是理直气壮地主张“高福利”,但对于这背后的代价——高税收却避而不谈;同理,右派在高悬“减税收”的胡萝卜时说得天花乱坠,但绝不会告诉你他们要大幅裁减国民福利。于是,左右两派轮番上台执政造成极其恶劣的非预期后果:为讨好选民,“低税收+高福利”的恶性螺旋造成财政的枯竭和国家能力无可逆转的损毁。对此,有人会问,为什么这类国家有的早已破产,而有的却能依旧强大?
对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跳出国内政治的藩篱,用国际视野加以比较。一句话,弱国在国际体系结构中的位置决定其只能以恳求援助(或威胁不给援助就滥发签证)的方式转嫁国内危机;而强国,尤其是同时掌握世界货币金融体系和顶尖军事力量的超级“金铁大国”则通过剥削边缘国家(哪怕如中国这样富有、强大却仍未主导国际政治与金融体系的大国)来实现以邻为壑式的自我救赎。依附论、世界体系论对此已有系统阐述,笔者兹无赘言。
再追问:像这样的一个国家,它在国内又是怎样的一种“社会”?答曰:衰败的社会。受福山和孙立平教授的启发,笔者将“社会衰败”界定为,在一个以“乡愿”粘合的共同体中,国内不同党派、利益集团不仅以福山所观察到的“否决制”为工具争权夺利,为了短期的选票收益而无视长远的国计民生;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过度民主”(福山本人语)的政治生态背景下,其统治精英与国内民众借助选举系统在事实上达成某种默契与合谋——统治者借助该国的全球霸权向全世界人民征收“铸币税”并转嫁危机;通过“剪刀差”等贸易手段合法地对世界各国进行剥削并获得超额利润;当其国内生产“空心化”所导致的实力衰退已无力支持它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继续护持霸权时,通过推出区域性自贸协定排斥他国,从而巩固并延续区域性经济霸权;同时还以精明的移民政策“收割”全球政商学精英为其效力;最后,在满足自身需求的同时拿出一点残羹冷炙以社会福利的方式安抚草根,从而在形式上貌似无比公正合理的“问责”中名正言顺地获得统治合法性。在这个社会中,一部分民众或知情或不知情地也都在相当程度上成为统治者的某种“同谋”——他们似乎已无其先辈那开拓进取、产业革新的锐气,不过如尼尔·波兹曼所嘲弄的那样,在沙发薯片肥皂剧的浓汤里“娱乐至死”。
诚如孔子所言“乡愿,德之贼也”,这种体系在道义上是站不住脚的。谭复生倘若复生,亦必斥之曰“唯大盗利用乡愿,唯乡愿工媚于大盗,二者交相资,而罔不托之于民主”。而从工具理性角度看,它貌似严丝合缝、稳定持久的表象也遮盖不住由其内在制度革新动力之匮乏所决定的脆弱。于是,当外部出现一个可能的替代品、一个全能型竞争者时(而非如冷战时期日本徒有经济优势、苏俄全赖军事实力),其反应之大、芥蒂之深也就不难理解了。而鉴于其成熟度之高、稳定性之强,似乎看不到有什么内部力量能够冲破一切阻拦,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既不道德又不可持续的治理模式。是故,有英吉利布公问:民主其殁乎哉?对曰:尚在;然疾在骨髓,司命之所属,无奈何也。
超越福山:中国崛起的全球性制度贡献

崛起的中国正在世界新体系的形成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一带一路的构想和建设全球瞩目。图为维基百科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示意图。
有关“中国崛起”的话题已热议多年。但论者似乎始终更多地关切中国的经济与军事硬实力对世界的冲击,却不问“中国崛起是否可能对全球的制度变革贡献智力”。这或许也是一种西方中心论-民主终结论的现实反映罢——作为异质性“他者”的中国力量,终究要被融入美式民主的大熔炉,经过锻造而后成为历史终结的另一件标本。但必须申明的是,笔者对所谓“中国模式”、“中国纪元”也始终有所保留。浩瀚的太平洋足够大,能容“中国式协商民主”与“美国式自由民主”平等对话。纵观人类文明的千年演进,都是在不同文明文化、不同制度理念间通过对话、试错、竞争、合作、相互借鉴、取长补短而踽踽前行。崛起中的中国应该有足够的自信力将自己在制度实践中所总结的经验与教训贡献给这个瞩目中国的世界;同时也应继续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毫不犹豫地学习人类一切先进文明成果。陈乐民先生生前就曾说道“不读中国史,不知道中国何以伟大;不读世界史,不知道中国何以落后”,这样的审慎与胸怀的确值得我辈学习。
大师终归是大师。同样二十年多前,亨廷顿发表了反驳其弟子福山“历史终结论”的论述《文明的冲突》——历史并未终结,只是斗争焦点从“意识形态”转为“文明之争”。数十年来,无数年轻的学者因批判亨氏“文明冲突论”而成家成名,但学术的万神殿里至今仍只供奉着亨氏的神龛。同理,笔者也不敢奢望一篇小小的评论就能冲击福山先生三十年来的全球盛名,但为一习作,直抒胸臆,求教方家,庶几无愧于学、无愧于心、无愧于时代已矣。
凤凰大参考专题文章为本栏目特约,转载请务必注明来源及作者姓名,违者必究。
王鹏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后研究员。

凤凰资讯微信
扫描微信
关注凤凰资讯
凤凰评论出品
策划:易心
栏目合作:zhaoqm@ifeng.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