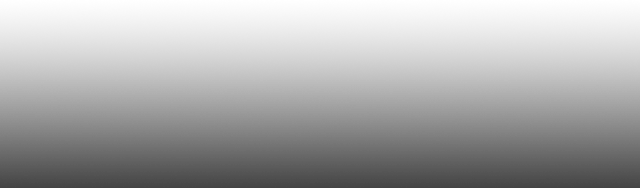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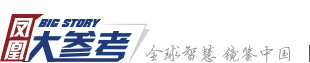 No.23
No.23
林达:我是查理
我也是我自己(三)
作者:林达 2015年1月22日
编者按:关于《查理周刊》恐怖袭击引发的争议仍然在发酵,凤凰大参考特邀著名旅美作家林达撰写查理事件反思录,深度分析由查理事件引发的言论自由尺度的争论,共分为三期专题发布,本期为第三部分,以下为正文:
有十一个欧洲国家,对“否认大屠杀言论”,即对“声称在纳粹时期德国没有发生过犹太人大屠杀”的人,视为有严重罪行,可以法律惩罚。这当然和二战中欧洲的历史伤痛过于惨烈有关:在历史上,德国纳粹思想言论的宣传鼓动,曾经导致战争和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德国法律更规定不得展示纳粹党徽和其他标志,违者被视为有严重罪行。这是最近法国等欧洲国家受到“言论自由偏向”批评的来由。
虽然这样的法律有顾忌这些言论表达刺激伤害犹太人感受的一面,但是,这类立法主要是在国家层面,对于纳粹在历史上曾威胁欧洲安全、引发国家灾难的具有强大宣传效果的言论依然心有余悸,对“开放纳粹言论”是否会带来危险后果缺乏信心。
在美国最高法院支持的弗吉尼亚州 “禁止为恐吓某个人或者某群体而焚烧十字架”的立法,有“恐吓某个人或者某群体”的前提。例如,不可以在某个黑人家门口或者黑人教堂面前,做有针对性威胁性的焚烧、形成“针对具体人的恐吓”。“无针对性地焚烧十字架”并不在禁止之列。
而德国法律“不得展示纳粹党徽和其他标志”等相关规定,不是限于针对特定个人或一些人的威胁,而是无特定目标的展示也不可以,因为它事涉对国家、欧洲安全威胁的判断。
美国的宪法第一修正案也同样保护纳粹言论和“否认大屠杀”言论。这并非完全来自它的历史伤痛经历和欧洲国家有差别,因为就连美国的邻居加拿大,也对“否认大屠杀言论”视为严重罪行。保护一切言论是美国人对宪法第一修正案两百多年反复思考和实践的结果。美国人总是引用霍姆斯大法官那句名言:“我们所痛恨的言论,也有自由。” 虽然它也并不是绝对的。
美国宪法只衡量言论后果不考虑内容对错
讨论《查理周刊》漫画时,不断有人提出冒犯宗教的漫画涉及“言论边界”,提出这样的“冒犯”是可以还是不可以。一个成熟的法治社会遇到这样问题,会先划清两个概念:“不可以”是法律的,还是道德的?而没有这种公民训练的社会,经常混为一谈,概念不清。
再提一下教皇举过的例子,“假如一位好朋友对我母亲出言不逊,我会举拳打他,这很正常。”这个“不可以”,就是道德上的“不可以”,因为法律不会因为一个人对朋友的母亲出言不逊就判定他必须坐牢。教皇还说:“有那么多的人说其它宗教的坏话、嘲笑,把人家的宗教信仰当玩物:这种人就是挑衅。”他强调,宗教自由和言论自由“皆为人的基本权利”。显然,一个宗教“被他人嘲笑、说了坏话”,并不等同于“失去宗教自由”。
那么,在法律意义上的“言论自由的边界”在哪里?美国人都熟悉霍姆斯大法官在“申克诉合众国案”中的一段话:“对言论最严格的保护措施也不会保护有个在剧院故意大呼失火而引起混乱的人”。这句话在《查理周刊》事件之后被人们反复提到,以质疑《查理周刊》漫画的“言论自由的界限”。
一个重要的界限,就在霍姆斯大法官在同一段判词里提到的判断标准:“在每个案件中,需要考虑的问题是,是否所用的词语具有这样一种性质,即有引发实质的、邪恶的、清楚的、迫在眉睫的危险,从而使国会有权加以阻止。”这就是现在主导美国最高法院的言论边界原则:会引发“迫在眉睫的、清楚的即刻危险”后果的言论,不受保护。

一位手持标有“我是查理”巨型铅笔的女士参加巴黎反恐大游行。
所以,“边界”的划定,不仅在言论本身,也在于它所发生的具体背景。同样一句“起火了”,在坐着稀稀拉拉几个观众的剧场里呼叫,当然就是可以的。今天你没有任何行动计划,只是站在白宫前对路人号召:“我们把白宫给炸了!”哪怕在最紧张的反恐时刻,你也许会被逮捕,只要查下来没有任何具体行动计划,你只是“泛泛而号召”,就不会因为这个“言论”被定罪。
如果你是对恐怖分子极具影响的人物,对着蠢蠢欲动寻求袭击目标的恐怖分子说:“我们把白宫给炸了!”他们也确实会准备这样做。那么你会受到起诉,再由法庭根据具体证据推敲衡量,你是否越过了法律意义上的“言论自由的边界”、是否可以定罪。
在1969年有个“布兰登伯格对俄亥俄案”,三K党一个头目说:“我相信黑鬼最好被送回非洲去,犹太人该滚回以色列”,联邦最高法院判定他的言论无罪。因为,并没有证据说明,这言论后面有当下和未来可能发生的行动。
1977年,美国的纳粹组织宣称,他们要佩戴希特勒的纳粹标志在一个名叫“斯科基”的小镇举行游行,小镇当局作为应对,宣布禁止传播包括服装、标志在内的任何“因种族、国籍和宗教差异而激起仇恨的东西”,并且向所在州法院申请了同样禁令。在打官司的时候,著名的“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支持了纳粹组织,导致许多成员退出。在上诉到联邦第七巡回法院的时候,禁令被判违宪。该纳粹组织后来也自己取消了游行。
时过境迁,“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因而更壮大了,因为更多人理解了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法理意义。在第二部分文章提到的《好色客》一案中,也同样强调了“言论自由的中性原则”,就是法律只衡量某言论是否会引发“迫在眉睫的、清楚的即刻危险”后果,并不考虑它的内容的对错、持什么样的观点、是否“政治正确”。
美国认为民众在认识纳粹问题上心智成熟
“斯科基”小镇一案涉及今天如何处理纳粹宣传,所以在国际上很有名。其实在欧洲,对某些国家禁止“否认大屠杀”言论,也存在法理上的争论。他们在讨论中也引用“某言论是否会引发危险后果”这样的判断标准,思路有相似之处,但是,也有不同。
例如法国的法学家兼法官罗杰•埃雷拉认为,欧洲人绝不会接受美国在“斯科基”小镇一案上,对待类似仇恨言论的观点。他认为美国人的观点建立在“不可救药的社会、历史乐观主义之上”他认为,经历大屠杀的欧洲绝不可能接受这种观点,希特勒写的《我的奋斗》宣扬了种族仇恨,当年要是一出来就给禁了,防患于未然岂不更好。
写到这里,正好看到新闻,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一书,已经过了它的七十年版权期。原来,这本书的版权一直在德国的巴伐利亚州政府手里。德国政府并没有法律规定禁止再版,但是版权拥有者却一再阻挡该书再版,其理由和罗杰•埃雷拉相同。现在,可以肯定,既然版权过期,又有时网路时代,阻挡本身一定失效了。
有欧洲媒体人对此忧心仲仲,但是再看美国媒体的反应,一如罗杰•埃雷拉所描绘的,看上去似乎仍然普遍抱着“不可救药的社会、历史乐观主义”态度,美国人对《我的奋斗》的版权变化所带来的出版扩大、可能在德国再版,似乎感到“没什么大不了”。他们相信本国和欧洲民众对认识纳粹问题上的心智成熟,相信这种成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所生活的言论自由的现代社会环境下,对纳粹时期多年的反省教育,相信纳粹宣传已经不会对世界带来真实的灾难。这种乐观是否过于天真,会通过实践检验,反正可以看得到。
欧洲国家立法禁止了“否定大屠杀言论”,却没有禁止《查理周刊》的漫画,是这次招致“双重标准”批评的重要原因。其实,在这个文化中,是撇开内容,即“内容中性”地一直在认真探讨。
例如英国的《经济学人》就在2006年撰文谴责这样的立法,包括反对将种族歧视言论列为罪行。文章写到:“巨大的危险在于打着阻止顽固分子的旗帜限制言论,最后结果往往只是扼杀所有批评。”那一年,著名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去世,在她临终前,还在等待意大利法庭对她言论是否有罪的裁决,原因是她在九•一一以后的那篇文章中,批评了伊斯兰文化。

图为被誉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女记者”的意大利记者奥莉娅娜·法拉奇。她于1980年8月采访邓小平。她于1967年开始任《欧洲人》周刊战地记者,采访过越南战争、印度和巴基斯坦战争、中东战争和南非动乱。
如果了解美国工业革命初期的历史,就知道美国人并非天生乐观,而是他们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社会动荡的大风大浪,红色革命思潮、与黑色无政府主义结合的工人运动、百年前的恐怖主义和暴力袭击,他们经历了社会在危机应对中,面对了激烈社会动荡、如何处理暴力言论、暴力革命宣传和言论自由关系的曲曲折折的路径。
他们一次次地区别,什么是法律必须制裁的“迫在眉睫的、清楚的即刻危险”;什么是必须容忍的个人表达、社会表达、对社会现状不满的言语宣泄和批评批判;这些语言是将导致暴力摧毁,还是促进进步的社会变革?并且一次次去判断,那些曾经“危险的言论”,由于时过境迁和社会危机缓解,在什么时候,已经可以重新“解禁”、言而无罪。可以看到,这种制度是深具挑战的,因为压制言论最可能的受益者就是政府及其官员。
对于言论的规范不是简单的、绝对的。完全相同的一句话,可能在甲地波澜不惊,在却乙地掀起轩然大波、暴力冲突。那个为布鲁克林博物馆的展览辩护、并且战胜了纽约市政府的著名律师Floyd Abrams,就曾经思考过这个问题。
他问到:“持续地保护言论自由到如此程度,我们这样做对吗?就我们特定的文化而言,我想我们是对的。容许信奉一种宗教的人诋毁另一种宗教会不会无可避免地导致社会冲突?在印度就可能如此。”在印巴分治期间,印度教和穆斯林的冲突曾经导致数百万人丧生。
“容许否认大屠杀的事实,在战后的德国可能就是无法被接受的。两个国家因此都制定了符合他们需要的法律,将这样的言论定为是犯罪。在其他国家,另外的情况可能会证明,相比我们依据宪法第一修正案得到的表达自由,他们只能得到更少的自由是正当的。”
心智不成熟的社会容易爆发冲突
那么,这种地区国家差异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这还是文明发展阶段的差别。纳粹宣传会带来威胁和危险,显然和民众的心智的成熟程度有关。听到别人诋毁自己的神就会引起大规模暴力冲突,也和信徒们的心智成熟程度有关。
天主教曾经更为敏感:只要信徒对圣经的理解和正统解释不同,就视为非法,一步步发展到对宗教的讽刺嘲笑是非法,暗示、影射、腹诽是非法,最后是“可能的腹诽”都非法,在政教合一制度下,就可以逮捕关押酷刑处死,这种做法曾经得到大量心智不成熟的狂热教徒的拥戴。
今天,虽然欧美之间有一些具体分歧,但是确实,现代“西方文化”在对待言论出版自由的制度演进上有趋同性。原因只是他们先其他文化一步,理性地一次又一次反省、吸取了自己的历史教训,他们从中看到,假如没有新教徒对天主教的强烈抨击,就没有宗教改革的进步;假如不能表达对神的怀疑和不敬,就没有启蒙时代,假如绝对不能表达对宗教的彻底否定态度,进化论无神论作为一种思想,就完全没有生存的空间;假如对宗教不容许任何怀疑,科学技术的许多门类可能被扼杀。

2015年1月16日,伊斯兰大会党在位于巴基斯坦卡拉奇市的法国大使馆外抗议法国《查理周刊》对穆罕穆德的讽刺漫画。现场至少有三人受伤。
尼采的“上帝死了”是宗教冒犯;《国际歌》“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是宗教冒犯,从宗教法庭,到今天梵蒂冈拥有世界一流科学家聚集的教宗科学院、可以讨论一切科学议题,他们只是从自己的千年禁锢和野蛮中,先行一步地走向了保障思想自由,才在制度上尽最大可能地容许冒犯,包括容许他人冒犯自己和自己的信仰。
这是非常困难的话题。因为,正如Floyd Abrams所说,在一个心智不成熟的地区,容许触动危险话题,那么带来的结果就是社会冲突动荡的危险。所以,在一百多年前,美国曾经禁止某些无政府主义的反政府暴力宣传,因为它带来“迫在眉睫的、清楚的、即刻危险”的社会后果。但是,当民众心智成熟,不再受这些暴力鼓动的影响时,法治国家要有诚意和能力解禁那些曾经在危机时刻禁止的言论。
但是,由于政府有不乐见批评的天然属性,所以在很多国家,往往是相反情况:假借对国家危险和威胁,积极立法扼杀言论。如联邦最高法院的怀特大法官在“《迈阿密先驱报》对托尼罗案”中所说:“我们已经并将继续从其他国家的不幸经历中吸取教训”,不让“政府悄悄潜进我们的编辑室”、由“执政者来决定我们可以说什么和不可以说什么”。
在这个《查理周刊》事件有关“言论自由”的讨论中,其实分为三个不同层面的问题:《查理周刊》作为一个政治性讽刺漫画刊物,它涉及宗教的漫画是不是越过了法律层面的“言论自由”定义的界限,所以“不可以”;《查理周刊》曾经刊出羞辱冒犯不同宗教的漫画,是不是在道德层面越界,所以“不可以”做;恐怖分子在《查理周刊》的屠杀是不是代表了穆斯林对宗教冒犯的反弹。
前面我简单理了一下美国的政治讽刺漫画在言论自由框架内得到法律对宽泛保护的思路来源。法国的法理思路是一样的。因此很显然,《查理周刊》的漫画并没有在在法律上对“言论自由”的权利越界。人们会很困扰,已经到了引人开枪屠杀的地步,这样具有宗教冒犯的漫画,怎么还不是会引发“迫在眉睫的、清楚的即刻危险”后果、应该被禁止的言论。实际上,很简单,只是需要把恐怖主义袭击从漫画冒犯事件中区分出来。可是,大家会很困扰,怎么可能区分?
全球的伊斯兰极端恐怖组织,拥有同样的价值观、同样的奋斗目标和残忍手段,他们今天选择《查理周刊》作为攻击目标,和当年本拉登选择纽约世界贸易中心作为攻击目标,和阿富汗、巴基斯坦的塔利班把自己国家的女童学校当做必须炸毁的攻击目标、枪杀邻居上学的女孩,并没有什么差别。
确实,那些以为修正西方文化就有可能平息恐怖战争的人们,多少有点天真。因为这个世界不可能修正到大家变成塔利班治下的阿富汗。而只要不是那样,恐怖分子就不会善罢甘休。其证据,不仅是恐怖组织对西方平民的袭击,更是在塔利班和ISIS这样的极端恐怖组织的统治下,他们对异教徒、对同为穆斯林的异教派的大规模血腥杀戮、以及他们对所谓“违反教规”的同教派穆斯林的任意残杀。
法国恐袭不是宗教被冒犯导致的过激反弹
在前面提到的“《好色客》对Falwell案”中的主角Larry Flynt,他远不是一个受到主流社会欢迎的人,他看不上眼的政治家、宗教人物或者公众人物,就可能被他放入《好色客》的“混蛋榜”栏目,不知羞辱和得罪了多多少少人。而且,美国主流社会的很多人厌恶他的作派,感觉被他严重冒犯。所以他在自传中把自己称为社会弃儿(outcast),一直都官司缠身。
1978年,他因为一场官司来到佐治亚州,那还是在那场“《好色客》对Falwell案”在联邦最高法院裁决的十年之前,就在离我家不到一个小时的一个县法院门口,一名暗藏在附近的狙击手,几枪把他给打残了,还打伤了他的律师。Larry Flynt此后一直困在轮椅上。
枪手叫Joseph Paul Franklin,是一个“孤狼型”的恐怖分子。他先对基督教福音派感兴趣,之后崇尚希特勒,同时是白人国社党和KKK的成员,但是他并没有受任何组织的唆使,只是自己决定发动他一个人的恐怖袭击。他后来自豪地承认自己杀了一系列的人,最后被法庭确认、定罪了六项谋杀案,他在2013年11月20日被执行死刑。
在美国不认同Larry Flynt价值观、被《好色客》冒犯的人,都能够把枪击事件和《好色客》言论的法律界定截然分开。他们不会认为,那个不认同Larry Flynt价值观的恐怖分子的袭击,就是判断《好色客》言论引发社会危险度的一个标准,或者说参考值。

2015年1月11日,法国总统奥朗德在反恐大游行时安慰幸免于难的《查理周刊》专栏作家Patrick Pelloux。
虽然《查理周刊》有漫画同时冒犯了普通穆斯林、也冒犯了恐怖分子,但是,事情的性质并不是宗教被冒犯而过激反弹的事件。恐怖分子就是恐怖分子。这也是欧洲和巴黎的穆斯林领袖会站出来哀悼《查理周刊》死者、坚决谴责恐怖袭击的原因。这也是那一天巴黎成为世界首都、大家一起站出来说“我是查理”的原因。
法律的界限非常清楚,道理也很简单。并不是说,合法的事情就一定是道德的、应该做的、是合情合理的、是适当适度的、是负责任的。在成熟的文明社会,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行为准则;对他人言论可以认同和不认同,对艺术表达可以喜欢和不喜欢。
每个人站出来,做了反对恐怖主义的表态之后,他当然是他自己,他如果有不同意见,他可以一如既往地、具体地说,我不赞同《查理周刊》、我不赞同冒犯他人的宗教,我不喜欢这些漫画,这和“我是查理”的反恐态度,完全可以同时共存。
《查理周刊》是个销量极小的刊物,甚至濒临破产,它平日的销售量说明,成熟的法国社会自有它自己的判断标准。一份杂志做得好不好,它的政治讽刺漫画的思想、道德、艺术水平如何,这本是正常社会的正常话题。它原本就生存在同样的、容许尖锐批评的社会环境之中。
一个再成熟的社会,也无法避免激进的思维和行为,成熟的社会就是最大限度开放批评,包括对各方的激进思想和行为的批评。那些共存的不同思想的表达,在交流批评碰撞中相互教育,也接受民众的筛选。同样,回到常态,他们也要面对自己社会的各种新旧问题:经济问题,移民容纳量问题、不同族裔和宗教相处的问题,雇佣相关法律和失业率的关系,反恐问题。
在由《查理周刊》引出的关于言论自由的讨论中,能感受到文化隔阂。那就是讨论不是在同一个逻辑内进行、难以进入它的文化逻辑。我每次细读七七八八的案例分析,总有很享受很感叹,享受和感叹它的内在逻辑,抽丝剥茧层层深入,把人和社会可能遇到的悖论和困境,都一点点解开。那是不是一个单向进程,那是一个多维空间,同样的大原则,在遭遇不同的时间和时代,在遇到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个体。
美国是个万花筒,给法律尽可能提供了最丰富困难的题材和最有意思的挑战,当我在美国南方啃着墨西哥人做的好吃极了的欧式点心,当我去纽约坐在一车讲着五花八门语言五颜六色的人中间,在哐当哐当的摇摆中,知道各个文化永远是不同的文化,知道各个宗教永远有他们自己的神,可是也知道各个文明可以进入同一个逻辑,理解有关自由权利的复杂的司法推论。
就像Floyd Abrams律师在海牙的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为一个与新闻自由的案子为华盛顿邮报的一名记者辩护,他代理了世界各国支持这名记者的组织,“在来自法国、圭亚那、斯里兰卡、土耳其和美国的法官面前进行辩论”获得胜诉。
直到二十世纪上半叶,美国法院的“司法审查权”还是它的宪政体制的“一个独特风格”,但是它在实践中表达的法理逻辑并不是只对一个国家适用,到二十世纪末,几乎所有宪政民主国家都采用了“司法审查制度”,尽管形式可能不同,有的也不尽完善,例如,德国、意大利、匈牙利、南非等,都有宪法法院,加拿大、印度、澳大利亚和日本等,都有最高上诉法院。完善这个制度的法理逻辑成为这些国家的共同目标。
由于沙利文案涉及言论自由领域的判决,几乎引起了绝大多数国家法院的关注。对言论自由的思考起于西方文化,但是它绝非止于西方文化,因为社会都是人组成的,人有共性的一面,不同社会也有它共性的一面,需要应对共同的难题。
各种文明是不同的,但文明是有发展阶段的,文明的进步和落后是有清晰的标准的:一定是越来越多的女孩向去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马拉拉一样,追求读书的权利;一定是有一天,不再有孩子被教唆去对一个跪在地上的人质行刑;一些文明进入现代思维逻辑的进展缓慢,其实是讨论的大前提卡在一个前置的瓶颈里,就像美国人必须先确立宪法第一修正案才可能进行下面一系列案例的推理解析,当它卡在一个大前提的确认上,那么,后面那一切充满智慧的智力游戏都无法进入,那些波澜壮阔,都无法展开。
凤凰大参考专题文章为本栏目特约,转载请注明来源及作者姓名,并发邮件至all_opinion@ifeng.com告知。违者必究。

林达
著名旅美作家,已出版“近距离看美国”系列《历史深处的忧虑》、《总统是靠不住的》、《我也有一个梦想》以及《历史在你我身边》等书。

凤凰网评论微信
扫描微信
凤凰大参考尽在掌握
凤凰评论出品
策划:赵雅楠
栏目合作:zhaoyanan@ifeng.co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