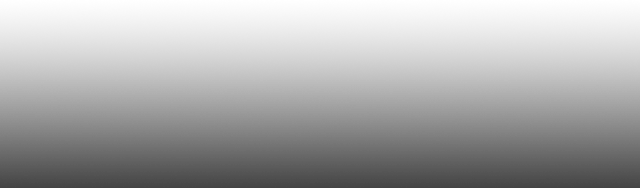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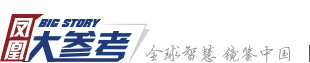 No.22
No.22
林达看查理:
“象粪圣母”为何能在美国展出?
作者:林达 2015年1月21日 文章原标题:我是查理 我也是我自己(二)
编者按:关于《查理周刊》恐怖袭击引发的争议仍然在发酵,凤凰大参考特邀著名旅美作家林达撰写查理事件反思录,深度分析由查理事件引发的言论自由尺度的争论,共分为三期专题发布,本期为第二部分,以下为正文:
那是一个来自英国的展览《感觉:萨奇收藏的英伦艺术家》,在纽约的布鲁克林博物馆展出,这是美国最大的几个博物馆之一。《感觉》展出的这些都是当代艺术,当代艺术常常是追求新颖,总要弄出点“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效果。虽然其中三名艺术家得过英国当代艺术最高的丢纳奖,但是它在伦敦展出时就引发很大争议,例如被切成一片片的母牛、吊在甲醛里的猪,等等。但是显然,每个国家的敏感点不同。
其中在英国毫不起眼被批评家忽略的一幅作品,却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这幅画叫《圣母玛利亚》,是个黑人妇女的形象,主要的绘画材料是涂抹上去的大象粪便,细细去看,有许多地方由女人私处的小照片拼贴而成。这一次,又是广告公司惹的祸,为展览设计的广告词被他们耸人听闻地撰写成了“健康警告”:“本展览会引起休克、呕吐、迷惑、恐慌、亢奋和焦虑”;接着《纽约每日新闻》的长篇报道提到“泼了象粪的圣母玛利亚”,引起了市政府的强烈反应。
艺术即使“亵渎”宗教也受法律保护
本来市政府就是反感也只能是说说而已,可是,这个案例不同,第一,市政府每年给博物馆约七百万美元赞助,这一年还有两千七百万的投资基金和建筑翻修拨款;二是博物馆的“馆”是出租给他们的市府财产。
天主教徒的朱利安尼市长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展览让我很不愉快。以艺术的名义让一个城市资助,而这所谓艺术作品,在向一幅圣母玛利亚的画像扔象粪,这种做法令人恶心。”
“如果私人为它买单,这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但是让政府买单则无法容忍。你无权用政府的资助去亵渎他人的宗教。因此,在展览的主管醒悟前,我们将尽量撤回资助……是政府赞助,就不能亵渎这个社会最个人化最深坚持的观念。”
朱利安尼其实知道,市政府资助博物馆,并不意味可以干涉艺术展览内容,无权下令停展,他说:“他们有权用个人的钱做,即使我们在一旁说他们有病、令人厌恶,我们也要捍卫他们展出的权利。但是,政府不是非要把纳税人的钱放在这里,这不是纳税人必须承担的事情。如果这是对新教、犹太教、穆斯林宗教的亵渎,我也会是同样感受。”而后,副市长打电话通知博物馆,如果不撤掉这幅画,市政府将中止所有资金。
市长在另一个场合表示,这画是“对宗教邪恶的、恐怖的和有偏见的攻击。”期间,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馆长曾经发表文章,赞扬朱利安尼市长的艺术眼光,对该展览的质量有“敏锐的判断力”,但表示:自己将如伏尔泰所说,虽不喜欢这些展品,但是要“誓死捍卫”布鲁克林博物馆展出这些“糟糕艺术品”的权利。

图为1999年在布鲁克林博物馆展出的克里斯·奥菲利作品“象粪圣母像”,图中细节处为女性私处。作品展出时遭到强烈抵制,被观众泼了白漆,三百教徒馆外大唱圣歌。
看上去,既然是纽约政府出钱,似乎有权决定收回赞助。但是,就在一年前的1998年芬利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关注到国家艺术基金可能滥用权力,“根据主观标准给出资助,以惩罚不同观点”。最高法院在芬利案的判词中说:一开始“政府可能并不想‘压制危险观点’但如果一项资助被‘操纵’产生了‘强制效果’,(法律)救济就是适当的。”那么,纽约政府作为“房东”,是否理所当然有权收回房子不续租?
针对以这种方式对“艺术表达”的报复,之前在联邦法院也已经有过判例。那是1999年的“古巴艺术博物馆和文化公司诉迈阿密市”一案。迈阿密政府认为该博物馆是聚集支持卡斯特罗的左翼艺术家的组织,因而要收回出租给博物馆的房产。最后,当地的联邦法院裁定,即便博物馆的房子是可以任意中止租约的市政财产,“市政府以上诉原因中止博物馆的租约仍然是违宪的”。
在这样的判例下,纽约市政府聪明地绕开宪法第一修正案,绝口不提《圣母玛利亚》,而是提出了三个和这幅画毫无关系的理由,诉博物馆违背租约,把他们告上了纽约州法庭,并宣布要收回房产不再续租,要把布鲁克林博物馆撵出待了一百零六年的家。同时,博物馆也以“侵犯博物馆的宪法第一修正案权利”为理由,把市政府和市长告上联邦纽约东区法庭,要求赔偿。
法庭辩论期间,涉及一些相关问题。例如,假如谈冒犯,佛罗伦萨的大卫雕像这样细雕了人体私处的古希腊古罗马大型裸体雕像,是不是可以展出?又如格森法官提出:“图书馆满载着因政治、社会、宗教等原因而可能得罪这个群体那个群体的书”,是否就要关掉;“市政府是否就有权决定,凡渎神的书就必须从公立图书馆清除出去”?
1999年11月1日,联邦纽约东区法庭裁定市政府只是寻找借口,实质上是“试图审查艺术表达的作品”,“由于一个重要的文化机构未能遵循政府要求的正统观念,因而以威胁其生存作为惩罚。”格森法官的判决认为,政府的行为是在“威胁政府在宗教领域的中立。”
纽约市政府向上诉法院提起上诉,辩护律师提出各种实例,表明在人类艺术史上, 许多在当时被大众、被教皇、被名人、被如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这样的政治人物认为是“粗俗下流的东西”,今天看来是公认的名作。
“新艺术被称为是‘恶心的’艺术不被接受,这是常态而非例外。”最后,上诉法庭支持了初审法庭的裁决,下令纽约市政府不得以任何形式报复博物馆,博物馆也随之撤销了要求的经济赔偿。
比亵渎宗教更危险的是把宗教当政治工具
我简要介绍几个案例,只是想在讨论涉及《查理周刊》事件的言论自由问题之前,先理顺所谓西方文化在率先进入的、对于言论出版表达自由讨论的一些基本逻辑。它确认言论出版自由是人最基本的权利,因为“思想是人最基本的权利”。
比如,联邦最高法院的安东尼•肯尼迪在2002年一个案子的判词中说:“思想的权利是自由的开端,言论必须受保护以免受政府的侵犯,因为言论是思想的开端。”而它实践的前提就是政教分离,因为宗教信仰是非理性非逻辑的,“信”即可,为什么信不需要推理也没有道理可讲。而假如要借重法理对人的基本权利进行思辨、以法律作为工具保护人的基本权利,“理性、逻辑”是一个最基本条件。
当一个文化还无法区分政治权利和宗教感情,当一个文化把政治宗教化、把政治人物宗教崇拜化,那么它在基本点上和先进文明的差别,不是文明内容不同,而是文明进化阶段不同。
美国立宪确立宪法第一修正案,最初是由一些极看重个人名誉的上层古典政治精英们,通过思考确立的,在那个为了个人名誉还要拔枪决斗的年代,他们主动放弃了自己手中现成的镇压之权,去维护民众以最自由的方式批评和攻击自己的权利。
经过两百多年来的不断完善,政府立法者和执法者构建了一个对自己极为不利的法治环境,以换取社会和政治的透明度,换取民众无穷无尽的创造力。而政教合一的社会,通常以最大可能利用民众的宗教热情,来保护自己的政治利益。它们可以借助民众的宗教感情宗教热情来维持这个制度,但是,一个国家走向政教分离的历史趋势还是很清楚,那是一个历史遗留的制度、不是一个可以在现代社会一直维持下去的制度。
在《查理周刊》事件之后,大家可以看到非常多的表态和评论,1月15日,教皇方济各接受记者采访就是一个典型。他表示言论自由是一项“基本权利”,但并不等于因此就可以“侮辱他人的宗教信仰”。他还谴责说,“以真主的名义杀人”是“荒唐的”。
因为“假如一位好朋友对我母亲出言不逊,我会举拳打他,这很正常。人不能挑衅,不能侮辱人家的宗教信仰,嘲笑人家的信仰。”教皇还说:“有那么多的人说其它宗教的坏话、嘲笑,把人家的宗教信仰当玩物:这种人就是挑衅。”他强调,宗教自由和言论自由“皆为人的基本权利”。

2015年1月7日,教皇方济各与巴黎大清真寺教长塞迪齐、法国穆斯林信仰委员会主席穆罕默德·穆萨维等人见面并交谈。
这些话似乎怎么看都是对的,好像一点问题都没有。大家把这样的说法都归于“哪里是言论自由边界”的讨论。但是实际上,这是跨越两个性质不同概念的讨论,那就是:什么是由“法律判断”可以惩罚的言论;什么是由“道德判断”是不应该发表的言论。
也就是说,“侮辱、冒犯他人的宗教”的“不可以”,是划在“言论自由法律界限”的“基本权利”之外?还是言论者“道德上有瑕疵”?对于一个成熟的社会,民众知道,“法律许可”和“道德许可”的明确区分,这是社会必须面对的基本概念。
也有人引入了法律上划在“言论自由法律界限”之外的“仇恨言论”概念。这也是在法律的逻辑上被一再细细推敲的概念。
“禁止种族歧视”言论同样违背言论自由
在上面的那些案子上可以看到,制度化的言论自由,在操作上是极其复杂的事情,对人类的智慧是巨大挑战。言论和表达是有力量的,也可能具有杀伤力。并不是所有的言论都受到法律保护。人们必须面对不计其数在不同年代的案例,思考怎样处理。至今为止,还在不断认识和修正的过程中。
美国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在1992年的“R•A•V对圣保罗市案”。R•A•V是一个青少年的名字。他在一家黑人门前焚烧了一个十字架,被控违反了圣保罗市当时新出台的“禁止煽动种族仇恨言论法令”。圣保罗市法令的条文,是禁止使用“种族、肤色、信念、宗教、以及性别等原因引起愤怒、恐惧和憎恨”的言论。
要说明的是,言论自由的“言论”后来延伸到“非言辞表达”。焚烧十字架的行为,就是一种典型的“非语言表达”。在历史上,如KKK这样的白人至上主义组织,经常用于他们的仪式,伴随他们对黑人的恐吓甚至私刑。

1999年3月20日,30名三K党成员举起左手宣称“白人的力量”在俄亥俄州法院外集会,招募新成员。三K党是美国历史上及现在的一个奉行白人至上主义运动和基督教恐怖主义的民间仇恨团体,也是美国种族主义的代表性组织。
当时的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该法令仅对涉及有限、特定的言论予以禁止,说明圣保罗市政府对特定主题言论和其他主题言论,有“区别对待”,“这种偏袒构成了观点性歧视”。就是说,这个立法并不是说“凡是引起愤怒、恐惧和憎恨的攻击性言论”都违法,那么,它就有了“议题偏袒”。为什么在这些“特定议题”之外的“其他引起愤怒、恐惧和憎恨的攻击性言论”就被法律排除在外呢。所以,圣保罗市的“禁止煽动种族仇恨言论法令”因其没有维持对言论内容的立场中性,被判违宪。
但是2003年,联邦最高法院在十一年后重新思考,支持了弗吉尼亚州的一部立法,它“禁止为恐吓个人或群体而焚烧十字架”。起因是美国KKK在历史上对黑人私刑的时候,有伴随焚烧十字架的行为。
最高法院经过重新考虑认为,从威胁言论中挑出最具恐吓性的某个“表达形式”加以禁止,并不构成偏袒和歧视。因为这一种“特定表达”对黑人深具现实的生命威胁与恐吓的含义。“威胁恐吓”是不受保护的言论。
“R•A•V对圣保罗市案”以政府法令违背立场中性而被否决,那么,是不是一切“凡是引起愤怒、恐惧和憎恨的攻击性言论”都违法,都可以划在法律规定的“仇恨言论”以内,也就是说,有了这样的言论就要被抓起来吗?
有人在《查理周刊》之后评论说,那些有宗教冒犯的漫画涉及“仇恨言论”,如果在美国大学,有这样言论的教师早就被学校开除了。这是不严谨的说法。联邦最高法院不仅依据政治漫画政治讽刺的特点,对它有特别的“生存宽容”,对“仇恨言论”的定义也十分谨慎。
联合国有几个国际条约和公约,号召各国不仅禁止宗族歧视和其它各类歧视,也号召禁止宣传此类歧视的言论。美国依据自己的言论自由传统,对此持相对谨慎的态度。例如在1978年,卡特总统代表美国按时签署了《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公约》,但是同时签署了一条有法律约束力的保留:“公约中的任何规定不得视为要求或者授权美国立法或者建立其它程序,限制其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权利。”
也就是说,美国赞同公约的原则,但是,涉及具体案例,它只能按照这个国家对言论自由的立法逻辑来处理。它还是需要循它原来的不间断的、小心翼翼的思路继续衡量和判断。
校内过度禁止侵犯性言论会削弱学术自由
其后不久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的大学校园就随之兴起“禁止仇恨言论”运动,起源就是“反种族歧视”,要在校园内禁止“暴力言论”,制定《言论守则》,其中非常有名的是《斯坦福大学言论守则》,禁止“根据个人的性别、种族、肤色、生理缺陷、宗教信仰、性取向或血统,对个别人或少数个体进行口头攻击和语言侵犯。”
1995年马萨诸塞大学的一个分校,在《言论守则》中对禁止的言论类别,还加入了“年龄、婚姻状况和是否服役”,该校学生联合会还要求加入“公民身份、文化传统、艾滋病毒携带者、语言、家庭背景、政治信仰和孕否”等条目。
《言论守则》的出发点当然是善意,可是,它的规范其实很复杂很困扰,例如批评到怎样的激烈程度,就算“仇恨语言”了呢?它的禁忌越来越多,无形中会令人活得小心翼翼、顾首顾尾,束缚和愚化了人的自由讨论状态,甚至破坏幽默感、创造力。对大学这样一个理应最开放活跃最有活力的地方,约束了众多社会话题的自由讨论,影响了学术自由。因为很多话题的内容,你很难确定哪句话就是“具有侵犯性”了。
1989年,联邦法院裁定《密歇根大学讲话守则》违宪。几年后,《斯坦福大学言论守则》被判违宪。“言论守则运动”渐渐消失。但是,它还是在无形中给美国留下了很深的正面和负面的双重印记:它令人在“种族”等敏感话题上留意自己语言对他人带来的感受;它也令许多敏感议题的深入讨论无法正常展开,很可能因此延迟了一些敏感社会问题的尽早解决。

美国联邦法院于1989年裁定《密歇根大学讲话守则》违宪。几年后,《斯坦福大学言论守则》被判违宪。
在大学里,教师也确实可能因为言论被解雇。那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就是大学“机构自治”原则和教授言论自由有时会产生冲突。它的前提是联邦最高法院在几个判例中确立了大学的“机构自治”。例如,在“斯维奇诉新罕布什尔州”中,大法官法兰克福特就强调了大学“免受政府控制”的独立性。但是,大学的自治原则下,如果有教师或学生诉学校侵犯了他们的“自我表达权”,他们得到司法救济的机会也会相对受到限制。
例如,有些教师因言论涉及种族问题等,被学生认为言辞不当,告到学校,控其有“仇恨性言论”,虽然教师言论涉及公共议题,以“言论自由、学术自由”自辩,但是,在“机构自治”原则下,最高法院认为,教师也是学校的一个雇员,学校作为“独立机构”雇主,有相当大的解雇权。当然,这不仅和“法律惩处言论”无关,这样的程序也和政府并无关系。
相比欧洲,在以法律对待“仇恨性语言”上,美国是很特别的一个国家,和欧洲很不相同。美国的宪法第一修正案甚至同样保护纳粹言论和“否认大屠杀”言论。为什么美国保护纳粹言论?最后一部分接着说。
凤凰大参考专题文章为本栏目特约,转载请注明来源及作者姓名,并发邮件至all_opinion@ifeng.com告知。违者必究。

林达
著名旅美作家,已出版“近距离看美国”系列《历史深处的忧虑》、《总统是靠不住的》、《我也有一个梦想》以及《历史在你我身边》等书。

凤凰网评论微信
扫描微信
凤凰大参考尽在掌握
凤凰评论出品
策划:赵雅楠
栏目合作:zhaoyanan@ifeng.co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