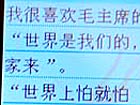我和陶野交上了朋友
分场压缩了编制,将原来的分场的果树对下放到我们连,大部分是孩子妈妈,少数几个男人,年轻人只有一个,叫陶野。我原来就知道他的大名,我们很快就相识相熟了。当时连里组建了一个写作组,我,陶野,张侠民,还有宋娜娜。一共四个人。我们还起了一个颇有文革遗风的名字叫;"指点江山",当时在团里还有一点小名气,不过只办了几个月就消声逸迹了。可是我跟陶野却建立了深厚感情。
他是孤儿,毕业于辽宁的 岳农专果木专业,在当时的农场就是不小的知识分子了。我们都喜爱文学,很谈的来。
夏日的傍晚我们经常漫步在田边的小路上,谈理想抱负。谈我们要写的长篇小说。
夏季的北大荒真是太美了。夕阳的余辉映红了半边天,嗅着新翻泥土的芳香,一望无迹的三江平原,天高望远,心旷神怡。我们连在一个平缓的山坡上,所一我们可以看到很远的一,二,三,六队,看见还没收工的拖拉机,看见晚归的马车,也可以看见一对一对偷偷摸摸谈恋爱的人。张侠民和赵邦妹就被我们碰见好几回。
当时陶野还有意把我调到果园去,让我给他当助手,我倒无所谓,他对果园做了美好的规划,我们的果园有好几百亩,他计划分几个区,种上不同的品种,建一个实验室,将来穿着白大褂穿行于桃红柳绿之中,的确有点诱人。当时我们有五千多棵果树,品种比75连的好,他们的是小,酸,硬。我们的是大甜,脆。叫"123"。不知为什么叫这个名子,前年我去北大荒,尝了尝真是不错。
他给我介绍他们的学校生活,讲他的恋爱,他家曾给他介绍过他的表妹,他没同意,后来他和一队的`一对双胞胎中的妹妹结的婚。叫张丽华。我离开北大荒的时侯他们已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叫陶红。
我们曾经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想得很好,但真动起笔来可不那末容易,人物,事件,情节,构思起来也是绞尽脑汁。后来我们也意识到功力不到,还是先从短篇写起吧。他还有他的一大摊的业务,我也帮不上他的忙。终于眼高手低也没写出像样的东西。
第一次大块的吃狗肉,那是一个香
8月18日来了第一批哈尔滨市知青,吴克和他们一起到的,他是北京知青中第一个享受探亲假的。再加上原来的10个双鸭山知青,连里一下字就热闹很多。
这帮哈尔滨的实在很浑,刚来就要和北京的大爷们打架,那他`们那是个啊,一来就把他们镇住了。以后消停了很多。
我依然住在李秀祖的小后屋,一个人十分寂寞,胡思乱想,身体也月来越坏,我决定搬出小屋住进了刚刚盖好的大宿舍。一开始是和小干子,韩祥,李生平住在一起。陶野当时还没结婚,住在对面。
住进大宿舍生活要丰富多彩的多了。当时张忆;龄在猪棚喂猪,北大荒的冬天太冷,零下三,四十度,经常有小猪冻死,我们哥几个晚上就到猪棚炖上一锅,吃个肚圆,有一天高三和李嘉滨不知从那捉了一只大黄狗,真肥,毛色也`特别好,他们俩用凿子给狗放的血,美美的炖了一大锅,一次楞没吃完,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十分豪气,吃也上瘾,以后我们还自己到副畜队买过鹅,一次,营部演"列宁在1918"高三喝的大醉。难得的一次电影他都没去看。
吃吃喝喝确实是人们的一种交往的媒体,虽说酒肉朋友不可交,但没有酒肉也交不到朋友。
后来调正宿舍,刘柏森偏要住进来,他是机务排的,我没办法,只好搬家。刘柏森这个人十分令人生厌,长得歪瓜裂枣,一副假正经,有一次高三在门口放哨,我正在往他的脸盆里撒尿,他突然从外边回来,我还没撒完呢,高三拼命在门口缠住他,等我撒完了才把他放进来。
后来我搬到了杨明哲,李生平和曹友文的宿舍,晚上没事我们经常躺在被窝神聊。谈人生,谈理想,谈我们走过的路。我也见到了我的一些良师益友。我从六队到四队的时侯,刘一新曾对我说,到四队去可以找曹友文聊聊,过去没机会,现在住在一起,才发现曹友文真是一个十分有头脑的人,他说话慢条斯理,好象总是在观察着什么,思考着什么,但是脾气有点死倔,一次排长万瑞吉叫他出操,任凭排长磨干了嘴皮,他楞是一声不吭,好象没这个人一样,后来连里把他树为"老大难",其实真是有点冤枉他,他干活十分卖力,从不偷奸耍猾,而且待人诚恳,知识广博。只是没好好发挥他的特长而已。
李生平我们接触比较多,从初一我们就在一起踢足球,不过跟我一样也是替补。他博得人们的喜爱是因为他的为人正派,憨厚,不爱说话。
杨明哲是我们的良师益友,他是双鸭山数学竞赛第一名,他有时还回给我们出些立体几何题,我们都是初中毕业生,那懂那些,他就启发我们,他觉得北京的学生知识面就是宽,有时我们也聊些文学,高尔基的鲁迅的,我们的聊天是起发式的探讨式的,不象张侠民跟你聊天,他总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他很自负,实际上当他真正接触北京人之后,他也规矩了好多。我们宿舍有时也搞些小宵夜,我们回在电炉是做出香浓的巧克力奶茶,我们也会聊些各地的美食。我的古文比较好,所以他们给我起了一个外号"老夫子",后来一直在叫。
转眼在马棚工作已经一年了,岁说马棚的或不多,但没把子力气也是顶不下来的。光说那两个大水桶足有一百多斤,还要劈柴烧水,北大荒的冬天白天有特短,下午三点半天就黑了,够紧张的。平常没事还会去骑骑马,刘少征在猪棚没事他硬拉着我去骑马,我骑老黄马,他骑小里套,一直牵到八号地,我在前边一打马,老黄马撩开蹄子往家里跑,我只听得耳边风声呼呼作响,双手紧紧抓住马鬃,等我跑过晒场回头一看,只见一匹光马,主人不见了,等了半天才见刘少征一瘸一拐的从后面赶来,嘴里还不听的骂着,"这他妈的破马,一跑他就低头,没几步我就摔下来了。"我骑在马上哈哈大笑。不过我也被马狠狠的摔过几次,那年冬天,我们丢了一头牛,天都快黑了,马棚的人分头去找,我牵出一匹白马,老杜说天冷要戴着手套,我戴上手套又抓不住马鬃,没跑几步一个倒栽葱把我狠狠地摔在了草地上,还好草厚雪也厚倒没摔疼。
这一阶段在我的一生中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我变得成熟了,我学会了冷静地观察世界,深深的思考了一些问题,我开始向领导进言阐述我的观点。我觉得我变得成熟了。
| 您可能对这些感兴趣: |
|
|
|
作者:
毛鸿德
编辑:
刘延清
|